
画家乌恩

乌恩
昔年乌恩先生常来我家,他素重仪表,看上去总是衣着得体、有样子,而夫人孟玉珍身量不高,有时也陪着来。他和我父母相识已久,来家后闲聊一呆就是半日。我当时已经学画,知道他是自治区美协最初的副主席,满族,可是通蒙古语。家里曾有过一张他的国画,后来遗失了。
乌恩原名张恩贵,是出生在北京的旗人,小时候已家道中落。他的姑父经常往来于锡林郭勒盟做生意,听说王爷身边需要人,就征得他母亲的同意把年少的张恩贵带至锡盟做了王爷的茶童。几年后蒙疆政府让王公子弟和蒙古族青年接受新式教育,王爷的儿子也许是养尊处优的缘故,不愿就学,张恩贵得到机会顶他的名额上了张家口兴蒙学院。他所读的师范二部是给各旗的小学培养师资的,到1945年毕业时正赶上抗战胜利,乌兰夫主席去他们学院选拔人才,他随即在那里参加革命,据夫人追忆,连他后来的名字“乌恩”都是乌兰夫起的。

此时的乌恩意气风发,由于爱好美术,他选择去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美术组,在周戈、张凡夫、尹瘦石麾下工作。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1946年7月文艺工作团撤离张家口,一路辗转经锡察草原来到林东,稍作休整,与另一支来自赤峰的文工团汇合后又去了王爷庙(乌兰浩特),路途十分艰辛。据文浩回忆,他们经常风餐露宿,仅有的交通工具是三辆双套马车,上面放着道具服装箱和乐器;而团里的队员们、尤其男青年,主要徒步走。他们沿途在居民点张贴宣传画、漫画,还抓紧时间用画笔记录着牧民的生活。我从张绍柯编制的《内蒙古剪报》上见过几幅画,有头像亦有生活速写,可以从侧面窥见几分当初的景况。他们的这批画不计工拙,若留存至今将会印证历史,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第二年8月他和尹瘦石调至王爷庙的内蒙古报社,开始筹建《内蒙古画报》。从那时起到今天,转瞬七十多年过去,这段历史知者寥寥,除尹瘦石外,在内蒙古本土,乌恩正是美术事业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1957年他因说了“党内有裙带关系”,被定为右派言论遭到批判,行政降级并下放劳动。记得他给我讲过一段经历,是当右派时在呼和浩特南郊桃花公社劳动,某日骑自行车回城,路上有匹大狼由远及近追来,他发现后急忙下车,怕狼从后面扑上来,手中无物无法抵挡;狼只是不远不近地跟定他,并不进击,可他内心难免紧张。就这样好不容易走至小黑河的监狱附近,看见高墙处有站岗的军人,才松了口气,没曾想军人不让靠近,他说后面有狼,军人亦不听分辨,还拉枪栓让他赶紧离开;无奈,只好一面和狼周旋一面走;延宕至日暮时到了城边,见有人家,狼掉头而去,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此事给现在的人讲恐怕难以置信,但我小时候呼市周围确实狼多,上小学时路过的曙光街在新城,两侧民房的墙上用白粉画着圆圈,据说也是防狼。

《领到了选举票》
改革开放后他的右派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再见到时他正作画,在博物馆的一间画室里与蔡树本合作一幅油画《深情》,这中间我和树本曾去北戴河写生,半个月后回来,见他仍站在那儿,端着调色盘蘸油彩调整画面。此时,他们已结为亲戚,其子找了树本的妹妹,夫妻二人都在广播文工团工作。另一次去北京观展,记不清是一道走的还是在京相遇,他带我和树本去了美院陈列馆,正值展厅布展未开放,他找到馆长、一位外表像老干部模样的妇女,让我们提前进去,说那人是罗工柳夫人。看罢展览又请我们吃了担担面。

《妻子像》
回呼市不久听说他病了,我和树本去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人显得消瘦,头发也剪短了。他的一生几经波折,真正安心作画的日子并不多。从他留下的一幅1955年的油画《妻子像》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平静,此时的他刚从美院归来,正处在技艺最纯熟的阶段,他的代表作《伊敏河畔》也是这阶段画的。他在这幅画中刻画了二十几个人物,画中坐着勒勒车过河的年轻女子,就是由妻子摆动作画的。
《伊敏河畔》顺时针旋转90度观看

《伊敏河畔》局部 顺时针旋转90度观看

其妻孟玉珍是出生于呼盟的达斡尔人,家族是当地上层,父亲贵福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同父异母哥哥凌升做过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因不满意日本人的专横跋扈,和他们对着干,最后在1936年被日本人以“通苏通蒙”为由杀害。我翻看文史资料,据当事人回忆,凌升最后是慷慨赴死的,他的胞弟等数人也一同殉难。札奇斯钦在《罗布桑车珠尔传略》中,记述了自己的父亲得知挚友凌升惨死后的郁愤心怀。两位兄长的死,对孟玉珍和她的家族影响深远,老父贵福也退隐家中,直至五年后病逝。到了抗战结束前夕外面世道混乱,长辈把手中的浮财分给子女,准备日后分散躲避。而她本人上东北军政大学后接受了进步思想,随后把自己的那一份捐给了初到呼伦贝尔、立足未稳的文艺工作团,并成为团里的舞蹈演员,她和乌恩就是此时相遇的。到了晚年老太太还清晰记得最初会面的情景,说团里开会,乌恩在会上发言,自己就是这样第一次见到的他。母亲曾和我谈起过孟玉珍,说她是大户人家出身,年轻时家境好,可遇到乌恩后,主动追求结为连理。


《公社接羔员》
听说夫人高寿,依然健在,只是听力不佳,有九十几岁了。也许是自幼受父兄影响,见识过场面的缘故,她身上总有那么股劲。一次在内蒙古博物馆看展,她指着进门不远处挂着的一张照片对儿子说,那个给毛主席献花的人就是自己,后来北方新报还专就此事对她进行了采访;即使到了高龄,她独自一人拎包随旅行团去国外也到处跑。这次疫情初期人们多很紧张,可老太太照样不戴口罩出门。他们在文工团的儿子后来去了珠海,孙女告诉我珠海家里尚有他爷爷留下的画,我加了她的微信,陆续发来几幅,其中有一张接羊羔的水印版画,曾在日本出版,是我先前见过的。

《乌恩的夫人孟玉珍和孙女米娜》
乌恩是有情趣的人,年轻时居家用留声机收听外国歌曲,自己还会拉小提琴,喜欢栽种君子兰,摆弄日本茶具等。反右前家里也常有友朋往来,当时有位擅长年画的画家常到他家,每逢过年必给他的母亲磕头,后来也不登门了。面对着人情冷暖,他陷入沉思,与圈内的人往来渐疏,所以日后给人“孤傲”的感觉。他对子女一向管教很严,儿子长大学小提琴,他心有余悸,认为将来当个工人平平稳稳就得了,不要进文艺界。可儿子在母亲怂恿下坚持不懈,到后来他才转变看法,出面联系让儿子进了专业团体。
由于长期身处逆境,他一生的最好时光被白白消磨掉,待到风停雨霁,刚把精力投入自己喜欢的绘画当中,生命却戛然而止了。当前文提到的《深情》参加首届全国少数民族美展并获奖时,画家本人刚故去不久,那次展览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美术的盛会,来自全国各民族的作者汇集一堂。我们这些与他相识的人,每一念此,常为之遗憾心有不平。


《草原上的新路》
前两年,适逢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我在新城西街的旧美术馆看了一个文献图片展,展出不少老照片、老年画、老画报。除了一张老美协班子成员和尹瘦石的合照外,我注意到里面有乌恩的几件作品,既有与别人合作的年画、连环画,也有自己独立完成的画,其中一套彩色连环画《草原上的新路》,印在1955年出版的《内蒙古画报》上,表现了单干户阿迪亚的畜群遭遇暴风雪,最后参加互助组的故事。由此可知他对牧区新生活的熟稔。他的《保卫和平》采用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勾勒出牧民围拢过来听人宣讲、签名的情景,画中出现了毕加索的和平鸽,还有牧民在拉马头琴,一派祥和景象。他和官布合作的年画《抱上胖娃娃感谢毛主席》,描绘了牧民得子后的喜悦心情,在当时公开出版发行产生过广泛影响。他去世后《伊敏河畔》有段时间就挂在树本位于内蒙古报社的家里,我未见过原作,听树本讲这幅画很大,画得还是有些才气。由于年深日久,屡次搬动,画的内框已经瓢了,再加上刷房子时画面落上了一层白粉,为了保护画,后来树本把它从木框上卸下,又和另外两张画一并卷至装画的大筒里。只是当初画布底子做的不够好,颜色多有脱落,以至一直不敢再翻动,随后寄到南方,由他的孙女保存。
对于前辈,我们应该挖掘整理遗产,给自治区现代美术的早期历史,留下比画作本身更多一些的印迹。
2020年6月16日
奥迪/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原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国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抱上胖娃娃感谢毛主席》

《热爱和平》
乌恩(1927—1981),原名张恩贵,满族,北京人。擅长油画、年画、连环画。1945年毕业于张家口兴蒙学院师范二部,同年参加工作,任内蒙文艺工作团干部。1947年8月,与尹瘦石由文工团调到《内蒙古日报》社工作,着手筹备《内蒙古画报》的出版工作,任《内蒙古画报》社创作组组长。1950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专修科学习。1956年8月,担任美协内蒙古分会副主席(驻会)兼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平反恢复原职。
多幅作品参加全国、自治区美展。年画《抱上胖娃娃感谢毛主席》(合作)1952年在首次文化部年画评奖中获奖;油画《伊敏河畔》1957年获首届全区文艺创作评奖二等奖;油画《深情》(合作)1982年1月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美展佳作奖。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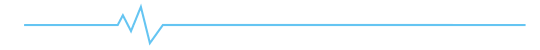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