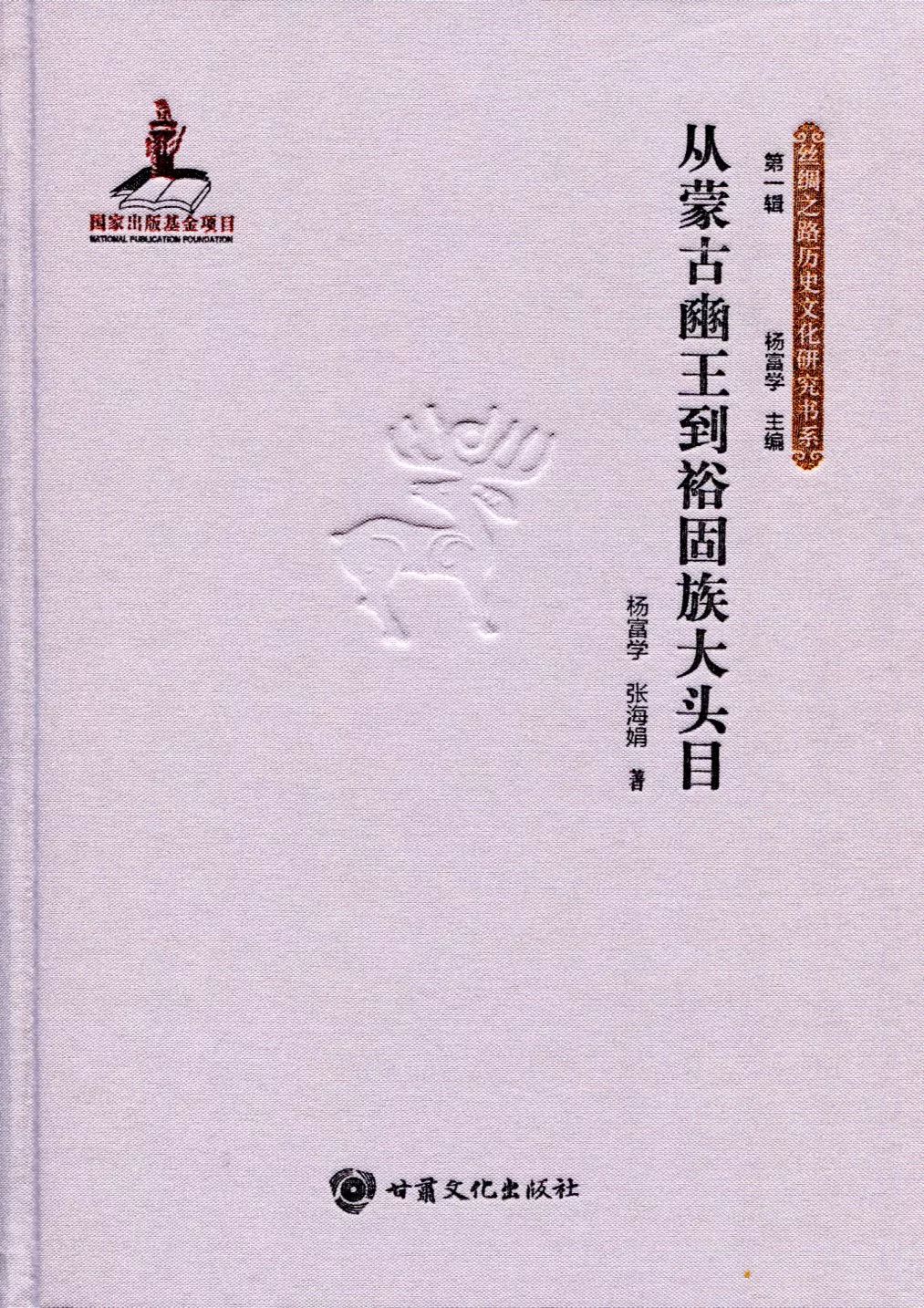
作者: 杨富学
出版社: 甘肃文化出版社
出版年:2017-5
字数: 326千字
定价: 69.00
装帧: 精装
ISBN:978-7-5490-1262-6
《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一书,主要阐述了13世纪后半叶西域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发动反对元中央王朝的叛乱,察合台曾孙出伯、合班兄弟率骑兵万人于1276年率众东归,投奔忽必烈,受到重用,出镇河西与新疆东部地区,被封为豳王,后又派生出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蒙古豳王家族优渥境内诸族,与回鹘关系极为密切,奉行佛教以抵御来自西域的伊斯兰教的渗透,促进了回鹘佛教文化在河西西部地区的持续繁荣,为裕固族佛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蒙古豳王家族与回鹘关系密切,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
杨富学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10项;出版《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回鹘之佛教》《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庄浪石窟》《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甘州回鹘史》《回鹘摩尼教研究》《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元代畏兀儿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及其续编、《回鹘学译文集及其续编及译着《回鹘与回鹘社会》等多种著作,发表论文300余篇,译文百余篇,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丛书)》《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历史文化丛书》《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大型丛书。《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于2017年5月出版,此为最新推出的精装版,乃作者三十余年来研究西北民族史心血的结晶。
目录
绪论(1)
一基本史料述评 (2)
二研究状况 (6)
三选题意义 (10)
第一章蒙古诸王在西北的混战与豳王乌鲁斯的形成(13)
第一节阿鲁忽西使及其对察合台汗国的掌控(14)
第二节海都与八剌之乱(19)
第三节察合台汗国汗位更迭与出伯东归(24)
第四节豳王乌鲁斯的形成(28)
第二章豳王家族对河西西域的镇守(38)
第一节豳王家族的防守区域(38)
第二节豳王家族军队之构成(43)
第三节豳王家族于元代西北地区的征战(49)
第四节豳王家族于明初的活动(56)
第五节明代哈密二王之废立(60)
第六节明朝关西诸卫与蒙古豳王家族之关系(67)
第三章豳王辖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76)
第一节元初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凋敝(76)
第二节屯垦与当地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79)
第三节整饬驿路及其作用(83)
第四章豳王辖区佛教的发展与敦煌石窟的营造(89)
第一节豳王家族之奉佛与河西西域佛教的发展(89)
第二节豳王家族与敦煌石窟的营造(94)
第三节文殊山石窟与蒙古豳王家族之崇佛(105)
第四节文殊山万佛洞与蒙古豳王家族之关系(110)
第五章蒙古豳王家族与亦集乃路之关系(124)
第一节亦集乃路与豳王家族之军政关系(124)
第二节亦集乃路与豳王家族之物资供给(131)
第六章榆林窟第12窟回鹘文题记所见威武西宁王考释(137)
第一节榆林窟第12窟所见回鹘文题记 (137)
第二节题记所见Buyan-Qulï Ong为威武西宁王考论 (139)
第七章蒙古豳王家族的民族政策(145)
第一节河西发现的多体六字真言 (145)
第二节多体六字真言所见豳王家族的宽松民族政策 (152)
第八章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155)
第一节元明时期蒙古豳王对河西的经营与影响 (155)
第二节豳王家族与辖域内回鹘人的特殊关系(157)
第三节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之关系(162)
第九章裕固族大头目的来源及其谱系(167)
第一节《有元重修文殊寺碑》所见蒙古豳王世系(167)
第二节从蒙古豳王到安定王 (173)
第三节裕固族大头目“安”姓应来自“安定王”(177)
第四节裕固族大头目世系表 (181)
第十章裕固族东迁与蒙古豳王之关联(185)
第一节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说(185)
第二节裕固族东迁传说的演变 (191)
第三节黄头回纥与关西七卫 (196)
第四节裕固族东迁为豳王辖区内部转移说(199)
第十一章蒙古豳王与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202)
第一节回鹘与吐蕃的早期接触 (202)
第二节藏传佛教在豳王辖区的兴盛及回鹘的皈依(209)
第三节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217)
第十二章蒙古豳王家族与锁阳城及大塔之关系(224)
第一节锁阳城大塔非西夏塔辩(224)
第二节锁阳城大塔为元塔说(228)
第三节锁阳城遗址与蒙古豳王家族之关系(231)
第十二章结论(235)
大事年表(237)
参考文献(235)
索引(276)
后记(293)

后记
裕固族的族源可直接追溯到回鹘,这已为国内外学术界的通识。
如所周知,回鹘原居漠北,其族源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代的丁零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铁勒。当然,回纥又不等同于铁勒。铁勒部族众多,计达四十部,回纥只是其中的一部而已。该部在南北朝时写作袁纥,隋作韦纥,唐朝作回纥。据史书记载,回鹘族分为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又称“九姓回纥”,包括药罗葛、胡咄葛等九个氏族;外九部又称“九姓乌古斯”,包括回纥部、仆固等九个部落。内九族是回纥最基本的氏族集团,以药罗葛为首,日后回纥可汗多来自该氏族。今天裕固族的亚拉格氏,即由此而来。外九部是回纥与其他八个部落构成的集团,以回纥部落为首。到744年漠北回纥汗国建立以后,这些不同的部落亦统名曰回纥。贞元四年(788),回纥统治者上表唐廷,请求改名回鹘,得准,故以后的史书一般都以回鹘命名之。
漠北回鹘汗国的强盛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至9世纪30年代开始由盛转衰。840年在黠戛斯的打击下分崩离析。回鹘汗国灭亡后,部众四散外逃,大致可分为向南、向西两个方向。
其中南下的十三部逃至唐朝边塞,被唐将击破,不知所终。西迁者分为三支,一支逃往中亚,建立了哈喇汗王朝,在短期内继承了漠北回鹘的文化传统,使用回鹘文,并信仰佛教,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回鹘佛寺遗址,即为历史的见证。10世纪中叶,哈喇汗王朝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回鹘文化传统基本中断。第二支入西域,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处)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蒙元时代,高昌回鹘文化昌盛,影响甚大,史不绝书,只是族名称谓不一,常被译作畏兀儿,有时又译作瑰古、乌鸽、畏午儿、委兀儿、畏吾儿、畏吾尔、畏吾而、畏吾、畏兀、卫兀、外五、伟吾尔、伟吾而、伟兀、伟兀尔等。清代称为回子、缠回等。写法很多,不下六十种。直到1935年才由新疆省政府以檔的形式将其定名为“维吾尔族”。第三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先后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在论及裕固族族源时,学界奢谈甘州回鹘而忽略沙州回鹘。其实,恰恰相反,沙州回鹘所辖的沙、瓜、肃三州,才是裕固族得以形成的根本所在。甘州回鹘于1028年亡于西夏后,几乎销声匿迹,没能给后世裕固族的形成留下多少可以确定的因子。当然,待定因子还是不少的,如“黄头回纥”有可能来自甘州回鹘之孑遗,裕固族对汗点格尔的崇拜有可能来自甘州回鹘天崇拜等。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黄金家族成员豳王、肃王、西宁王成为肃、瓜、沙三州回鹘居地的统治者,另有威武西宁王,成为哈密一带的统治者,那里也是回鹘文化的繁荣之地,著名的回鹘文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就是在那里发现的。回鹘高度发展的文化对入居河西的蒙古人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蒙古贵族在文化上逐步回鹘化。经过元明二代的长期融合,最终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在这个民族共同体中,回鹘的核心力量体现在经济文化层面,而蒙古的核心力量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就一个民族的形成而言,决定民族内在特质的往往是经济文化而非政治,这一规律在裕固族中同样适用,尧乎尔(又称尧熬尔,乃回鹘Uighur的音译)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名称,切要根基庶几即存乎此。
今天的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历史上并非如此,萨满教、摩尼教、佛教、祆教、景教、道教都曾在回鹘中长期盛行。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化进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时间。迁入西域的回鹘人,继承漠北回鹘的传统,以摩尼教为国教,同时受当地流行宗教的影响,多数民众皈依了佛教,还有一部分皈依了景教、祆教和道教。他们以回鹘文为主要书写工具,同时,出于宗教的需要,又用其他文字作为拼写回鹘语典籍的工具,如以摩尼文书写摩尼教经典,用叙利亚文书写景教文献,用婆罗谜文、藏文书写佛经,不一而足。10世纪中叶以后,中亚伊斯兰教势力大举东侵,西域回鹘佛教受到冲击,逐步伊斯兰化。及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域回鹘之佛教势力完全让位于伊斯兰教,漠北以来的摩尼教、佛教回鹘文化传统随之在西域渐趋消亡。
与西域情况不同,河西回鹘在蒙古豳王家族的保护之下,佛教势力得以独存,且有所发展,加上蒙古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崇奉与支持,为裕固族藏传佛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其影响一直延及于今。
裕固族的形成,是以河西回鹘为基石的,以《裕固族简史》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裕固族族源的叙述就是从河西回鹘,尤其是甘州回鹘开始的,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不同意见一直存在,李符桐、薛文波等早期学者都不认同这一观点,前者认为黄头回纥是投降唃厮啰而又西迁的回鹘人,后者则认为河西回鹘与黄头回鹘关系不大,而黄头回鹘与西州回鹘的关系似乎比河西回鹘的关系更大一些。尤其是近期,多数研究者由于受裕固族东迁之歌的影响,认为裕固族是由吐鲁番东迁至酒泉等地的,但在论述时却又不忘记把河西回鹘抒写一番。问题是,如果秉承“高昌回鹘来源说”,那么,对河西回鹘的叙述自然就成为徒劳和一种摆设,而且自相矛盾,无以化解。学人们之所以倾向于西域,尤喜将裕固族的族源与高昌回鹘(西州回鹘)相联系,根源似乎在于误认为将裕固族的来源地追踪得越远越好。殊不知,这种偏颇既不利于理清裕固族形成史的脉络,又无益于探寻裕固族自身的个性,更与历史事实相悖,使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了。河西回鹘与高昌回鹘的发展轨迹是平行的,易言之,裕固族的先民与维吾尔族的先民是在不同地域各自发展的,尽管会有所交叉,互有影响,但基本轨迹是不同的,不可混为一谈。如果将裕固族的来源地界定在高昌,势必会让人产生裕固族是维吾尔族分支的误解。
谈起裕固族族源,“西至哈至”的东迁传说自然会萦绕于心。但凡裕固族研究者,概莫能外。至于“西至哈至”具体何指,由于史无所载,众说纷纭:一说称之为西州、火州的转音,即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才让丹珍在整理该传说时,直接命名为《尧熬尔来自西州哈卓》,导向意义更是非常明显。此外的说法有“盐渍甘州”说、“安定曲先”说、“肃州西方”说等,还有说是从哈密、于阗、喀什,甚至是撒马尔罕来的。我们近期的研究证明,所谓“西至哈至”,实乃沙州、瓜州之译音也,《元史·移剌捏儿传》把沙州、瓜州写作“蛇州”“合州”,《元史·成宗纪》作“薛出”“合出”,明人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卷6《为夷情事》(撰写于1516)更写作“写出”和“哈出”。Šiči-Hači/Šiji-Haji(西至—哈至)是西部裕固语的读法,在东部裕固语中,情况有所不同,有时读作Šiči-Hači/Šiji-Haji(西至—哈至),有时又读作Šeči-Hači/Seji-Haji,可译作写至—哈至,也可译作赛至—哈至。“州”,裕固语读音为“至”,如肃州(今酒泉),今天的裕固语就读作肃至(Sukči/sugji)。以此类推,“写出”和“哈出”在裕固语中就是“写至”“哈至”,连读之,就成了写至哈至/西至哈至了。裕固族东迁的出发地不是高昌,而是沙州和瓜州(即所谓的“西至哈至”),更具体一点儿说,是从莫高窟和榆林窟启程的,比较原始的裕固族东迁之歌即谓“我们是从西至—哈至来的人……千佛洞万佛峡来的”。原歌词称裕固族是由“千佛洞万佛峡来的”,及至20世纪80年代被径改为“经过了千佛洞和万佛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东迁裕固族最后迁徙至肃州一带,整个东迁范围,自西向东,皆不出蒙古豳王家族的辖境。在此之前,《裕固族简史》也提出过类似见解,只是受体例所限,只能从简,未展开讨论,故而缺乏说服力。兹后,胡小鹏撰《试揭“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之谜》和《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二文,也把西至哈至考订为沙州和瓜州,但由于未能将东迁事与豳王家族的作用联系起来,缺少必要的中间环节,同样不能完全服人。笔者认为,只有把裕固族历史置于河西回鹘大背景中来认识,将河西回鹘之源与蒙古豳王家族之流通盘考虑,才能真正解决裕固族形成史研究中的诸多难解之谜。
裕固族文化发达,追根溯源,与源远流长的回鹘文化,尤其是河西回鹘文化息息相关。由于各种原因,在今人撰写的维吾尔族文化史著作中,回鹘文化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河西回鹘文化更是几乎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如李国香先生撰广受学界好评的《维吾尔文学史》,仅给出回鹘文学一章的篇幅,区区14页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4%,而且是《高昌文学》,没有关于河西回鹘的文字。无独有偶,维吾尔族学者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维吾尔文学史》、海热提江·乌斯曼着《维吾尔古代文学研究》、拓和提撰《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等,同样也仅给予古代回鹘文化以十分不相称的短小篇幅,河西回鹘文化几乎被忽略。而事实是,宋元时代的回鹘文化成就巨大,影响深远,不仅是维吾尔文化史的巅峰,而且对周边民族(如党项、契丹、蒙古等)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一时期,河西回鹘文化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敦煌发现的回鹘文献数量约为现存回鹘文文献的三分之一,沙州回鹘的石窟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可等闲视之。
古代回鹘文化之所以未引起足够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回鹘文化研究者未必精通回鹘语文,即使有所了解,也未必能够见到回鹘语文献的刊本,更不用说回鹘文献原件了;其次,与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回鹘文化的研究有赖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零篇断简和石窟壁画。而这些文献残片散藏于世界各地,收集整理不易,不若后期伊斯兰时代的文献保存完整、丰富而又易得。此外,不能不承认,与研究者的文化倾向会有一定的关系。对一个维吾尔穆斯林学者来说,对佛教、摩尼教文化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伊斯兰教文化那样谙熟,那样运用自如。恰如汉族学者对佛儒道文化的认知要远胜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不足为怪。
在如是前提下,回鹘文化,尤其是河西回鹘文化研究的担子,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落在了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作者的肩上。与维吾尔族相比,裕固族对回鹘文化传统的保持显得更完整、更持久,尽管其文化史不若宋元时代西域回鹘文化那样影响巨大。在西域回鹘于10世纪中叶开始伊斯兰化进程时,裕固族的先民——河西回鹘继续保持着摩尼教信仰,佛教渐趋昌盛。11世纪摩尼教于河西消亡后,回鹘佛教兴盛不衰,敦煌、瓜州、酒泉成为元代回鹘佛教文化的中心,直到今天,佛教仍是裕固族的全民信仰。回鹘文化的集中代表——回鹘文,在河西回鹘中一直流行至18世纪。20世纪初,酒泉文殊沟发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抄写于敦煌,长期被视为时代最晚的回鹘文文献。近期,在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又发现了时代比之更晚的回鹘文题记,在纪年清楚的题记中,时代最早者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最晚者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此外尚有万历十五年、万历二十年、万历四十二年、顺治八年、顺治十五年和康熙十三年等。而在西域地区,自10世纪中叶始随着伊斯兰化进程的深化,回鹘文逐步被阿拉伯文字所替代,至十五六世纪时已完全销声匿迹,成了“死文字”。文殊山一带发现的回鹘文字遗物表明,至迟到清康熙朝后期,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成为回鹘佛教与回鹘文化的最后家园。遗憾的是,今天的裕固学其实并没有担负起研究河西回鹘文化的重任,国内出版的几部裕固族文化研究著作,如钟进文着《裕固族文化研究》、贺卫光着《裕固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裕固族民俗文化研究》等,庶几对河西回鹘文化都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有的略有论及,有的则完全忽略。如是以观,裕固族文化史如同其形成史一样,都到了不得不重写的时候。
过往对裕固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经常受一条线索的界定,那就是黄头回纥→撒里畏兀儿→裕固族,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要复杂的多。
近年,我们投入了较大的精力用于琢磨裕固族形成史的问题,尤其是与河西回鹘、蒙古豳王家族的关系问题。随着认识的加深,裕固族形成史的蓝图在我们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了,那就是:把河西回鹘、蒙古豳王家族写进裕固族史,裕固族史也应该从河西回鹘写起,而同时应给予蒙古豳王家族更多的篇章。
1276年,出伯兄弟因不满于窝阔台后王和察合台后王在西域地区发动的叛乱及其家族对察合台汗国统治权力的丧失,毅然率万骑东归,投于忽必烈麾下,受到忽必烈重用,奉元政府之命长期驻守河西。自出伯兄弟始,其家族成员先后被封为豳王(驻酒泉)、肃王(驻瓜州)、西宁王(驻沙州)、威武西宁王(驻哈密)等。他们不仅有效抵御了西域叛王的东侵,捍卫了河西地区的稳定,而且采取措施,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及于明代。在蒙古豳王家族的统治区内,回鹘势力比较强大,且文化发达,受到了豳王家族的优渥与扶持,使回鹘佛教文化在河西西部地区获得持续繁荣。明朝初年,西域回鹘佛教势力逐渐衰退,最终于十五六世纪之交完全让位于伊斯兰教。只有河西地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保护之下,回鹘势力得以独存,社会稳定,文化昌明,尤其是佛教文化,不仅没有随着西域地区的伊斯兰化而走向衰落,而且有所发展,加上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崇奉,受其影响,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裕固族的主要信仰。这些,为裕固族文化的兴盛与长期保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蒙古豳王家族在元明时代始终与回鹘保持着密切关系,回鹘文化对河西地区的蒙古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古贵族在文化上逐步回鹘化,这些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条件。长期的水乳交融与文化上的趋近,使二者最终融为一体,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裕固民族。
过去学术界对裕固族形成史的探讨,多着墨于回鹘因素,对蒙古因素注意不够。主要原因在于包括《元史》在内的历史文献对回鹘记载较多,对包括豳王家族在内的和蒙古的记载却相对较少,而且极为紊乱,以至于许多事实都模糊不清,如关于出伯家族的身世,学术界一般推定为:成吉思汗→拖雷→旭烈兀→猛哥帖木儿→出伯。出自东部裕固的著名学者、文学家铁穆尔先生,在《裕固族民族尧熬尔千年史》中考证其祖先来源时,同样采纳的是这种观点,误把来自中亚察合台系的出伯兄弟解释为拖雷的曾孙。从文殊山发现的回鹘文—汉文合璧碑铭《有元重修文殊寺碑》及波斯文史籍《贵显世系》看,出伯真正世系为成吉思汗→察合台→拜答里→阿鲁忽→出伯,原居于中亚,具有伊斯兰文化背景,这完全符合敦煌发现《莫高窟六字真言碣》《重修皇庆寺记》的记载。从二碑看,出伯的三个儿子分别被命名为速来蛮、养阿沙、速丹沙,前者为穆斯林常用名,后二者为穆斯林国家对统治者的常见称呼。这些都说明,速来蛮、养阿沙、速丹沙之取名皆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至其后代,即速来蛮之孙子辈,取名多来自梵文,表现出佛教的强烈影响。若言其出乎拖雷家族,则势必来自蒙古高原或中原地区,其文化背景自然大异其趣。出伯家族对裕固族的形成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误判其来源,就会对裕固族形成史的研究带来许多问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幸的是,地不爱宝,近些年不断有新文献涌现出来,首先是河西地区相继出土的多种汉文、回鹘文、蒙古文文献,其次是敦煌、酒泉等地的相关石窟图像、碑刻、题记等,其三为来自波斯、阿拉伯的异域资料,内容丰富,为重新认识蒙古豳王家族的历史兴衰及其与裕固族形成之关系,提供了前所未知的新数据。本书的撰写,正是得益于新资料的发现与刊布,间或有所获,也应该归因于对上述新数据的倚重。
对本课题的研究最早发轫于1989年,是以《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为开端的,1995年出版的《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杨富学、牛汝极合着,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回鹘与敦煌》(杨富学着,甘肃教育出版社)、《甘州回鹘史》(朱悦梅、杨富学合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可以说是这一工作的前奏,那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裕固族的回鹘裔方面。对裕固族蒙古裔及裕固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则肇始于2009年,在杨富学建议、指导下,张海娟将《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社会》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先后发表《元明蒙古豳王家族史研究回顾》(刊《吐鲁番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31~141页)、《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刊《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第84~97页)和《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1~37页),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12年,张海娟硕士毕业后,进入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工作,继续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本书第一、二、三、四、五、八、十一诸章之初稿均由张海娟执笔撰写。幸运的是,我们先后得到2012年度甘肃省文物局学术研究课题《甘肃河西地区出土蒙古豳王家族文献文物研究》和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编号14JJD770006)的经费支持,使这一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这是我们首先要表示感谢的。
其次,敦煌研究院长期以来坚持以学术立院的原则,对研究工作给予了不少的支持,尤其是坚持以学术为上而非随大流,抵制那种不看质量看数量,不看文章看刊物,不看学问看学位,不看水平看职称的不良学风,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也是我们需要感谢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裕固族学术同仁和朋友的关心与支持,他们是钟进文、铁穆尔、贺卫光、巴战龙、阿尔斯兰(安玉军)、杜曼扎斯达尔(杜成峰)、郭梅及肃南县领导如安玉冰、安秀梅、安维武、A. 玛尔简(安雪琴)等诸多关怀。国内外学术同仁也给予了各种支持与说明,特别需要感谢德国学者Peter Zieme,俄罗斯学者I. F. Popova,土耳其学者Ölmez Mehmet、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松井太、山本孝子,及伊斯拉菲尔·玉苏甫、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张铁山、高启安、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白玉冬、李建宗等,或提供数据,或答疑解惑,或解决考察中遇到的困难等,其情可感。
本书的出版还得益于国家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经费支持。在该书出版过程中,郧军涛、李浩强、凯旋等诸位编辑出力尤多,改正了各种讹误,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此外,参与本书校对、数据复核与索引编制工作的有胡蓉、金琰、闫珠君、钟勤勇等诸位同学,也于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研究既不全面,也有待深入,甚至会有各种谬误,冀识者不吝教正。
杨富学 张海娟
2016年10月8日
- 上一篇: 【第42期】镶珊瑚花丝发饰
- 下一篇: 【民俗】蒙古妇女系腰带的习俗(蒙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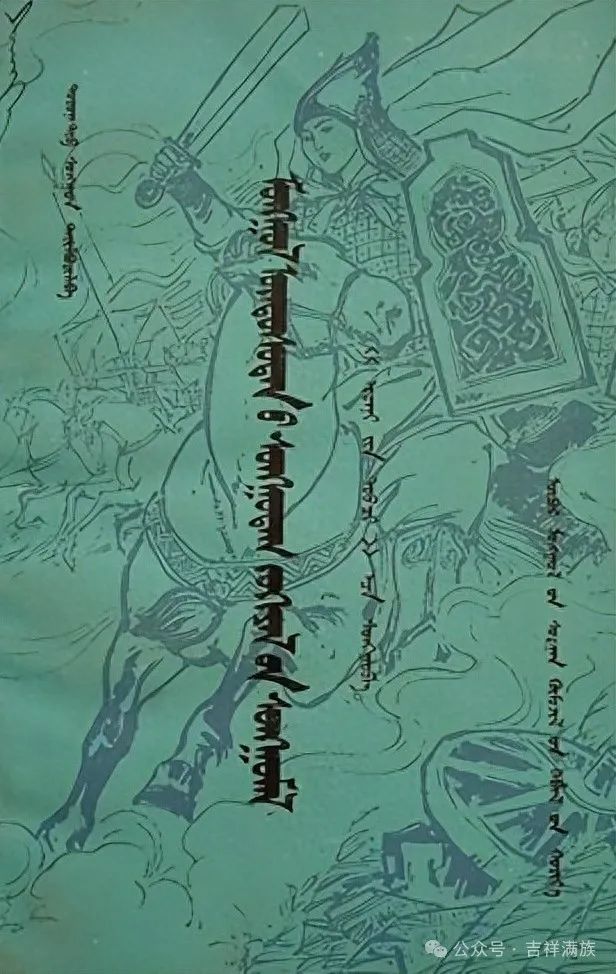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