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及清代八旗时某些蒙古人为荣,大部分蒙古人为耻,小编也很气愤,这也是一种历史演变,关于汉化或满洲化的争论往往占据了主要的篇幅,有意无意中将八旗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八旗蒙古置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正如这一群体在民国初年划分民族归属时的曾经遭遇的尴尬境遇一样。
那么,蒙古人是何时开始流入后金(清)政权的?“满蒙一家”仅仅是指满蒙间频繁的联姻政策吗?入关前的八旗中有多少蒙古人?如今内蒙古境内分布的旗盟建制是否与八旗制度有关?就此种种疑问,小编以奉谈资。
从蒙古牛录到蒙古固山
明代辽东地区的女真(满洲)人与蒙古人间交流往来的频度与深度,特别是民间的贸易往来的程度,可能要远远超出世人的理解与认知。
笔者曾在拙作《后金建立400周年︱明末女真各部为何相互厮杀》中提及,明代的辽东,围绕着开原、抚顺、宽奠这条边境线,曾经存在着一个由女真人、汉人、朝鲜人和蒙古人共同参与的初级市场。更何况如海西女真叶赫部的酋长本就出自土默特蒙古,地域与血缘上的亲缘性决定了海西女真内部存在一定数量的蒙古人,他们在一定时期内被称为“游牧蒙古”或“移营蒙古”。

明末辽东局势图
(一)欧洲人是上帝的宠儿吗
在1924年的老上海,大约是暑期。在一辆电车的头等座位上,坐着白人父子。儿子也就十一二岁,长园的小脸,面颊白里透红,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和平而秀美。车上的一位中国青年人,不由得仔细地多看了这个孩子几眼。谁知,白人孩子到站下车时,在青年人面前停住,突然把脸向这个青年人尽力伸过来,恶狠狠的,好像是说,黄种人,看罢!你配看我!然后下车扬长而去。年轻人羞辱、愤怒而又无奈。他知道,白人孩子凭借着种族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势,在这个孩子眼中,黄种人就是劣等人。
这个青年人把这次经历,这次羞辱的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名为《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抨击白人身上的种族主义。这个青年人就是写了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作家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是语言文学家,可能不太了解欧洲的历史。其实,欧洲历史辉煌的时期是在两端,早期是古希腊、罗马帝国时期,晚近是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帝国时期。从罗马帝国衰落的公元500年到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1500年间,欧洲是一个贫弱之地,是欧亚大陆经济版图上的遥远边陲。欧亚大陆中心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经常劫掠欧洲,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都曾对欧洲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匈奴首领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在欧洲纵横驰骋,以至于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可见欧洲人的痛苦和无奈!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认为,所谓欧洲,实际上就是在抵抗欧亚中心地带草原游牧民族的侵略过程中形成。这也反面说明,当时欧洲的积贫积弱。
欧洲兴起于1500年。水手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也可以到达印度。这样,就可以找到一条替代被穆斯林世界控制的欧洲通往印度的商路。1492年8月2日,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率领三艘帆船出发。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后来西班牙人又在美洲发现黄金、白银,开始了欧洲的殖民时代。通过杀戮当地印第安人,抢夺黄金白银,欧洲人抢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1498年,葡萄牙人达·迦马率领四艘帆船绕道好望角,来到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中心城市卡利卡特。回去的时候,达·迦马搜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回到家乡卖了大价钱,是整个船队探险经费的60倍。暴利让葡萄牙人眼红了,他们要独霸这条商路。不是通过商业竞争,而是用武力把对手消灭掉,把对手赶走。葡萄牙人以一种“海盗+商人”的手段,最终独霸这条商路,并美其名曰“持剑经商”。后来的荷兰、英国纷纷效仿。由此,欧洲人开启了所谓的“大航海时代”。这是欧洲兴起的原点。实际上是欧洲人在母国的庇护下,纷纷驾船出海,碰到强大的国家就老实经商,碰到弱小国家就掠夺。现在好莱坞有一种星际探险类型的科幻电影,总是描写一只宇宙飞船船队在外太空探险、作战,消灭黑暗势力,消灭邪恶生物。这背后,笔者怀疑,是否无意间渗透着欧美人对大航海、大探险时代的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
但是,在1500年时,欧洲的生产力却是乏善可陈。欧洲是欧亚大陆一个荒僻的角落。1498年,达·迦马到达印度卡利库特,但是,却没有带来任何反响。葡萄牙人带来的都是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织品。看看达·迦马献给卡利库特统治者的礼单:羊毛织物、帽子、珊瑚珠串、脸盆、罐装的油和蜂蜜。[1]笔者不太了解印度当时的生产水平,但是,想想我国传统评书中国家间互赠的礼品,达·迦马的这份礼单实在是太差了。卡利库特的统治者卡拉巴尔王公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让达·迦马给葡萄牙国王带回一封信,信上说,他的国家繁荣富足,他希望从葡萄牙得到的是黄金、白银、珊瑚和胭脂。[2]实际上,应该替达·迦马感到幸运,这要是赶上暴君式统治人物,还不落一个羞辱君王的罪名,掉了脑袋。更重要的是,不仅统治者没兴趣,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没兴趣。由于葡萄牙,以至欧洲的生产水平落后,葡萄牙商品在葡萄牙本地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在印度卡利库特的价格,根本就无法进行贸易。
因此,欧洲人在1500年时,只能抢,只能进行所谓的“持剑经商”。
真正改变欧洲人的生产能力,改变欧洲人在欧亚大陆经济版图地位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从此欧洲真正崛起,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成为上帝的“宠儿”。
(二)工业革命巨变
一般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760年。标志性事件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被广泛应用。推动蒸汽机发明的是两个行业,一个是棉纺织业,一个是炼铁业。
棉纺织业在当时是英国的新兴产业。16世纪尼德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约三万名纺织工人逃到英国,给英国带来了纺织技术。棉纺织业属于轻工业,需要的资本较少,资金周转快,容易获利。英国棉纺织工业很快发展起来。最初的棉纺织业都是手工操作,家庭式小作坊生产。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这种织布器械改变了过去织工们用双手相互穿梭的织布方法。织工们只要用两脚交替踏板,飞梭就会自动地织成布匹,工作效率由此提高了一倍。随着飞梭的改进和应用,织布技术迅速领先纺纱技术。六个纺工才能供应一个织工所需的棉纱。
提高纺纱技术成为当务之急。1765年,织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一种手摇纺纱机,被称为“珍妮机”,又称多轴纺纱机。纺锤的数目开始时装八个,后来增加到十六个,到1784年增至一百二十个纺锤同时工作。棉纱产量由此大幅度增加。但是,珍妮机的缺点就是必须用手摇。1768年,普雷斯顿的理查德·阿克莱发明、制成了(实际上是偷了别人的发明)水力纺纱机。这种机器使用滚筒以不同的速度纺成棉纱。从此,纺纱机的转动不再依靠人力,而是利用自然力。英国也从此能够制造出纯棉织品。水力纺纱机体积较大,不适于家庭分散应用。它需要建造厂房,集中生产。1771年,阿克莱在德比郡附近的德温特河岸开办了英国第一家水力棉纺纱厂。工厂出现了。不久,他雇佣了六百多名工人,其中多数是工资较低的童工,这是近代机器大工厂的开端。
1779年,兰开郡的塞缪尔·克隆普顿吸取珍妮机的活动架子和水力机的纺纱滚筒的优点, 发明了综合纺纱机,又称走锭精纺机。这种机器纺出的纱既精细又而结实,一次能够带动三百至四百个纱锭。综合纺纱机自然代替了珍妮机。
今生我们有缘,陪你一起看草原,让爱留心间……
阳光灿烂的夏日,心驰神往。一起到草原,看那蓝蓝的天,看那白白的云,看那远飞的燕……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
走进草原,心飞扬。青青的草,烂漫的花,暖暖的风,一切是那样亲切。根在草原,心怀爱恋,草原的开阔,总能打开紧锁的心胸。这是山的宽厚,风的抚慰,天的洁净,云的懒散,草的青香给予的。
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
草原,你山地草原的特点,离天很近,人称你是倚天草原,摩天草原,一直向往天的无垠和明净,却注定不能与天相连,只能与天相望,与天相恋,这是天与地的绝恋!
根在草原,爱在草原,我要为你歌唱,歌唱蓝蓝的天,歌唱浓浓的情,让歌声随草原的风,传给我的亲人。那里有我的思念,有我心中的恋曲。
作一首草原恋歌,爱你,想你,思念你,化作山雨,淋透我身,浸润我心。
草原,我对你的情永不变,变的只是容颜。你是我的歌,心中永远的歌,一首无名的草原恋歌。
努尔哈赤的崛起,无疑打破了这一地区多民族间长期存在的平衡体系,也因此引起了辽西蒙古科尔沁、扎鲁特、巴林、弘吉喇、巴岳特和乌齐叶忒等内喀尔喀诸部的注意与不安。
其中,科尔沁部早在1593年便作为九部联军之一参与到古勒山之战中,内喀尔喀五部也多次与叶赫女真乃至明军联手,动则纠结“万余骑”与后金为敌。因此,部分蒙古人便以投诚、战俘或零散逃人的身份流入到后金。
在确立与蒙古的同盟政策后,科尔沁与内喀尔喀五部的台吉、贝勒们纷纷内附,“归投”于努尔哈赤的帐下。对此,明人在《三朝辽事实录》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虏(蒙古)自十方寺等处投入奴(女真)寨,至则纳之。今虏过辽沈者投辽沈,而近开、铁者犹投奴寨。”
最初融入女真(满洲)社会的普通蒙古人,凭借自身的才华,一面以巴克什的身份承担起最初的文官职能,一面随军征战尽显勇武之力,如武讷格、阿机拜、甘笃、托克托尔、鄂本兑、和济格尔、阿赖等人,均在历史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归附人数的增加,后金政权自天命六年(1621年)起,陆续将蒙古壮丁编为独立的牛录(或半个牛录),到天命、天聪之交,每旗增设为五个蒙古牛录(即一甲喇),平时隶属于本旗旗主贝勒管辖,战时独立集结成队参与战斗。追溯起来,这40个蒙古牛录应当算作是蒙古旗分最早的雏形。
天聪三年(1629年)前后,40个蒙古牛录被分为左右翼二旗(即“旧蒙古固山”)并设有两名固山额真,其中左翼固山额真为巴克什武讷格,右翼固山额真为鄂本兑。
有多少蒙古人成了旗人?
公元1634年,随着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病逝,天聪汗皇太极终于取得了对漠南蒙古的统治权。
天聪九年(1635年)正月,以察哈尔蒙古降众壮丁3126人分别编入八旗;二月,又编审出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共16953名,其中9123名外喀喇沁蒙古壮丁被编入“外藩蒙古三旗”(即喀喇沁旗、土默特右翼旗、土默特左翼旗),余下的7830名壮丁则“俱令旧蒙古固山管辖”。
但几乎就在同时,旧蒙古固山的两位固山额真鄂本兑(天聪九年正月)和武讷格(天聪九年二月)相继病逝,如何驾驭人数众多的“新附蒙古”也就成为皇太极的当务之急。
相对于察哈尔蒙古和内外喀喇沁蒙古而言,旧蒙古固山辖下的蒙古人归附较早,已经适应了八旗的组织纪律和战术习惯,因此把他们从八旗中析出、充实到新附蒙古人之中,能起到制约、规范乃至促进其融入后金(清)的作用。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皇太极决定将分布于八旗内的40个蒙古牛录析出,与新附蒙古“相合”,扩编为八旗蒙古,如按照天聪年间每牛录150人计,则具体丁额情况如下:

根据上表累计,天聪九年八旗蒙古正式编立时,共有蒙古兵丁16956人。清人魏源在《圣武记•附录》卷11中称:“天聪九年又分蒙古为八旗,兵万六千八百四十”,虽然不知其所列数据的依据,但大约应该可作一观。
如果按照传统上一户五人的习惯进行计算,则八旗蒙古体系内所涵盖的蒙古人口数应该在8.5万人左右,即便考虑到有可能存在部分一户出二丁乃至三丁的情形,这个数字也应该在5万上下。将如此庞大的蒙古人口通过八旗的形式容纳进自己的社会体制中来,可见“满蒙一家”真心不是一句停留在嘴上的政治口号。

福州蒙古营巷,其命名由来似乎与清代的八旗驻防有一定的渊源。
是满洲,还是蒙古?
值得一提的是,八旗蒙古的编立并没有将后金政权内所有的蒙古牛录全部纳入其中,仍有数目可观的蒙古牛录留在了满洲旗分内。
查《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可知,八旗满洲内共有“国初以蒙古人丁编立的牛录”18个,即:
镶黄旗 第二参领 第十六佐领
第三参领 第五佐领
第四参领 第十佐领、第十二佐领
正黄旗 第四参领 第十八佐领
第五参领 第十三佐领
正白旗 第五参领 第三佐领、第十五佐领
正红旗 第三参领 第十一佐领
镶白旗 第一参领 第四佐领
第五参领 第八佐领
镶红旗 第四参领 第九佐领
正蓝旗 第一参领 第一佐领、第十二佐领、第十三佐领
第二参领 第十四佐领
镶蓝旗 第二参领 第十七佐领
第三参领 第九佐领
以上18个牛录主要是由天命七年(1622年)跟随兀鲁特部明安等“十七贝勒并喀尔喀等部台吉共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并牲畜归附”之人编立而成。
来归伊始,努尔哈赤曾“别立乌鲁特蒙古一旗”,不过又在天聪六年(1632年)因“所行违背”被取消建制,改为“令随各旗贝勒行走,所属人员拨与武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即将兀鲁特贝勒分散编入与本人结亲的满洲贝勒旗分,而将其所属之牛录拨入蒙古左右翼二旗统一管理。
至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时,这些一度被“拨出”的蒙古牛录并没有被一体编入八旗蒙古旗分,而是恢复了原来的领属关系,跟随各自的兀鲁特贝勒留在了八旗满洲。

被误认为是科尔沁蒙古人的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实为留在满洲旗分内的蒙古人,本隶属于正蓝旗满洲,后被抬入镶黄旗满洲。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最早归附满洲的科尔沁及内喀尔喀五部蒙古贵族及其属人,因长期与满洲贵族保持着联姻的亲缘关系而被列入八旗满洲的序列之内,当然,保留满洲旗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殊荣,但同时也隐含着统治者对他们的防范之心。
天聪年间陆续归附的蒙古部落则被与“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蒙古固山整编为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八旗汉军一起承担起有清一代“国家根本”的支撑作用,以武力缔造并一度维系着一个幅员辽阔的政权。
八旗制度内的蒙古子弟们与满洲旗人和汉军旗人一样,居于京师又辗转驻防于各地。在严整而漫长的“旗制社会”影响下,他们一方面渐渐融入到旗人之中,一方面又与游牧的蒙古社会产生了语言和文化上的差距,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八旗中的蒙古后裔在上报民族成分情况时,有一部分报了蒙古族,却而也有相当一部分报为满族,还有一小部分报为汉族。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实际,也是民族融合与形成的必然。
相对于八旗满洲旗分内的蒙古子弟和八旗蒙古而言,真正传承着蒙古文化的主体乃是蒙古札萨克体系下的蒙古人。
蒙古札萨克与八旗蒙古
有清一代,施行于蒙古地区的札萨克制度同样也起始于天聪九年(1635年),即前文提到的“外藩蒙古三旗”设立之时。
外藩蒙古三旗设立后的第二年,正式登基为大清皇帝的皇太极命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与蒙古衙门承政尼堪、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汗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处“清查户口,编牛录,审问罪犯,颁布法律”,将外藩蒙古旗增至13个,即喀喇沁一旗、土默特三旗、科尔沁五旗、敖汉一旗、阿鲁科尔沁一旗、翁牛特一旗、四子部落一旗。
并规定每50户为一牛录,其佐领蒙语称为“苏木”,牛录以上即旗,旗长仍为部落酋长担任,蒙语称“札萨克”,这也是现在蒙古旗盟制度的肇端。

银质满、蒙双文“翁牛特左翼札萨克印”
需要强调的是,蒙古札萨克与八旗蒙古并不存在统属关系,而且彼此间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札萨克作为一个行政组织,虽然被冠以“旗”的称呼,但并没有打乱蒙古部落旧有的组织形式,旗长仍有贵族世袭,因此人数也多寡不一、不相一致。而八旗蒙古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则完全遵照八旗制度的要求,每牛录在150人上下,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额真等员也均由朝廷统一任命。
其次,蒙古札萨克是行政机构,设置在部落旧有的驻牧地,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生产状态,而八旗蒙古则完全集中内迁,与八旗满洲一样承担生产和军事职责。此外,就隶属关系而言,札萨克分隶属于蒙古衙门(即理藩院),而八旗蒙古则隶属于相同旗色之旗主贝勒。
部分来源:澎湃新闻
- 上一篇: 【丹麦】收藏蒙古文物最多的国家
- 下一篇: 除了忽必烈以外,明,清33位皇帝不知道自己的龙椅是"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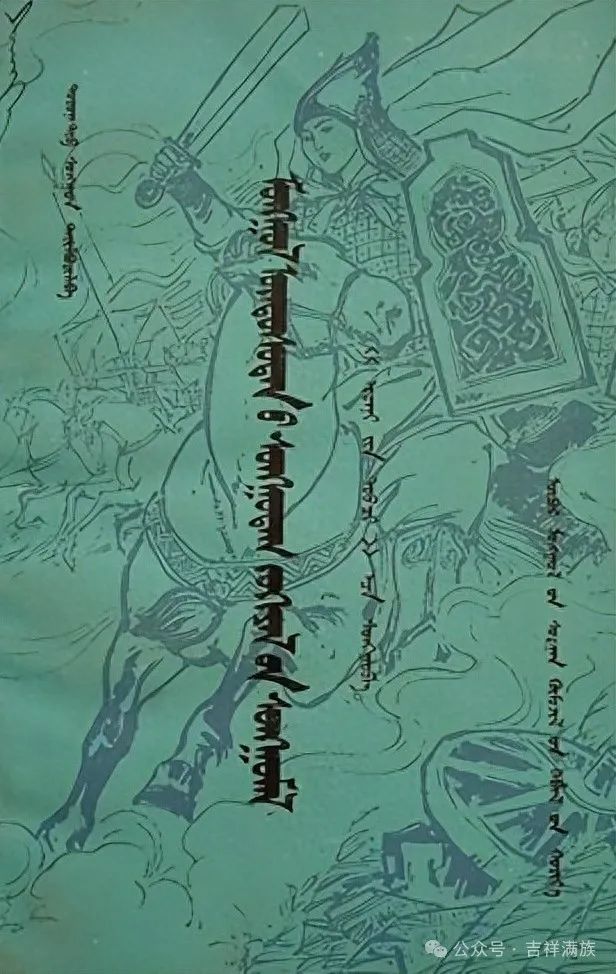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