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指挥阿拉曼战役和诺曼底登陆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战争史》一书中写道:“成吉思汗的军队具有很高的军事效率,他们将作战的机动性与协作性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协作能力使其成为当时最有组织性的军队,他们军事上成功的关键在于情报体系。”

美国历史学家德沃尼克(Francis Dvornik)则在《情报工作起源》一书中感叹道,成吉思汗就像是世界的统治者,他不仅了解帝国周边的情报,还了解并不与蒙古接壤的其他国家的情报,“成吉思汗明白,掌握其将要征战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的重要性,这是他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情报工作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中国古人早就已经十分了解。春秋时期吴国的军事家孙武即有明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过,将这个理论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是蒙古帝国的几位大汗。

西方人笔下的蒙古帝国的情报系统,指的是“站赤”和“急递铺兵”这两项情报传递制度,以及多种情报搜集制度。按照《元史》的说法,“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它的主要职能是通报边境的军情,传达上级号令,“未有重于此者焉”。“急递铺兵”指的是快递情报的兵卒。
驿站制度并非蒙古人的创举。商代的甲骨文里已有记载:“来僖自西,告曰:土方征我于东鄙。”这里所谓的“僖”,指的就是报告军情的士卒。西周时期已有指代邮驿的“邮”字,并有用邮车、快马传递紧急“简书”的邮传制度。公元前550年左右的波斯帝国,也已设立传递紧急情报的邮政驿站。不过,因为成吉思汗创下的霸业太大,蒙古人的驿站制度似乎更受关注。
事实上,很多西方人并不清楚,真正为蒙古帝国设下站赤制度的,并非成吉思汗,而是他的儿子窝阔台。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窝阔台在去世之前总结了自己的功过得失,在总结四件功劳时,他说:“坐在父亲的大位里,我在汗父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我远征金国,灭了金国。我的第二件事,是为使我们的使臣在路上可以疾驰,并搬运所需的东西,设了驿站。还有另一件事,是在没有水的地方,挖出水井,使百姓得到水草。我还在各方各城市的百姓中,设置了先锋、探马等官,使百姓能生活安定。”
但窝阔台没有把功劳都算在自己身上。他说,设置驿站这件事,“是察乃、孛勒合答儿两个人想起来,向我们提议的。”
由于现有史料有限,我们很难得知包括金帐汗国、伊儿汗国等汗国在内的蒙古帝国的驿站制度详情,而只能从元朝留下的史料中窥斑见豹。
根据《元史》的记载,元朝政府在各行省设置了近1400处驿站。至于用来传递军情的工具,陆路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水路则用船。比如,在陕西行中书省设置的81处驿站,即配置了7629匹快马;在江西等处行中书省设置的69处水上驿站,则配置了568艘船。

通过驿站传递的各种情报,以轻重缓急为标准进行分类。加盖玉玺的驿传书信,被称为“铺马圣旨”。如果遇到紧急军务,会以“金字圆符”为凭证,紧急程度稍次的,则以“银字圆符”为凭证。
各路驿站都设有都统领司,他们直接隶属于各路总管府。1274年,忽必烈将各驿站都统领司改为通政院。驿站的官员有驿令、提领及脱脱禾孙。其中,脱脱禾孙主要负责在交通要冲盘查行人。这些官员归属通政院和兵部管辖。
对于驿站的财政支出、资源配备、权责范围等方面,元朝政府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比如,窝阔台在1229年下令:“各驿站都要设置米仓,驿站所辖站户每家每年要交纳一石米,专设一名百户主管此事。”忽必烈在1264年下令:“站户可享受四顷农田免交税粮的政策,其余农田则全部要缴纳土地税。”
元朝政府还对往来使臣的待遇做出详细的规定。比如,窝阔台规定,“北方来的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忽必烈则规定,“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用发钱十文,冬季每天发给炭五斤”。
至于“急递铺兵”制度,元朝政府规定,各处官府要依路程的远近、人数的多少,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五里就设一个急递站铺,每铺设急递铺兵五人。此类兵卒从各州县百姓中征发。快递的情报要封锁在匣子里,“其匣子长一尺,阔四寸,高三寸……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
明代学者宋濂等人评论,正是因为有完备的驿站制度,“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意思是说,驿站使天下资源能汇聚一堂,这是元朝强盛的重要原因。
不过,以蒙古帝国幅员之辽阔,东征西伐之频密,仅有完备的情报传递制度,没有高效的情报收集制度,其军政要务也无法正常运转。
蒙古帝国通过两种方式收集情报:一种是直接的方式,比如直接派间谍或侦察兵去刺探情报;一种是间接的方式,比如在边境集市偷听敌国商旅的谈话,或者与过境的别国商旅交谈,或者收买敌国官员和平民,通过迂回的手段获得情报。至于情报的内容,则不仅限于军事方面,而是无所不包的。
德沃尼克在《情报工作起源》一书中说,在蒙古帝国的情报收集系统中,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原因在于,蒙古帝国的政策是善待商人,可汗们不仅保护贸易通道,有时还会直接资助商业组织。这种政策使其得到商人们的支持。为了与蒙古统治者保持友好关系,商人们会向他们提供大量信息。而商人们的优势在于,“他们控制了中国和中亚之间的一切贸易。他们清楚所有的道路情况。他们是精明的观察者,他们熟悉沿途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他们接触过许多官员。他们了解从波斯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通过商人收集情报,是蒙古帝国情报体系的独特之处。正是通过与花剌子模帝国有生意往来的商人,成吉思汗掌握了这个中亚国家的宗教情况,以至于在1218年时,派出了一个由穆斯林组成的庞大商队出使这个国家。当商队抵达花剌子模国的讹答剌城时,该城守将以蒙古商队是间谍为由,处死了几乎所有商队成员。这件事成为蒙古入侵中亚和西亚伊斯兰世界的导火索。
在边境集市搜集情报也是一个重要渠道,但这并不仅仅是蒙古人采用的方式。根据《金史》的记载,金世宗曾在1177年对宰臣说,宋人喜欢制造事端,违背盟约,不可不防备他们,因此,陕西沿边的榷场(指边贸市场),除保留一处,其他的都要关闭,“令所司严察奸细”。
与历史上所有国家一样,在蒙古帝国的情报收集系统中,侦察兵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可·波罗见识过蒙古大军的战斗编队。根据他的描述,蒙古军一般会派出四组侦察部队,每个部队由200名士兵组成。其中一组侦察部队充当先锋,他们比主力部队提前两天出发,去刺探敌军的动向、扎营位置等情况,其余三组在主力部队侧翼和后方警戒,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蒙古秘史》记载了一个例子:成吉思汗与王汗要一起攻打札木合。在与王汗的大军会师之后,两路人马顺着克鲁伦河行军。成吉思可汗派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三个人做先锋……在这些先锋的前面,还派出哨望(打探前路军情的分队)……刚要下寨的时候,在赤忽儿忽(地名)的哨望派人前来报告:“敌人来啦!”于是,成吉思汗就放弃了驻营的计划。
还有一个例子是,1220年秋,由于难以抵挡蒙古大军的攻势,花剌子模帝国统治者摩诃末仓皇出逃。于是,哲别和速不台率军追杀。他们一直追到里海附近,但最终还是让摩诃末逃掉了。不过,蒙古大军并没有急于返回,而是顺道侦察了里海一带的虚实。
蒙古人对军事侦察的重视,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关。古代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迫使他们不得不未雨绸缪,在迁徙之前,四处派人去寻找合适的落脚地。军事侦察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自然引申。
除了亲力亲为的军事侦察,蒙古人显然知道如何利用人的贪欲,收买敌国内部的人充当间谍。据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切希尔(Harold T.Cheshire)考证,蒙古大军入侵罗斯国(今俄罗斯)和保加尔国之后,曾雇佣这两个被征服国家的居民充当间谍。这些间谍经过里海潜入欧洲国家,收集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形势、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十字军东征后的兵力损失情况,以及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与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之间的斗争情况。
这些间谍刺探到的各个方面的情报,正是通过前面说的情报传递系统,传回了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当蒙古统治者了解到,欧洲人全然不知蒙古已入侵罗斯国,也不清楚蒙古的兵力情况,便制订了入侵波兰和匈牙利的计划。
不过,美国历史学家德沃尼克认为,速不台并没有雇佣平民充当间谍,而是从囚犯、商人和其他欧洲人那里收集的情报。
蒙古帝国在所有被征服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络。美国历史学家帕亚斯利安(Simon Payaslian)在《亚美尼亚史》一书中提到的一起历史事件,展示了蒙古帝国的间谍无孔不入的能力:1236年,蒙古帝国征服了中亚国家亚美尼亚。由于大汗窝阔台满足于已获得的战利品,他没有向这个被征服国家征收苛捐杂税。然而好景不长。从1243年起,蒙古统治者开始向亚美尼亚征收重税。1248年底时,不堪重负的亚美尼亚贵族酝酿叛乱。但他们的叛乱计划最终流产,因为蒙古人已提前获知叛乱消息。后来,叛乱组织者被拘押在哈剌和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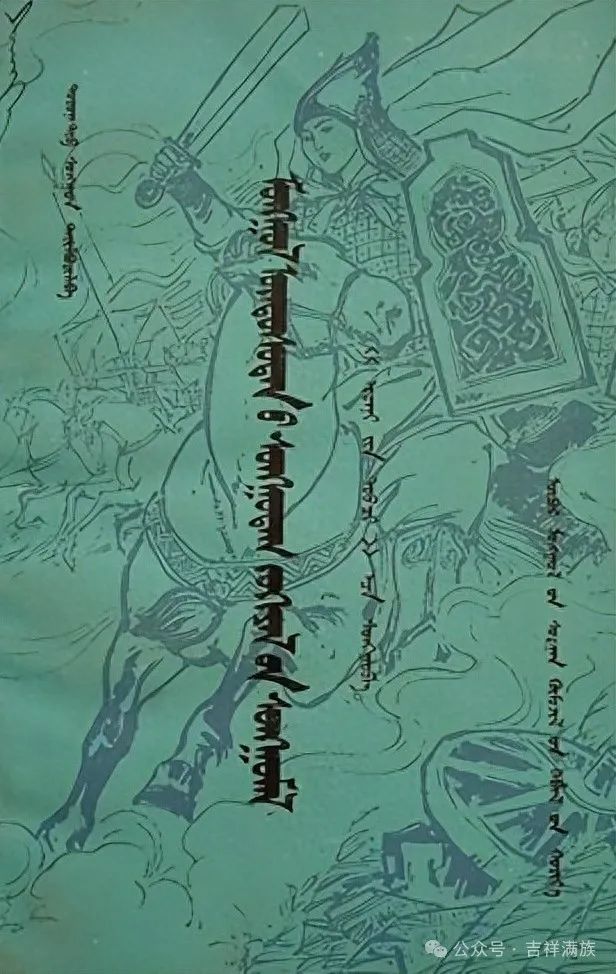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