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晓林,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蒙古人以天為最高信仰,“每事必稱天”,“無一事不歸之天”。對天的祭祀,可以說是蒙古禮俗的核心。關於元代的蒙古祭天,以往一些通論性著作中有一定涉及,較專門研究僅有日本學者今井秀周《蒙古的祭天儀式——從蒙古帝國到元朝》一文。但今井氏史料搜集未盡全面,且將不同的儀式混為一談,因此很多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本文擬重新梳理和辨析相關史料,探討元代蒙古人的祭天儀式,以及儀式中多元文化的交融互動。

蒙古国苏布日嘎峰国家祭天仪式
一、主格黎
主格黎祭祀,是史料所見蒙古人最古老的祭祀儀式。《元朝秘史》第43-44節述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兒死後(推測時間約為10世紀),庶子沼兀列歹被家人懷疑血統不純。沼兀列歹以前參加主格黎祭祀,這時從主格黎祭祀處被逐出。主格黎(ügeli),旁譯“以竿悬肉祭天”。以往學術界對其詞源、含義的討論已經很多,這裡不一一重複。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布裡亞特語中的üküli一詞,指祭祀中懸掛在竿上的帶有頭和四蹄的動物毛皮。這個詞無疑就是主格黎(ügeli~ ükeli > üküli),只不過詞義由祭祀名稱轉為專指祭品。因此《元朝秘史》旁譯所謂“以竿懸肉”,是對祭祀竿上祭品的泛稱。
有學者提出,既然逐出主格黎即逐出氏族,那麼主格黎祭祀的對象就不是天而是祖先。但是,僅這個理由不足以否定《元朝秘史》的旁譯。主格黎之類的祭祀,在古代阿勒泰語系民族中是頗為普遍的。這些儀式在祭天的同時,也祀祖先或其他神灵。
如辽国帝后在木叶山殺牲,体割,悬树,祭祀天神、地祇。10世紀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蘭(Ibn Fadlān)見到,突厥人在葬禮上杀马吃肉,將馬的頭、蹄、皮、尾悬于树上。13世紀到蒙古的西方旅行者柏朗嘉賓(Plan Carpin)、魯布魯克(Williamof Rubruck)以及亞美尼亞史家祁剌柯思(Kirakos of Ganjak)都記錄了蒙古人葬禮上悬馬皮于竿的儀式。
波伊勒指出,葬地已有獻給祖先的祭品,而竿上所懸馬皮的獻祭對象則是天。金國重五重九拜天,荐食物于架上,但是否祭祀其他神不清楚。而滿洲的情況有明確記載。清宮設立堂子祭天,悬肉于神杆,大祀當天也要在堂子設灵位祭祀祖宗。總之可以認為,在這些祭祀中,祭祀物件往往同時包括天、祖先,甚至還有其他神靈,將祭品高悬,其目的顯然是要將之奉獻給天。因此,主格黎本質上是祭天儀式,而祭祖的功能是次要的。
关于后金满洲春秋二季“举杆祭祀”的记载:
《满洲文老档·花喇荪恩都灵额汗》汉文译制版39


1932年牡丹江
满洲家庭院内的索罗神杆
在主格黎祭天儀式中,樹、竿、架都具有懸掛祭品的功能。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中,樹常被認為是與上天溝通的“世界之軸”(axis mundi)。《元朝秘史》第133節載塔塔兒部的駐營地名為“忽速圖失禿延”(Qusutu kitü’en)、“納剌禿失禿額捏”(Naratu 宨tü’en-e)。“忽速圖”意為有桦树的,“納剌禿”意為有松树的。“失禿延”、“失禿額捏”無旁譯。伯希和認為其詞根為《元朝秘史》第205、214節出現的詞“失禿額”(宨tü’e-),旁譯“抗拒”,因此釋宨tü’en為据点、城寨、堡壘。
但鮑培揭出居庸关过街塔洞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中的宨tü’en一詞,具體指佛像,因此宨tü’en的含義當為崇拜的物件、信仰的物件。其詞根當為宨tü-,《華夷譯語》的釋義是“倚”,現代蒙古語詞典釋為信仰、崇拜、信賴。神樹即可被稱為宨tü’en,因此塔塔兒部駐營的這兩個地名很可能與祭天儀式有關。這兩個地名的出現,應該是12世紀甚至更早前的事,折射出成吉思汗崛起前草原上的祭祀風俗。
主格黎祭祀在元代幾乎不見於直接記載,在現代也只在個別地區尚有留存。有學者認為,到13世紀以後主格黎一詞不大運用而似乎被其他名稱代替。筆者認為,既然明初《元朝秘史》能夠將其旁譯為“以竿懸肉祭天”,就表明主格黎祭祀在14世紀後半叶仍然存在。至於13世紀主格黎祭祀的行用情況,也有幾條旁證。
1221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人趙珙《蒙韃备录》記載,蒙古人:
“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遺制,飲宴為樂也”。
遍檢史料,正月初一、重午日皆非元代蒙古黃金家族的祭天時間。實際上,趙珙所記的是當時把持華北最高權力的木華黎(1170-1223)所行用的祭天禮儀。趙珙等南宋使臣還受木華黎之邀參加了重五拜天之後的打毬与宴飲。木華黎,蒙古札剌亦兒氏,1217年被成吉思汗委任為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全權處理華北事務。木華黎祭天的正月一日、重午兩個日期,都屬於金人遺制。《三朝北盟會編》記女真禮俗雲:
“元日則拜日相慶,重午則射柳祭天。”
《金史》載:
“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其制,刳木為盤,如舟狀,赤為質,画云鹤文。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
金國荐食于高架上的拜天禮,與蒙古人以竿悬肉的主格黎儀式頗為相似。燕京地區的蒙古統治者木華黎接受金人遺制,也許有政治上統禦金朝故地的考量,但儀式相似、文化相通應該是其重要基礎。
关于皇太极射柳的事,见下文文末:
《满洲文老档·花喇荪恩都灵额汗》汉文译制版33

契丹射柳
射柳在辽金元清一直延续
东北君补充:满洲、蒙古、朝鲜都有敬柳习俗。在满洲神话《佛多妈妈与十八子》中,柳神与石头神的结合,诞生了今天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的众多民族。所以在今天蒙古、达斡尔等民族的敖包祭祀中,仍常用柳枝、柳树立于敖包石块中。
元世祖至元五年,中書省規定了各路官府每年各項祭祀的支出錢數,其中包括“重午(即端午節)、重九(即重陽節)拜天節”。金國是否在地方各路舉行拜天,惜無記載。至元五年的這條關於祭祀官費的規定,很可能是對蒙古前四汗時期華北各路的舊例加以承認。而華北各路的蒙古官員,當然要主持和參與重五重九拜天。對於他們而言,金国拜天遺制也是一種主格黎式的祭祀。但不久,中書省就下令革去各路官府的重五重九拜天,《元典章》載:
至元九年(1272)正月,中書吏禮部:
承奉都堂鈞旨判送:“戶部呈:為本路年例祭祀錢數,再行擬定必合祭祀事理。連判申呈。”本部照得:祭祀社稷、風雨雷師,釋奠至聖文宣王,立春日,俱系合行事理。其重五、重九拜天,據《集禮》所載,金人立國之初,重午拜于鞠场,重九拜於都城外。此系亡金体例,擬合革去。呈奉都堂鈞旨:“准呈。移關戶部照會者。”奉此。
以往學者把這次革去的拜天禮理解為國家級的祭祀。這是不確切的。如果要改變國家層級的祭天,勢必要聖旨裁奪。但這件公文是都堂鈞旨,目的是規範地方官府的祭祀經費。至元九年革去各路拜天,應理解為元朝制度建設過程中禮制規範化的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中書省針對的是各路官府,沒有干預民間祭祀,因此蒙古人中存在主格黎祭天的可能性很高。
結合《蒙韃备录》、《元典章》以及《元朝秘史》,我們可以推測,元代蒙古人仍然有主格黎祭祀的習俗。一些在華北的蒙古人至少在1221-1272年之間曾受到金国拜天遺制的直接影响。縱觀史料,主格黎祭祀出現于大蒙古國建立之前,在大蒙古國建立後是一種非國家級的祭天儀式。
二、洒馬湩
在大蒙古國、元朝國家層面,洒馬湩(馬奶子、馬乳酒)是祭天儀式最重要的特徵,而以竿悬肉的儀式、主格黎之名皆不見於記載。
洒馬湩祭天儀式的雏形出現於成吉思汗時期。《元朝秘史》第103節記載:
年輕的帖木真(成吉思汗)遁入不兒罕山逃過仇敵追殺後,感不兒罕山遮救之恩,他念誦了一長段祝詞,解帶掛在頸上,摘帽掛在手上,一手捶胸,向日跪拜九次,將馬奶子洒奠了。
波斯文史書《世界征服者史》與《史集》記載,成吉思汗在決定出征花剌子模、金国之前,都曾獨自登上山頭,解帶掛在頸上,脫帽,以臉朝地(跪拜),祈禱上天护佑。天給予成吉思汗护佑、福荫,是汗權的源頭,也是大蒙古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在儀式中,成吉思汗本人直接向天祝告祈祷,無需借助萨满巫師。有威望的巫師闊闊出(稱號帖卜·騰格裡)在成吉思汗即位後被處死的事件,標誌著成吉思汗將汗權、巫權合一,統合了對天命、天意的解釋權。祭天宣示了天對汗的直接護佑,成為國家層面最重要的禮儀。到元代,灑馬湩祭天也是“皇族之外,無得而兴”。將祭天儀式限定于黃金家族內,是將天命與成吉思汗血統捆綁在一起。
大蒙古國的祭天儀式之所以是洒馬湩而不是主格黎,我們應該考慮三重因素。第一,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諸部可能已有不止一种祭天仪式。第二,洒馬湩儀式可能對於成吉思汗而言有特殊意義。成吉思汗年少時,父親遇害,部眾散去,部众散去,母亲参加烧饭祭祖时没有分到祭余的胙肉,被氏族拋棄,生活貧苦,再未參加氏族的祭祀活動。
這種境況有可能促使成吉思汗家族採用新的儀式。第三,新儀式可能与成吉思汗建立新政權、新意识形态有关。匈奴、突厥、回鶻、蒙古等北方民族皆有“天”(tengri)的觀念,但“長生天”(蒙古語muggke tengri)觀念則是蒙古人獨有的。在《元朝秘史》全書中,“騰格舌理”(天)用例很多,但“蒙客·騰格舌理”(長生天)在成吉思汗即位以後才出現。長生天觀念適應於新興的大蒙古國大汗的至高權力。灑馬湩是祭祀長生天的儀式,是天授汗權的直接象征,是大蒙古國意识形态的最核心表徵。

春节前夕,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伊和诺尔苏木赫希格一家,冬季在雪敖包前祭天。
成吉思汗子孫的灑馬湩祭天,主要在春秋二季,但具體日期不固定。关于蒙哥汗祭天,《元史》載,
宪宗二年(1252)秋八月八日,祭天於日月山;四年(1254),會諸王於顆顆腦兒之西,乃祭天於日月山;七年(1257)秋,駐蹕于军腦兒,酾馬乳祭天。
魯布魯克記載,
蒙哥汗四年五月九日(1254年5月26日),聚集所有的白馬舉行祭祀,把新忽迷思(馬奶酒)洒在地上。忽必烈在做藩王時,率麾下洒白馬湩祭祀。
張德輝《岭北紀行》載,
“每岁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
姚從吾先生指出,蒙古祭天日期不固定,張德輝1248年在忽必烈帳下所見祭天恰好在四月九日,引起了他過分的注意。忽必烈即位後,中統二年(1261)四月八日,躬祀天於開平(元上都)西北郊,洒馬湩以為禮。馬可·波羅記載,七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大汗取白牝馬之乳,洒於地上。忽必烈之後的情況,最有名的一條史料是載于《元史·祭祀志·國俗舊禮》,其曰:
每歲,駕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謂之洒馬妳子。用馬一,羯羊八,彩段練絹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覡及蒙古、汉人秀才達官四員領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賽者。”礼毕,掌祭官四員,各以祭幣表裡一與之;余币及祭物,則凡与祭者共分之。
這是記錄洒馬湩儀式的最詳盡的一條史料。《元史·祭祀志·國俗舊禮》條在《祭祀志》最末,很可能是《元史》二次纂修時補入的,反映的應是元中後期的情況。這個儀式中不僅拜天,而且祭祀太祖成吉思汗。今井秀周認為,只祭成吉思汗而不祭其他祖先,說明蒙古人將成吉思汗視為一位“几乎与天神并列的大神”。這種說法有一定合理性。另外還可參考中原傳統的尊祖配天觀念,即祭天時以王朝創始者(太祖)為配侑。此處的元末洒馬湩儀式受中原傳統禮制影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六月二十四日仪式中,皇帝并没有亲临。今井秀周认为,忽必烈以后的皇帝因信仰藏传佛教,对萨满教的洒马湩祭祀失去了兴趣。今井氏显然没有看到其他史料。《元史·顺帝纪》载,后至元三年(1337)秋七月丁未(九日),“车驾幸龙冈,洒马乳以祭”。与这条史料相关的是后至元六年周伯琦记载,在上都,每年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北方陵园,指漠北起辇谷元朝皇帝陵寝。这都是皇帝亲自主持的仪式,而且也告诉我们,洒马乳不仅祭天,还祭祖先。
今井秀周只看到了《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这一条史料,误以为这是忽必烈以后唯一的洒马湩祭祀,于是推论从大蒙古国到元朝洒马湩祭天的时间从春季改为夏季。应该注意的是,春季洒马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初尝忽迷思(马湩)”,是每年牝马初产乳的庆典节序。元中后期春季洒马湩不见于记载,恐怕只是因为史料匮乏,不能断言其事不存在。搜罗其他史料,我们发现,元中后期夏秋季节至少有三次洒马湩祭祀,即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七日(或九日)、八月各一次。后二者又见熊梦祥《析津志》所记:
上京于是日(引者案,七月七日)命师婆涓吉日,勑太史院涓日,洒马戾(疑为“妳”字之讹),洒后车辕軏指南,以俟后月。……是月(引者案,八月)也,元宰奏太史、师婆俱以某日吉,大会于某处,各以牝马来,以车乘马潼。
关于八月的祭祀,《析津志》又记“于中秋前后洒马妳(nǎi)子”,顺帝时杨允孚亦记:“每年八月开马妳子宴,始奏起程。”七月的祭祀与望祭北方陵园有关,八月的祭祀是起程离上都前的大会,皇帝都亲临主持。六月二十四日的祭祀皇帝不参加也不足为奇,说明这次祭祀规制不是最高的。
今井秀周又认为,史料漏记了六月二十四日洒马湩的祭场、祭坛。他举证匈奴、乌丸、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北方民族祭祀皆围绕着树或木举行,从而推测蒙古洒马湩祭祀仪式中竖立木柱,洒酒是围绕着木柱进行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主格黎、洒马奶仪式合二为一了,但缺乏史料支撑。洒马湩祭天仪式的雏形可追溯到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独自登山,没有竖立木柱的迹象。因此我们仍然认为,主格黎、洒马湩是两种仪式。

马奶酒
三、祭天仪式中的多元文化
随着蒙古迅速扩张,治下包含了各种文化、宗教。蒙古人接受或参与了其他文化传统的一些祭天仪式,同时蒙古的祭天仪式也受到多元文化影响。
蒙古人将各宗教的祈福祝祷仪式也视为告天、祭天。元代圣旨、令旨、官府公文中,要求各类宗教人士为皇帝告天祈福祝寿。成吉思汗圣旨中称临济宗高僧中观、海云为“告天的人”。元武宗任命藏僧雍敦朵儿只班(g.Yung ston rDo rje dpal,1287-1365)为“诸祀天咒士之长老”。不过从史料来看,蒙古人不直接参与这些仪式。
蒙古人直接参与的一种祭天仪式是中原汉文化传统的郊祀。元代第一次郊祀,是世祖至元十二年遣官于大都南郊祭天。但元代皇帝亲郊很少,仅有文宗一次,顺帝两次而已,大部分时候都是遣大臣代祀。代祀南郊的大臣一般是当朝宰相,大多是蒙古人。成宗朝右丞相蒙古人哈剌哈孙甚至直接参与了郊祀仪式细节的制定。元朝郊祀中,“其牺牲品物香酒,皆参用国礼”,显然是蒙古人参与的结果。
蒙古传统的祭天仪式中出现了汉文化因素。元中后期六月二十四日洒马妳子祭祀,“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洒马湩祭祀在元世祖时期还是只有皇族才能参与的,而到元中后期出现了汉人秀才与蒙古人共同领其事的六月二十四日洒马妳子仪式。这是蒙古、汉文化融合的表现。
金国拜天礼俗对蒙古人造成了影响。蒙古兴起于金代,受到金国文化影响。在祭天仪式方面,今井秀周发现,北方游牧民族祭天的朝向大多是西向(东北君:满洲人的西炕也是摆放祖先祭祀之地),唯有蒙古南向拜天,这很可能是受了金国南向拜天的影响。蒙古前四汗时期到至元前期,在华北的蒙古人施行重五重九拜天,体现出金国礼俗的影响。至元九年,各路官府停办重五重九拜天,但金国拜天礼俗从另一方面影响了蒙古人,此即射柳击毬(马球)活动。
在历史上,金代始固定于重五重九拜天礼毕当天“行射柳击毬之戏”。蒙古攻占金中都燕京之后,很快便熏染其风。1221年重五日,木华黎国王曾邀请南宋使臣一起打毬宴饮。华北世侯张柔之子张弘范(1238-1280)作《射柳》《打毬》二诗,反映出13世纪中叶蒙古统治下华北达官贵人有此风尚。直到元末,在大都、上都、扬州等地,上层统治者射柳击毬仍蔚然成风。《析津志》载:
“击球者,(今)[金]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常于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诸王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上召集各衙万户、千户,但怯薛能击球者,咸用上等骏马,系以雉尾、缨络,萦缀镜铃、狼尾、安答海,装饰如画。……如镇南王之在扬州也,于是日王宫前列方盖,太子、妃子左右分坐,与诸王同列。执艺者上马如前仪,胜者受上赏;罚不胜者,若纱罗画扇之属。此王者之击球也。其国制如此。”
马祖常《上京书怀》《次韵端午行》二诗,皆咏及元上都重午射柳之戏。《元宫词一百首》之一云:“王孙王子值三春,火赤相随出内闉。射柳击毬东苑里,流星骏马蹴红尘。”火赤,当指火儿赤,蒙古语义为持弓矢者、箭筒士,是怯薛宿卫的一种。这些记载都说明元代蒙古上层极为热中重五重九射柳击毬。这是金国礼俗留下的间接印记。
 、
、
契丹人打马球
盛行于唐宋辽金元的马球在清康熙后,逐渐消失。但将射柳与击马球结合的祭祀活动,主要流行于辽金元和清初。
四、结 论
总之,蒙古从漠北草原崛起,内部有着不同的部族、阶层。而在疆域广阔的元朝,多元文化交会与交融是突出的现象。新兴政权在文化建设中,对官方仪式进行了规范和塑造。这都导致元代蒙古人祭天仪式体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
蒙古传统的祭天仪式,主要有主格黎与洒马湩两种形式,二者在元代都与其他文化产生了互动。
主格黎是以竿悬肉祭天的仪式,较普遍地存在于突厥、契丹、女真、满洲等民族中。主格黎与契丹割牲悬树、女真荐食于架的拜天仪式类似,所以1221-1272年之间在华北应该有一些蒙古人曾施行重五重九拜天遗制。至元九年元朝中书省革去诸路官办的重五重九拜天,金国拜天礼对官方祭祀的影响中止。在元代非官方层面,蒙古人可能仍然有主格黎的习俗。重五重九拜天礼虽然停止了,但当天的射柳击毬活动仍然成了元代上层蒙古人的风尚,这可以说是金国礼俗的影响。
洒马湩祭天,是元代最高级别的国家祭祀,其雏形是成吉思汗的洒马湩祭天。洒马湩祭天仪式的举行时间集中在两个时节,一是四、五月,二是六、七、八月。洒马湩的主要参加者是皇族宗亲,强化了成吉思汗血统得天命的神圣性。《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所记六月二十四日洒马妳子,是元中后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祭祀,皇帝本人不参加,蒙古大臣与汉人儒士一起领其事,这是文化交融的结果。
蒙元王朝将各宗教的祝祷仪式视为告天,兼容了多元文化,扩展了祭天仪式的范围。元朝蒙古上层人士在郊祀中主祭,并将一些蒙古“国礼”因素糅进了仪式中,是蒙古文化对中原礼制的渗透,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 上一篇: 1925年纪录片丨日本人拍摄的赤峰巴林右旗《蒙古横断》
- 下一篇: 蒙古与高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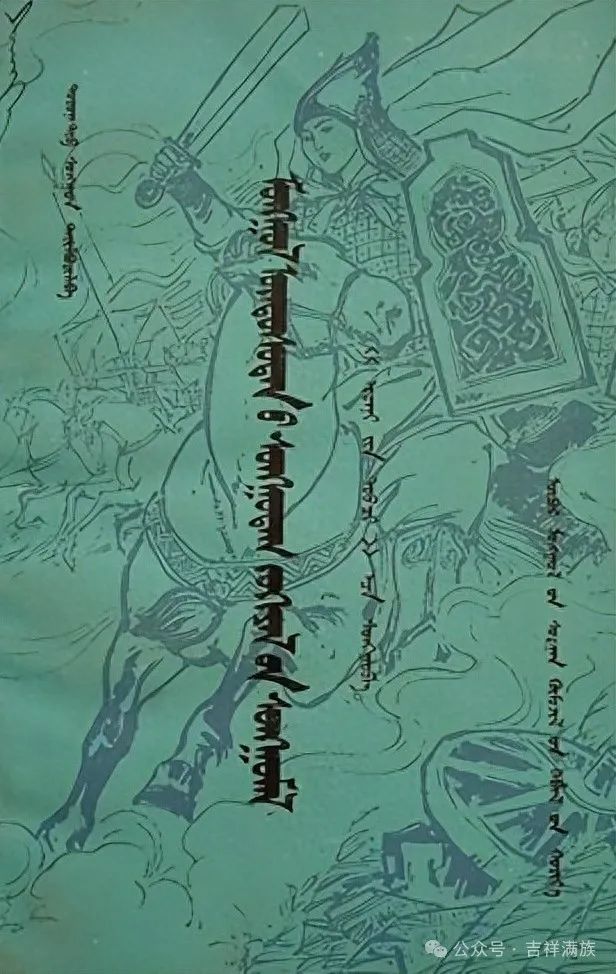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