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默特蒙古生息于土默特地区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对其五百年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际遇,史学界已有专文论述,这里仅就土默特蒙古姓氏的演变作一点肤浅的探讨。据《辍耕录》载,蒙古氏族计有七十二种,如瓮吉剌歹、郭儿剌思、伯要歹、忽神、兀鲁歹、秃别歹、外剌歹等等,绝无与《百家姓》或者《千家姓》所载相同者。笔者生于斯,长于斯,颇留意有关本地区之著述和资料,发现土默特蒙古之有汉姓或汉式姓氏。不过是近百年以来逐渐出现的。这一社会现象,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探讨其由来、演变,或许对本地区的历史乃至民族、民俗诸学科不无裨益。因而不揣冒昧,写此短文,以为引玉之砖,敬请识者指正,并盼补充。
一、蒙古族人名的变化
在谈土默特蒙古族姓氏之前,有必要对其人名的变化稍作叙述。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土默特蒙古族的人名,完全是蒙古式的,不受其它民族或其它文化的影响,如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其兄衮必里克,其弟拉布克、巴雅思哈勒,其子孙都隆森格、布延、把林、博达锡哩、陶克陶、楚鲁克、把汉那吉、那木儿,其臣思达陇囊素、阿尤其、图古齐、宝迪苏舍迪齐、敖其赖古彦等等,均为蒙语名字,即使出边投奔土默特部的汉族,凡改名者,亦一律为蒙语名字,如李自馨改名为巴哈毕斜气,赵全之女名簿合图等。象永谢布前期封建领主亦卜刺这样伊斯兰化的名字是绝少的。以后,土默特蒙古分别受到藏、满、汉等族的影响,人名凡三变,简述如下。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以阿勒坦汗为首的土默特部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教逐渐成为全民的宗教信仰。孩子出生后,多有请喇嘛命名者,于是土默特蒙古开始出现藏语人名,如道尔吉、扎布、扎木苏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此其一变。
1628年,土默特部降附后金(即满洲),至1636年清廷编土默特部为左右两翼,每翼一旗,完全按清制设官牧民,土默特改为满洲的附庸。由于满族系统治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土默特蒙古的影响甚为深刻,约当清朝中叶,土默特蒙古的风俗习惯在不少方面已经满化,如服装多改蒙古袍为半截袍,妇女的发式改链椎为“两瓣头”,鞋改蒙古靴为“高底鞋”;其它如礼仪方面的满式请安,称谓方面改“必力更”(嫂子)为姐吉,称姐姐为“格格”(再后简称为“格”)等等。随着风俗的满化,人名亦随之一变。满洲人除以满语命名者外,多有以汉语起吉祥如意之名者,为福临(顺治皇帝)、富昌、吉福、永德、瑞良(均为绥远城将军)、福长、普泰、安祥、文保、恩铭(均为绥远道员)等等。土默特蒙古受其影响,有的起满语名字,如阿慎阿、伊精额、喜蒙额、札格胜阿等等,更多的则起满式汉语名字,如德胜、泰顺、锡龄、国安、经济、吉祥(均为佐领)、福承、瑞恒、凤林、瑞春、庆春(均为骁骑校)等等,此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民国年间。此其二变。
从康熙、雍正两朝开始,清廷逐渐采取开垦土默特牧场的政策,乾隆朝开垦达到高潮,大批边内农商之民蜂拥出边垦殖、经商,人口越聚越多,为土默特蒙古的十数倍,土默特地区遂形成蒙汉杂居区,大多数村庄汉族占绝大多数,交际交流几乎完全为汉语。经过长时间濡染、影响,到清末,土默特蒙古族的民族语言已处于沦失的边缘,其风俗习惯亦掺入许多汉俗,即以人名言,蒙古族起汉名者逐渐多起来(平民尤多),如光绪年间的三来柱、兰锁子、银柱、福柱、胖挠子,民国初年的明才、存旺、才才、海牛、成成、安安等等。到1930年以后,土默特蒙古族多数人均已取汉名,并冠以姓氏。此其三变。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土默特蒙古之人名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蒙语人名——蒙藏相间——蒙、藏、满相间——汉、蒙语人名。这一变化过程,纯系蒙古族人名的“汉化”,而汉化的结果之—就是采取用汉姓或汉式姓氏。解放以来,部分蒙古族已抛弃汉语人名,而以蒙古语人名代替之,表明其民族文化传统在恢复和弘扬。

二、蒙古族姓氏沿革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土默特蒙古族的姓氏有如下一百一十余种:
云、荣、张、章、王、李、赵、孙、贺、郝、谢、康、丁、卜、补、包、巴、苏、常、昌、田、任、景、万、殷、都、孟、伊、奎、吉、锡、富、傅、伏、满、文、姜、丰、穆、亢、吴、武、黄、肖、经、高、朱、韩、贾、刘、白、马、金、陈、何、徐、境、墨、胡、恒、廉、连、石、游、成、杨、林、玉、俞、奇、齐、祁、魏、洪、通、克、多、杜、焦、柴、霍、薛、曹、曾、乌、兰、宋、潘、方、古、鲍、蒋、佛、全、南、松、钱、周、冯、明、牛、银、蔺、姚,阎、薄、钟、春、安、郭、郑,夏、元。
如此众多的姓氏是怎么演变来的呢?《通志·氏族略序》说:古代“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三代(按,指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这是就汉族而言的,蒙古族与此不尽相同,但在“别贵贱”这一点上则颇为一致。如成吉思汗出身的黄金氏族曰孛儿只斤,其姓为奇渥温。黄金氏族系贵族,其后裔极重视自己的“所由出生”,因而其姓氏一直保留至今,如鄂尔多斯各旗贵族取“奇渥温”之奇为姓,土默特等旗黄金家族后裔取“孛儿只斤”首字的同音或同声字卜、薄、包、宝为姓。但是,古代蒙古族似乎更重视氏,即某人出自某氏族,用以“别贵贱”,别“所由出生”。如《蒙兀儿史记》载:“(木)合黎,札剌亦儿氏”,“孛罗忽,许兀慎氏”,“者勒蔑,札儿赤歹兀良孩氏”,“者别,别速惕氏”,“伯颜(丞相),你出古惕巴阿怜氏”。元朝以后,不仅以血缘关系结成的蒙古社会经济单位——氏族早已打乱,即使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千户制也已不复存在。退出中原的蒙古族几经战乱,重新组合而成新的部落(也有称作鄂托克的),尽管氏族的残迹仍然留存于蒙古社会中,但毕竟已不占重要地位。因而十五世纪后期到十六世纪,除个别原来声势显赫的望族外,见于史籍的对人的称谓,一般已形成这样的模式:某某部落的某某人,《蒙古源流》等书的记载即如此,例如“卫刺特·扎哈明安之浩海·达由”,“蒙郭勒津之蒙克拜”,“永谢布之伊斯满太师”,“土默特·茂明安之多郭兰阿忽勒呼”,“土默特·杭锦之阿勒楚赉”等等。这种称谓方式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定鼎北京以后,蒙古族的称谓有所改变。对官员的称谓,上级部门(如理藩院)对下的称谓一般是“地区+部(旗)名+职衔+名字”,如“归化城土默特左翼都统古禄格”、“归化城土默特参领达尔玛”等等;如在本旗之内,则只称职衔与名字,如“佐领阿拉布坦”、“骁骑校仁钦道尔计”等等。对披甲、兵丁则称“某佐领下披甲某某”,“某佐领下某人”。到清末,如前所述,不少蒙古族采用汉名,这一时期的称谓再度变化,一般称作“蒙古某某”,如“蒙古兰锁子”, “蒙古明才”等等,名字之前并不冠以姓氏。
土默特蒙古采用汉姓或汉式姓氏,约始于晚清,即十九世纪后期。据同治十二年(1873)的《重修毕齐克齐城隍庙碑记》载,该庙地基由蒙古何姓施舍,修庙董事之一为“蒙古甲头任从”。由此可知,至迟在1873年部分土默特蒙古族已有汉姓或汉式姓氏。但是,使用这种姓氏则较晚,大多始于民国初年,盛于二十年代以后。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土默特两翼参领、佐领、骁骑校、前锋校表内共计一百四十余人,仅有一人名字之前冠以姓氏(见附表一)。大约当时部分人虽已有汉姓或汉式姓氏,但在正式场合(如官场活动、签定契约等)绝少使用,只有个别人例外,如1907年随棚考试的蒙古文童巴文峒,同年贻谷奖励办垦出力人员名单中的云隆。中华民国建国后,土默特蒙古族使用汉名并冠以汉姓的逐渐多起来,到二十年代已普遍使用汉姓或汉式姓氏。如1923年至1925年土默特旗旅京学生四十六人(见表二),其中三十八人有姓、名和字(如奎璧字子璋,吉雅泰字岱峰,李裕智字若愚,赵诚字璧臣)。再如1931年土默特旗职官表内共列一百一十—人,有汉姓者约占40%(见表三)。那么,土默特蒙古族的汉姓或汉式姓氏是怎样被采用或确定的呢?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仅就已了解到的情况分述如下。
1、以氏族、部落名称首字为姓:
据清编《土默特旗志》载,土默特蒙古有孛儿只斤氏、巴拉格特氏、云硕布氏、乌梁汉氏、纳(拉)氏等。孛、巴为氏族名称,其后裔取首字为姓氏,如和林格尔县台吉营子的卜姓、包姓,包头一带的巴姓即属此类。云、乌为部落名称,大约在明末的社会大动乱中,部分永谢布、乌良哈等部落的属民流落于土默特地区,成为土默特两翼之属众,其后裔不忘自己的“所由出生”,遂以部落名称的首字为姓氏,土默特蒙古的部分云姓(如美岱召一带)即属此类。
2、以父名之首字为姓:
土默特蒙古族以父祖之名首字为姓者颇多,如参领贺色畚之子孙以“贺”为姓,参领万才之子孙以“万”为姓,总管满泰之子孙以“满”为姓等等。此外,有的蒙古族本无汉姓,在社会交往中,彼此初次见面,往往相互询问“贵姓?”蒙古族遂名字之首字漫应之,久而久之,遂以此为姓,如锡琨、常龄,均系满式名字,本人及子孙竟以“锡”、“常”为姓。
3、因职业而定姓氏:
土默特蒙古族的姓氏,有的因职业而定,如毕克齐香坊巷之马家,其先人曾长期从事牲畜交易业,并任当地牲畜交易市场(即牙行)头目,凡交易,须其人主持方可成交,历时既久,买卖双方渐呼之为“马头儿”或老马,于是其后代遂以“马”为姓。
4、因讹传而定姓氏:
目前仅发现一例。现居武川县西红山乡大公村、小公村的蒙古族,系辅国公剌麻札布之后裔,而剌麻札布的先祖为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故而辅国公一系为土默特之黄金氏族。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美岱召一带至大青山后的牧场,为把汉那吉及博达锡里之领地。有人根据历代辅国公死后均归葬美岱召祖坟的事实,推测剌麻札布与把汉那吉或博达锡里有渊源关系。但是,在美岱召和大公村一带,民间传说美岱召的太后庙为辽代萧太后之庙,并由此演绎出辅国公一系为萧太后之后人。到剌麻札布的七世孙,误信讹传,竟以“萧”为姓,迄今未变。
5、相互影响而定姓氏:
民国初年,土默特蒙古有的已有汉姓或汉式姓氏,有的则无。无姓氏者效法已有姓氏者,彼此间或因亲戚,或因关系密切,或张或李或王定为姓氏,这种现象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尤多。如常黑赖村李明旺本无姓氏,入学注册时,先生以为“应该有个姓”,他急切间问其表兄姓什么,答曰“姓李”,于是他便说:“那我也姓李吧”,自此遂以李为姓,“姑舅姓甚我姓甚”一时传为笑谈。诸如此类的事,并非绝无仅有,如在编查户口时无姓氏者为了“有名有姓”,向亲朋故旧借某一姓氏为己姓者往往而有。
6、因特殊需要另定姓氏:
这类情况多发生在革命干部中。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因工作需要或别的特殊原因,往往有改换姓氏者。如徐史、李振华、黄静涛原先分别姓云、连、丁,参加革命后始改为现在的姓氏。另外如土默特总管荣祥之长子荣钟麟,抗日战争时曾赴延安学习,—度改姓名为胡铁麟。
7、其它:
除上列诸种情况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民国以来有抱养他人婴儿为子嗣者,个别人长大后有以生父之姓为姓氏的。还有一些穷苦蒙古,被迫顶替富家子弟充当壮丁最后竟以被顶替者的姓氏为己姓。
以上仅为初步了解到的情况,许多蒙古族汉姓或汉式姓氏的来源尚不清楚,例如赵姓,会不会是由昭那斯图、昭日格图之类的名字演化而来?王姓有无可能系取自旺吉拉、旺亲之类名字的首字?苏姓或许与苏都那木苏亚拉图一类名字有关?这不过是一些推测,一时尚难找到确证,故而只得暂付阙如。
三、关于云姓
土默特蒙古族姓云者甚多,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这—社会现象的呢?黄静涛先生在《土默特历史问题丛说》中认为:“我以为归化城土默特人姓云,偶然性很大,而且是较晚时候才出现的,其普遍地出现,甚至是在民国以后。”事实近乎如此。清编《土默特旗志》的《职官表》共列一百四十四人,无一姓云者。(见表一)在土默特历史文献档案中,仅见云隆为云姓(1907年),此外仅知的云姓为1911年前后的辛亥革命志士云亨(嘉惠),彼时土默特蒙古是否还有姓云者尚不清楚,但这起码表明,清末土默特蒙古姓云者并不多见。民国以后,云姓渐多,例如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就读的土默特青年共四十三人,其中云姓十五人(按,本地云、荣发音相同,且同—家族兼有云、荣二姓,为统计方便,姑且视为一姓),占35%(见表二)。到1935年,土默特旗呈报蒙藏委员会的《职官表》共列一百三十四人(兼职重名者不计),有汉姓者六十七人,其中云姓二十二人,占32.8%。(见表四)可见时代愈晚,云姓增加愈多。
关于云姓的来源,《土默特历史问题丛说》指出:“客列亦惕氏速哥、拔实二人……他们的先人或后人均被封为云国公。速哥辖治八达岭以北及山西地区,这已经很接近土默特的居地,那个云国公的封号,不能说,绵延开去一定不能成为一种族姓的依据。”此说为我们探讨云姓的来源,提供了一种思考的线索。然而,时代既远,又无资料佐证,一时尚难稽考。也有人以为,历史上以地名为姓氏者不乏其例,土默特地区历代曾有云中,云内等州郡建置,部分蒙古族的云姓或许来源于此。这也是一种推测,不足为据。
当然,也有人曾确切指出过云姓的来源,如荣祥先生在其《土默特沿革》中说:永谢布“是土默特部的族姓,汉字书中有写作永邵卜的,也有写作云石堡、云社堡、永谢堡的……几百年来,呼和浩特土默特蒙古人自己用汉字写族姓时都是写云硕布,决不用别的写法”。又说,土默特“十二分部里,有七个部分是以云硕布氏的氏族人口为主体而编制起来的,所以叫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又叫多伦土默特……其余五个分部是由少数云硕布氏和各种氏族人口,其中包括许多汉人混合组成”。云社堡村“正是永谢布之七鄂托克的适中地方,也应是这个部族的总办事处”。荣先生的上述论断,在下列几方面难以成立。
首先,永谢布并不等于土默特。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大量史料表明,达延汗时期,其右翼三个万户为鄂尔多斯、土默特和永谢布,三者并列,不存在等同或替代关系。把土默特人说成永谢布人,进而把云硕布氏定为土默特蒙古的族姓,没有史实依据。因而如黄静涛先生所说:“说土默特人普遍姓云就是永谢布氏的简化云云,恐怕就难于成立”。
其次,所谓“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又叫多伦土默特”,恐怕是搞错了。据《蒙古源流》等书记载,永谢布万户是由大永谢布、阿速特和喀喇沁组成的,“永谢布七鄂托克”应为“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或“喀喇沁七鄂托克”,其领主为阿勒坦汗之弟巴雅思哈勒(昆都伦汗,即老把都),其驻牧地在张家口以北,与朵颜卫兀良哈相邻。而多伦土默特即《明史》所谓多罗土蛮,其领主为阿勒坦汗之叔父阿尔斯博罗特及其子孙,驻牧地在穆纳山(乌拉山)以北,系十二土默特之一部,与喀喇沁是属于不同万户的两个部落。故而所谓“用氏族称呼,就叫作‘永谢布之七鄂托’,用部落称呼便叫作‘多伦土默特’”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
再次,云社堡村既为云硕布氏的“总办事处”,那么其居民当然应是永谢布之属民,自应如荣老先生所说,他们该姓云硕布氏。然而实地调查的结果恰恰相反,世居该村的蒙古族并不姓云,而是姓李。据村中老年人讲,李姓之始祖,由东北出征西北,与另外四人结为安答(即结拜弟兄),凯旋后路经此地,看到水草丰美,五人遂留居于此。实地勘察李家祖坟结果如下:数十亩大的坟园,最北边为并排五个坟丘,以后所埋均为老三之后代,坟地中间因水冲沙压,已难辨出坟丘,但从第一代到最南的坟墓,共安葬约二十代人,足证李姓确系原居该村之蒙古族,亦说明故老相传不谬。还有需要说及的一点是,云社堡仅仅与永谢布或云硕布谐音,并不能说明就是云硕布氏的“总办事处”。正如云石堡是明朝的一个边防城堡一样,云社堡大约仅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村名,这在土默川并非绝无仅有,例如杨家堡村虽为汉语名称,但并不影响她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村庄(清末以来始渐为蒙汉杂居村)。以堡为名的村子还有一些,如毕克齐的前身名为聚安堡,名为里堡的村庄也有数个。因此单凭谐音而无其它佐证的附会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土默特蒙古的云姓是怎么来的呢?笔者作过一些调查,兹将结果分述如下。
1、由云硕布氏演化而来:
明代土默特部与鄂尔多斯、永谢布并为蒙古右翼三万户,关系密切,特别是阿勒坦汗时期,关系更加密切,如1550年右翼蒙古进军明都北京的“庚戌之变”,有永谢布骑兵参加;阿拉坦汗用兵西海,永谢布人参与其事,并留大量部众驻牧于彼(清朝以来青海之雍熙叶布即其后人);1570年以后,永谢布之大小领主跟随阿拉坦汗接受明朝封授的官职(都督同知到百户)并参加马市交易。《土默特历史问题丛说》指出,在永谢布之内有土默特人。反过来说,土默特之内也可能有永谢布人(如土默特的畏吾儿沁部就与永谢布前领主亦卜剌颇有关系),但当时各部延纳友邻部落属民是不容许的,因而即使相互包容属民也是极有限的。明末,右翼诸部历经战乱,永谢布、喀喇沁首先被林丹汗击败,其部众溃散,这大约就是清朝以来没有以永谢布之领主及其部众建旗编佐的原因。永谢布之部众逃奔土默特者有之,这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部分蒙古族清初由呼和浩特附近之哈拉沁迁徙至彼的情况是一样的,故而清编《土默特旗志》载有“云硕布氏”。这部分永谢布人不忘其先,以云为姓乃情理中事,诚如荣祥先生所说,他的家族即为云硕布氏。大约还有一部分云姓亦如此,但土默特如此众多的云姓,绝非全系永谢布人则可以肯定。

2、以父祖之名首字为姓:
土默特蒙古的云姓,有的系取自父祖名字之首字。如把什村云万虎之先人名叫云吉布,曾任土默特右翼嘎勒达(参领)。本世纪初,蒙古族渐有采用汉式姓氏者,云吉布之后裔遂以“云”为姓氏,目前已历四代而不变。
3、取“容”的同音字为姓:
自十八世纪前叶清廷大规模开垦土默特牧场以来,大批汉族徙来垦殖,蒙汉之间因土地及租银屡屡发生纠纷。1907年钦差垦务大臣、绥远城将军贻谷整理土默特地亩,为搜刮地价、荒价等银,剥夺土默特蒙古之地权,以发放“龙头大照”的形式承认汉族对土地的所有权;1915年,绥远当局以比贻谷更苛刻的条件继续清理土默特地亩,并发放“部照”(即“乙卯大照”)。经此两次清理,土默特蒙古的户口地被剥夺殆尽,蒙汉纠纷更加增多,加之大民族主义加之于蒙古族的歧视和压迫,更加剧了两族间的矛盾。本地汉族的习俗之一,是在年节时供奉祖宗牌位,俗称之为“容”。“容”最初当时为祖宗遗容,由遗容而演变为牌位(自始祖而下,按辈分书写于纸或布上并加装裱),年节时期悬挂室内,供子孙叩拜。本地区容与云同音,发音均为yong。部分蒙古族愤而以“容”为姓,以为“你们供容,老子就姓容,蹲在你们祖宗头上!”用汉字书写多写作云。如康台吉村蒙古族的云姓就是这样来的。
4、相互影响,云姓渐多:
据幼年曾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过书的老人讲,民国初年该校学生中云姓并不很多,不少学生只有名而无姓氏。以后由于受汉俗影响,采用汉式姓氏者多起来,同学间相互影响,以云为姓者渐渐增多,三十年代以后社会上这类现象也多起来。
上述诸种情况,可能仅仅反映部分云姓的来源。“云”作为一个为众多土默特蒙古族采用的姓氏,其渊源尚需进一步探讨。
四、蒙古族姓氏的特点
土默特蒙古原先并无汉姓或汉式姓氏,其历史最久者亦不过百余年。从其沿革变化中可以看出大致有下述特点。
其一,蒙古族生活方式随着草场的开垦而改变,其过程为由游牧而农耕,饮食由乳酪、肉类而粮食,衣着由传统蒙古服装而汉式裤褂,居住由蒙古包而屋居,语言由蒙语而蒙汉相掺最后变为尽操汉语,礼仪习俗亦揉入不少汉俗。这些即通常所谓“汉化”或“同化”。蒙古族的汉式姓氏由无到有,历史较短,到四十年代,除召河一带仍保持游牧生活者外,无姓氏者已经鲜少。因而其汉式姓氏,纯系被“汉化”的结果。
其二,蒙古族之汉姓或汉式姓氏,并不象汉族那样对姓氏恪遵不渝。汉族视改换姓氏为叛祖出宗行为,故而其姓氏历久不变。蒙古族的姓氏则保持相对的灵活性,父祖辈姓彼,到子孙辈改为此姓者往往而有,如常寿山之子孙有的改常姓为李姓,克寿卿之子孙改克姓为云姓。甚至同一家族姓氏互异者也屡见不鲜,如参领都格尔札布为云硕布氏,其子孙计有荣、云、殷、经、都五姓之多。另外,部分蒙古族渐以蒙语命名子女,并始摈弃汉姓或汉式姓氏,如巴图、巴特尔,青格尔图、其木格等等,名字之前并不冠以姓氏。
其三,随着各民族交往的密切,蒙古族的汉式姓氏渐趋稳定。如毕克齐的任、何、赵三姓,至少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沿用至今未变。其余如王、李、张、巴、孟、苏、康等姓氏,亦基本如此。
五、蒙古族采用汉式姓氏的原因
土默特蒙古族采用汉姓或汉式姓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如下几点:
经济方面——如前所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土默特蒙古以游牧为主,保持着传统的畜牧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与之适应的风俗习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大规模的强制开垦,使土默特蒙古丧失了赖以游牧的草场,畜牧业经济急剧改变为农业经济,于是传统的畜牧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为之一变,逐渐变成适应农耕的生活方式。经济生活的改变,成为土默特蒙古逐渐被汉化的前提条件,采用汉姓或汉式姓氏莫不由此决定。
社会方面——土默特地区在开垦过程中,形成蒙汉杂居区。据《归绥道志》、《归化城厅志》载,清末,仅归化城厅辖境的汉族已达十数万人。而土默特两翼全部人口还不足三万。蒙少汉多的结果,形成了汉语言环境,交际交流主要靠汉语进行,致使蒙古族不得不习汉语,此其一。其二,蒙汉常因土地、债务涉讼,从土默特文献档案看,这类讼案在道光年间还间或有蒙文诉状,道光以后的诉状则完全用汉文书写而成。诚如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在1928年的《内蒙的经济政治现状与革命运动》所说,“蒙汉人民之间发生财产土地争论或诉讼,如果蒙人不通汉话时,判官不问他的理由,只根据中国人(按,指汉人)的话来判决。就是晓得汉话的蒙古人也是十有八九次归于失败,因为一切权力都在省道县区。”这在客观上不能不促使蒙古人学习汉语,以维护自身利益。其三,清朝中期以前,朝廷禁止蒙古人习用汉语汉文,亦不准蒙古人起汉语名字。清朝后期,清政府下达的文件已多为汉文,土默特两翼对上的呈文也以汉文为主。不仅如此,官方还兴办专习汉文的汉书房,倡导蒙童学习汉语汉文。这些无不促进蒙古族习用汉语文。
还要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民国以来严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三十年代地方军阀在绥远主政时期,有一段时间对待土默特蒙古特别苛严,蒙古族出入城门、关卡,凡自报“蒙古某某”者,轻则不许出入,重者遭受折辱、欧打,有的甚至被关押,致使蒙古族而不敢显露蒙古身份,而以某村某姓某人自述。这种民族岐视进一步促使蒙古族使用汉式姓氏。
文化方面——自清朝中后期,土默特蒙古族或为维护自身利益,或因官方提倡,已开始习用汉语文。另外,蒙汉两族在长期交往中,蒙古族受汉族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吸收汉文化,导致最终以汉语文取代蒙语文的结果。在吸收汉语文的过程中,自然也将汉族的姓氏吸收过来,而成为蒙古族的姓氏。
心理方面——土默特蒙古族数百年间,确实从经济到文化被汉化了,尽管其民族语言文字已经沦失,但最可宝贵的一点,即民族意识依然存在,没有一个人不牢记着自己是蒙古人,而且是土默特蒙古人,这就是土默特蒙古虽被汉化而仍然为土默特蒙古的原因所在。在姓氏方面,以云姓为例,姓云的不必都是云硕布氏,但云姓既被视为土默特蒙古的族姓(且不论其是否正确),而此姓又为别部落、别旗蒙古所无,当地汉族也很少有姓云者,为显示自己系土默特蒙古,并告诫后人莫忘“所由出身”,于是云姓几乎成为土默特蒙古的一种标志,姓云者日渐多了起来。可以说,这正是民族心理,民族意识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土默特蒙古族之有汉姓或汉式姓氏,完全是由于从经济到文化被汉化的结果。当然,蒙汉两族长期交往,互相帮助,和睦相处的事例很多很多,将蒙古族采用汉式姓氏理解为相互影响的结果亦无不可。但是母庸讳言,蒙古族的汉式姓氏,在过去时代,是农耕化的结果,是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
表二:1923——1925年土默特旅京学生名册
荣耀先 傅汝枚 王 祥 云硕德 遇 春
(以上蒙藏学校专科)
昌 瑞 云 霖 崇 善 盂 纯 章士祥
吉雅泰 巴树棠 佛 鼎 多 寿 福 祥
云 盛 李裕智 赵 诚 王国栋 任殿邦
春 和 康济民 朱世富 康根成 云 泽
荣继珍 李春荣 荣 照 王丕绩 云彩章
云生瑞 云 润 麟 祥 康富成 高希柴
张崇德 荣继璋 荣尚义 赵文翰 云福祥
(上以蒙藏学校中学部)
云星槎 (北京大同中学)
桂十权 (北京大中公学)
云敬圣 (由蒙藏学校转河南军校)
以上据土默特历史文献档案抄录
- 上一篇: 清末珍贵的内蒙古旧影像资料
- 下一篇: !!! 罕见视频 稀有资料 实拍晚清时候的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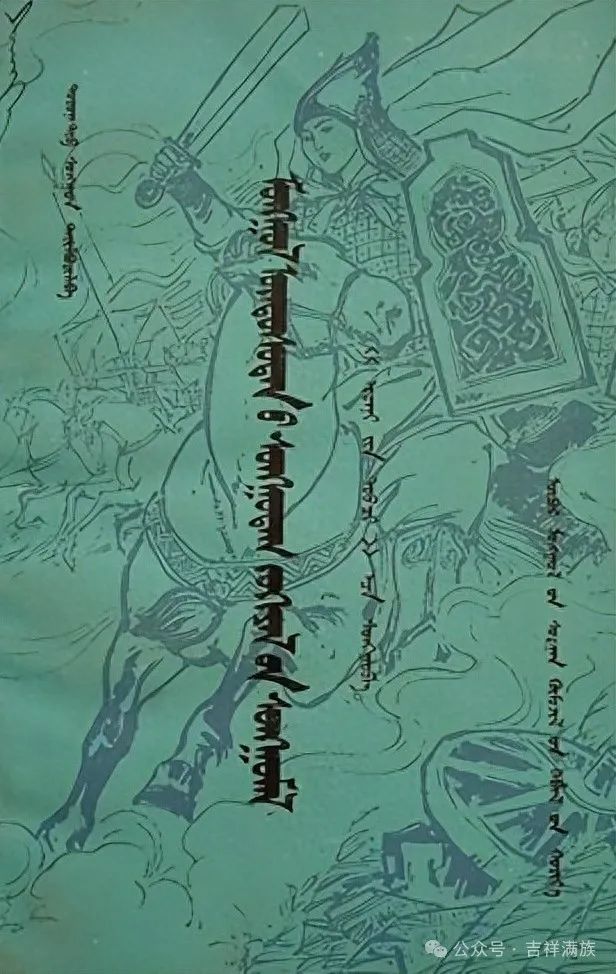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