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三期•南大C刊
·前沿聚焦·
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象征中的
“天人合一”观解析
李 军

[作者简介]李军,1976年生。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生导师。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方向。主持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艺术学规划项目一项;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艺术学研究项目三项;地市级社科艺术学研究项目两项。发表艺术类研究论文二十余篇,CSSCI来源期刊和CSSCI扩展版期刊论文五篇。多次参加国家级艺术教育教学会议。艺术作品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内蒙古美协展览多次,并多次获得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关于民族地区艺术创作研究论文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美术理论高峰论坛。应邀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包头博物馆等地举办个人学术讲座四次。近年来一直从事民族地区美术研究与创作。
摘 要
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以形象化的方式体现出本民族在宗教信仰、哲学思维、精神情感等诸多方面的民族本质特性,并且在悠久的历史积淀中蕴含着精神意象上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朴素宇宙观、哲学观。早在北方草原先民石器时代的文化创造中即体现出了人与天的互动关系,并依靠形象化的动物图案来寓意这种思维观念。之后,从玉器彩陶到青铜纹饰,再到蒙古族时期的动物图案,无不体现出这种“天人互动”的动态性的文化构建过程。蒙古族作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其传统动物图案的哲学渊源复杂而多元,在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融合中,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阴阳和合”等哲学理念也产生了深度的认同与涵化,并深刻影响着蒙古民族传统动物图案艺术创造和象征内涵的构建。
关键词
天人合一 动物图案 象征 哲学理念 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北方草原早期动物图案中的“天人感应”精神意象
蒙古族的传统动物图案艺术经历了复杂的传承与自我演化过程。蒙古族之前的北方诸草原民族在历史上的变迁与融合、在文化上的发展与积淀共同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草原文化,这些积淀也是蒙古族文化艺术发生与发展的基础。从原始岩画到之后的蒙古族动物题材图案都蕴含着精神意象中人与天沟通、和合的“天人合一”、“天人互动”的哲学认知。
1.北方草原史前岩画动物图案中的“天人感应”精神意象
原始时期的岩画可以说是人类动物题材图案创造的最早代表,产生于人类蒙昧而混沌的前逻辑时代的原始思维中,可以说是人类象征文化的一种显现和发端,它的象征性也是原始思维范畴的象征性。荣格把人类早期的岩画创造总结为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是某种屈从于“原始经验”的“原始意象”,伴随着神秘的原始的宗教观、宇宙观。
在早期人类动物形象岩画创造中,其创造动机往往屈从于某种功利性的思想或观念,原始人以巫术仪式来达到天与人、神与人之间的某种沟通,此种精神欲求往往成为原始动物题材岩画创造的心理驱动力,并且体现出信仰、观念与审美的混合状态。无疑,早期的岩画创造蕴涵着人的相关自身生存与生命的种种功利意识,巫术性、宗教性是其基本特征。北方草原地区遗留有极其丰富的早期岩画图案,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原始先民祭祀天地的情景。在后世的蒙古族传统动物题材图案中,同样与他们先祖的祭祀、宗教活动中的“天人合一”观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如,内蒙古磴口格尔敖包发现的神秘兽面纹石刻图案,这种特殊的造型符号无疑是某种巫术思维的体现,人物面部刻绘有天体图,头部之上也刻绘有天体图,可以理解为某种人与天的相互联系与沟通。在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巫师祭祀岩画,图中巫师作祈舞状,双乳外露,为女性,创作时间约为旧石器晚期。另外在包头市博物馆中有北方草原先民祭祀的仪式活动情景岩画,发现于阿拉善地区,断代时间约为夏商时期,人物作祭祀祈舞状,图中还有诸多动物形象刻绘,体现出北方草原先民以祭祀的方式通天地的祈愿。
北方草原先民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天体、动物等诸多事物都被当作具有灵魂和天佑神力的神灵来崇拜。这种观念在原始时期的岩画中即有所体现,其中包括天神崇拜、动物神崇拜等等多种形态。如,巴彦淖尔市乌中旗白奇沟发现的天神、兽面神图岩画;新石器时代磴口县阴山岩画中的“太阳神”岩画;包头地区达茂旗发现的“公牛•太阳神”岩画等等。都体现出北方草原先民对天、地、动物神灵的信仰和崇拜观念。黑格尔在《美学》中也说到:“象征的各种形式都起源于全民族的宗教世界观。” [1] 从这一点上来看,原始人类的整个意识形态,以及作为意识形态某种载体的艺术都被包裹、蕴涵于巫术与宗教信仰的范畴中。
贝尔在《艺术》中说到:“原始洞穴中的动物形象,仅仅具有一种极单纯的巫术含义,愈到后期,其象征意义就愈多。”[2] 即早期人类创造的形象化图式符号所蕴涵的象征内涵是随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对象性实践中而逐步丰富,并向多元化发展的。
中石器时代是人类艺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张碧波在《中华文明探源》中提到“玉器与彩陶是沟通天地的礼器、神器、法器。”[3] 无疑,依附于玉器、彩陶上的诸多图案纹样也具有了某种神秘的文化象征内涵。张碧波提出远古时期的王权即来源于神权,也就是所谓的“王权神授”。玉器、彩陶是这一时期掌握大权的巫师、巫觋们沟通天地的某种神圣礼器及法力的载体,而在这种文化中特定的动物形象图案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或为沟通天地的使者,或为巫师、祭司与天地相通的助手。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被称为中华第一玉的“玉玦”《周礼》中记载:“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4] 早期的动物形象图案与特定的玉器结合生成了特殊的文化象征性。在之后的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鹿龙、鸟龙、猪龙等主观创造的、幻化形的神兽动物图案。在赵宝沟遗址中还出土了神鹿纹陶器,其神鹿形象极似鹿与鱼的合体,也被认为是鹿与蛇的合体。这种复合形态的神兽图案在早期先民的文化中屡屡出现,多为氏族或族群的信仰物、崇拜物。另外,动物的神性化崇拜也是这时期的文化特点。如,源于与生存的直接关系,“猪”被赋予了祈求吉祥,护身辟邪的作用,祭祀中猪为人与天、神沟通的使者。
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一脉相承。同样,赵宝沟文化中出现的多元复合的、神秘幻化的动物形象揭示了原始时期部落氏族的宗教信仰、审美意识等文化特征,并印证了这些神秘幻化形动物图案所蕴涵着特殊的社会文化信息与象征内涵。如此时期出现的“龙”形象,龙代表天与神。《说苑》中记载:“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段,能为长。”[5] 阿木尔巴图在《蒙古族图案》中从视觉形态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华传统“龙”形象的雏形最早出现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堆塑龙、刻绘龙等形象皆蕴含着北方草原先民朴素的“天人合一”观。
红山文化是北方草原文化的发端。红山文化直接影响着北方草原民族后来的文化艺术创造,以及道德、礼制等社会文化形态,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艺术的发端。
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动物图案最具代表性。猪首龙是这一时期多元复合神兽的代表,以赤峰翁牛特旗三星塔拉的碧玉龙、黄玉龙最具特色,比中原文化的龙图腾及夏墟龙纹早1000多年。中华先民文化中的“玉琮”是礼祭天地的神器,玉琮上多刻绘神秘的兽面图案,是古代祭祀时通天地,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宗教法器。兽面形象也具有了人与天地、人与宇宙互通互融的文化象征。之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草原文明步入青铜时代的开端,多出现绘于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图案,形象神秘凝练,与商朝时期的饕餮神兽纹饰有相似之处,充分说明北方草原民族与商朝文化的某种联系和交流。
北方青铜文化之前的动物图案形象普遍具有神秘的、幻化的意象性特征,而北方青铜动物纹饰图案的出现与繁盛则说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以动物形象为题材的图案形式向多元多样化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
北方青铜时期的动物图案世俗化、生活化特征明显,种类繁多,其主题及造型有多种形式,如动物与人组合型、双兽组合等等。前面我们谈到在人类的早期某种哲学理念往往需要某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将其形象化并传达出来,所以,阴阳对立、匹偶形式、对兽组合、圆形造型等等构成方式就成为北方草原青铜动物图案普遍采用的手法。不仅在动物图案的文化寓意上具有历史延续的宗教观、天人合一观,在图案外在造型上也体现出北方草原民族对于这种思维观念的理解——即包含对天地、日月等互为阴阳的事物的认知,天父地母,日为阳,月为阴,天地、日月与人合而为一的观念。在这之中也蕴含有草原游牧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与和谐观念。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图案中的“对兽风格、匹偶风格”应该与草原先民的朴素哲学观或萨满信仰有关。阴阳互补、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并蕴涵着生殖繁衍、和谐统一等象征含义。早在北方草原远古时期的岩画创造中就有很多匹偶的形式创造,如新石器时代阴山岩画中的双马图、双鹿图等。匈奴时期的青铜动物图案也体现出这种匹偶的象征观念,如内蒙古博物馆中藏的“对兽青铜牌饰”;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三道湾匈奴墓葬出土“对马”金牌饰;伊克昭盟出土的汉代匈奴“双马”金饰件;准格尔旗出土的“双鹿”金饰件等都表现出天道、人道的合和观念。
北方青铜动物图案渗透着草原游牧民族独特的自然观、宇宙观和“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观念,在图案形象的表现中蕴涵着“强弱”、“生死”、“阴阳互动”等草原民族朴素的“二元对立”哲学思维和价值取向;蕴涵着对于天道、人道的意象性理解,是天、地与人和谐统一的朴素哲学观的形象化。
二、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中的“天人感应”与互动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其最终是人与天的感应和合,人与宇宙的“天人合一”的本体精神自由的实现,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始终执着表达着一个古老而当下的主题——天人互动。
1.动物崇拜与“天人感应”、“天人互动”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6] 蒙古族先民匈奴族称自己为“撑黎孤涂”,即“天的孩子”。匈奴崇拜自然,礼祖先,信鬼神,尚巫术。而蒙古族时期更是“无一事不问天”。《多桑蒙古史》记载:“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地五行。”[7] 在他们的意识中“天”对于人事起到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天可以左右一切。蒙古族思维意识中的“天人合一”理念体现出本民族的内在情感特征,即“天人感应”的精神意象,这种观念贯穿于他们的宗教、祭祀、文化艺术之中。
蒙古族信奉“长生天”,即“腾格里”,腾格里是蒙古族神灵系统中的主宰神,是创造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至高之神。道森在《出使蒙古记》中记载:“他们相信有一个神,他们相信他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的创造者,他们是世界上的美好事物和种种艰难困苦的赐予者。” [8]蒙古族认为“长生天”的佑护是幸福和美好的赐予,天神几乎掌管着草原民族的一切,因而历史上的蒙古族在诸种社会实践活动以及风俗习惯中都体现出对天神腾格里的崇拜和依赖。《蒙古秘史》中开篇即提到苍色的狼和惨白色的鹿是蒙古族的祖先,成吉思汗的先世是奉上天之名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一起渡海而来,在斡难河的源头布尔罕山,生下了巴塔赤汗。孛儿帖赤那即是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是惨白色的鹿。
蒙古族将自身先祖的诞生与天神的赐予相联系。《蒙古秘史》中德薛禅对也速该云:“我今夜得一梦,梦白海清握日月二者飞来落我手上矣。我将此梦语人曰:日月乃仰望之者也。今此白海清落我手上矣。正意白之落,盖汝乞牙惕百姓之族灵神来告之也。”[9] 在科尔沁、鄂尔多斯博物馆都收藏有海青图案的饰件。据《成吉思汗陵史纲》中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在乌审旗留有一只查干苏勒德,后被此地蒙古族供奉。据书中说,此苏勒德主希利彼(柄)上挂三面大白旗,早期白旗的中间绘制“海东青”神鸟图案,后来改为“飞马”图案。这种观念同样体现在蒙古族的神灵系统构建中,在他们的神灵系统中“动物”往往充当重要的角色,这些神灵观念中就有很多动物神灵。弗雷泽在《金枝》中说到:“早期人类对于动物的崇敬一方面是因为可以获得其皮肉,另一方面是在于所敬之动物能向人提供积极性的保护或帮助。”[10]
吴龙灿在《天命• 正义与伦理——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中提到“天人感应”,其主旨是上天有意志,有感应,有赏善罚恶的多重功能。蒙古族的“天人合一”观在早期则表现为“天命论”的世界观,是在原始初民的神灵观念和原生的萨满信仰相结合而产生的。这种观念在他们的实际生活、生产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体现出图腾信仰、动物神性崇拜等文化特征。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认为梦到特定的某些事物会与人的吉凶、祸福产生某种联系。如,蒙古族民间中“白骏”是最为吉祥的祥瑞动物,也被称为“天赐白马神”或“旺运神”。蒙古族认为梦到白马、白海青即是“天降吉祥”,这一点在《蒙古秘史》中有所记载。在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中白马、八骏图案非常丰富。特定的动物形象在这里充当“天与人”之间相互感应、相互融通的中介。在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牧民们认为梦到白马是大吉兆,会带来吉祥好运,乌拉特地区的蒙古族认为梦到白马、天鹅是吉兆,东部蒙古族一些地区认为梦到白海青、凤鸟是吉祥的征兆。另外,蒙古族的亚古特族群认为“白鼻马”是介乎于天与人之间的精灵神兽,而东部区蒙古族普遍崇拜的“鹰”则是天与人之间的使者。在蒙古族民间认为龙即是天神的化身,这一点在拉斯特的《史集》中有明确的记载,其渊源可追溯到北方草原早期文化中的“猪神”、“龙神”崇拜观念,具有祭祀天地的象征性,其图案形象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体现出。
早期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神灵化和崇拜观念实则是人自身本体“意志”的一种外化体现。也就是说,人类赋予了这些客观物以神秘力量和功能,包括思维意识中的那些动物神和依靠形象化的动物图案来求得天或神的赐予的欲求,使其最终成为了族群的崇拜对象,成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某种形象化象征。
2.“借兽通神”与“天人感应”
有学者认为蒙古族的祭祀文化源于北方草原民族的“天父地母、天人合一”观念,蒙古族将天与地合二为一来祭拜,是通过某种仪式求得“支配一切的力量”的庇护或赐予,即沟通天地的方式。另外,一些以特定的动物图案、图形为装饰的现象,则同样体现出这种特殊的象征性。
张树国在《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中提到:“巫师是沟通天地与人的使者,巫师升天入地的仪式中以特定的‘动物’作为牺牲,或者作为助手,包括龙、虎、鹿、蛇等,这些特定的动物形象在先民的意识中可以为人与天的互通中清除障碍。”[11] 张碧波在《中华文化探源》中提到:“玉器与青铜时代的动物纹应是‘尾饰’的发展和变化,表现借兽通神,以达到‘神人以和’的境地。”[12] 以“借兽通神”的方式达到“神人合一”,进而上升为“天人合一”,并且,体现出人与自然、宇宙的和合,人文与天文的同一律动。这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动物形象艺术化中象征的精神本原,涵盖人与自然、与社会、与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然而,科学与理性的低下致使早期人类对于自然万物及各种现象做出非科学与非理性的认知与判断,以自然的、天的力量和灵魂观念来判断、决定人事和人事的吉凶祸福。在这中间与他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动物必然充当了成为他们实现这些精神需求与功利的中介。在赵宝沟、夏家店、红山文化遗址中发掘的鹿龙、猪龙等神兽图案的陶器、玉器,即是敬天、敬神的祭祀神器,装饰于这些器物之上的神秘动物形象无疑即是天与人互动、人与神互动,并相通、相感应的中介或助手,并且用他们的方式将这些特定的动物形象化、艺术化。郑先光在《民间信仰与汉代生肖图像研究》中也提到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鹿龙等为“明器”,源于祭祀,“祭祀”源于对天、地、神灵的崇敬,是先民表达某种积极的、于己有利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欲求的方式。所以,祭祀中沟通天、地与神灵的那些动物、动物图案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也就是说人类从对动物的实体崇拜转化为动物形象的图案崇拜。这种形象化的特定动物图案同样也具有“借兽通神”,以达到“神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等效”作用。
我们拿敖包祭祀为例。蒙古族的敖包是一种原生态的生命文化承载物和象征体。敖包,底基为圆形,以祭祀天地,与蒙古族“独贵”的“天人合一”观相吻合。由蒙古族敖包文化延伸出的“十三敖包”,所供奉的神灵就有马神、牛神、羊神、骆驼神、战斗神等等。之后,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臧传佛教的经幡以及宗教图案、祥瑞动物图案才逐步出现在敖包文化中。现在,主要体现在我们常见的风马旗或印制有各种吉祥动物的经幡上。敖包祭祀的初始对象有白马神、龙神等。《内蒙古百科全书》中提到:“各地建敖包时,有的用树枝做成三角形支架,上置凤凰鸟形。各层装饰鸟兽等动物画像,以印有龙、蛇等动物的天马经幡装饰其上。”[13] 在一些地区的敖包上,杆顶部还装饰“凤凰”图形为冠首,也称“嘎如迪”。笔者在鄂尔多斯乌审旗调研时发现当地蒙古族在查干苏勒德祭祀时将各种动物图案的经幡、画像放置于祭祀台上,包括马图案、龙图案等。东部蒙古族地区祭敖包时有的部族会在敖包周边竖立部族的图腾神,如神鹰。蒙古族崇尚白色,因此有的部族则竖立白色的神鹰,即“查干鄂勒”。乌拉特、阿拉善地区的敖包祭祀时,有大量的绘制有马、四雄,以及“五畜”图案的风马旗和经幡来装饰。还有的地方将马、牛、羊、蛇,以及龙、凤等神兽动物形象绘制在白色的布上或经幡上,插于敖包的石堆上进行祭拜。这种现象具有久远的历史。
内蒙古很多地区萨满巫师的服饰图案同样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萨满——“额烈乌都干”、“查干额烈”,即“鸢萨满”、“白鸢萨满”的意思。“鸢”即是鹞鹰、鹰,“查干额烈”是萨满翁衮中的形象。萨满神帽上的鹰造型以及“鸟羽”式萨满服即是这种文化的象征。关于这一点早在上古巫觋的祭祀活动中即有所体现。首先人与天地的沟通需以某种方式实现,那么,会飞的鸟类即成为萨满陟神通天方式。“巫师们必有以陟神的工具或凭借,这就是有羽毛的翅膀、飞鸟或其他动物。”[14]萨满服饰中的鸟、鹰、蛇、龙等等图案形象无疑是这一观念的反映,这些动物图案即成为通天使者,也成为特殊的象征符号。
在这个时期,动物图案的形象化与哲学理念、宗教信仰往往是一体的、混沌的。蒙古族朴的意象性的哲学观无疑是本民族思想史中最为普遍的原则和基础。同时,在这个特殊的社会阶段中,既体现出哲学的理念特征,也是本民族文化和艺术创造的美学思想渊源。反之,这种文化艺术创造中即蕴含着他们人与自然的互动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观,并以暗示和隐喻的方式存在。
三、中华传统“天人合一”观与蒙古族动物图案象征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相通并和谐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本原。
在以“气”、“道”为基点的中华传统宇宙观中,“气”、“道”幻化生成万物,“无”是初始本源,也是“有”的归宿。有与无、实与虚在终极上不是对立的,万物与人在精神、心灵层面是相通相融的。“天人合一”其渊源产生于《周易》,原本是卜筮之书。
“天人合一”是一个具有广泛含义的抽象性概念,更是一种具有无限思维延伸的精神意象。“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人类与自然万物的诸种对象性实践活动中构建了人与宇宙、万物之间可通、可融的合一性精神意象,并且在阴阳、五行思维体系中蕴涵着“天”对人事的吉凶、祥瑞、祸福等方面的影响。
《周易》中“阴阳”的哲理认知包括天地、日月、四时、男女、白黑、昼夜等方面。《尚书•甘誓》,阴阳幻化与五行相生相克影响万事万物的变化,进而逐步与生殖、人事、吉凶、祥瑞、福祸等生成某种关联。《周易•系辞下》中:“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有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也。”[15] 旨在阐明阴阳五行变化对祥瑞、福祸的影响。而祥瑞、福祸又与某种现象的变化或某些特定的事物产生联系。《周易》中:“天垂象,见吉凶。”[16] “象”为自然之“象”,“象”与人产生感应或共感,并且“象”的出现或变化预示诸事的吉凶、祸福等。这些现象或事物也就成为人与天沟通、合一的具有神秘力量的中介,即人与宇宙之间相通、相感的“天人感应”思维观念,他们的形象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含义,这本身是建立于非科学、非逻辑性上的,但是在早期人类的意识中却赋予了它神秘的“逻辑性”和因果关联的思维特征。如《周易•坤卦•彖》中: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牝马”即“雌马”,“祥和”之兆。《说文解字》中:“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安宁。” [17]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凤凰”具有母仪天下的祥和象征,是“天降祥瑞”的征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凤凰”是人与天、地相通相感应的中介使者,凤凰也被绘制于墓穴,是“引魂升天”的神鸟,具有特殊象征寓意。
“四灵”图案是代表四方神灵的具有神性的动物形象,在中原和北方蒙古族地区广泛流行。“四灵”与古代先民的天文学、哲学思想和五行思想有密切的渊源。裸虫、麟虫、介虫、羽虫、毛虫,五虫分类与五行相配,东配麟虫,南配羽虫,中配裸虫,西配毛虫,北配介虫。龙、凤、虎、龟即成为四类虫之“长”,“四灵”被赋予了神性特征、祥瑞特征,也被称为“四方天神”。“四灵”图案即是在“天人和一”的精神意象中寻求“人与天”、“人与神”的某种感应和相通,将人文与天文、地理与星宿相对应,成为祥瑞象征的动物图案,并且在文化的交流中广泛出现在北方草原先民及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到后来的辽代及蒙元时期,四灵图案中的虎多被狮子替代,朱雀多以凤纹替代。另外,在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民族传统动物图案中常出现的双鱼、对兽图案中,皆有“阴阳和合”的象征性思维内涵,并蕴涵着宏观意象的“天人合一”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认为:“象征体系中包括‘双重性’,或称‘两极性’,即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如自然/文化、阴/阳等。”[18] 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与地、男与女都是具有阴阳对立的两极。天地化生万物,男女化生人类,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阴阳和合”观念的体现,并蕴涵着对立统一的“天人合一”哲理认知。《周易•系辞》中说到:“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9] “乾”符号“一”,表阳。“坤”,符号“一一”,表示阴。《说苑》中云:“雄为阳,雌为阴,其在獣则牡为阳而牝为阴,其在民则夫为阳而妇为阴,天之道也。”[20] 天道化生万物,天道与人道和合统一。这一点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玉器、彩陶及青铜器动物图案中多有体现。
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维观是中华文化创造的某种心理动因和普遍性的本质内涵,形成一种隐而不彰的内在精神主线。同时,在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中,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渗透、融合,并体现于他们的文化、艺术创造之中,成为蒙古族传统图案“天人合一”观象征生成的重要文化渊源。
结语
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象征生成的文化背景是多元的,这些图案往往以形象化的方式体现出本民族在宗教信仰、哲学思维、精神情感等诸多方面的民族本质特性,而这些也正是构建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象征产生的文化渊源。另外,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的象征是一个动态性的构建过程,在自身文化的历史发展中积淀生成了基于大生态理念、社会和谐理念与精神意象上的“天人合一”观。同时,在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中,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阴阳和合”等哲学理念也产生了深度的渗透与互化,成为构建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象征的重要部分。
English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stone age,the northern grassland ancestors had produced primitive and simple outlook on the universe and philosophy. Relying on the intuitive and expression of the aesthetic image,art, moral thinking to suggest some,although not yet formed a rational world view of philosophy,but has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religion and ar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aos.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the symbolic formation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animal motifs is complex and diverse. In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the northern grassland nationalities,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been formed based on the great ecological view,social harmony view and spiritual image. In addition,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Multicultural,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harmony","harmony between yin and Yang" philosophy also has the depth of identity and acculturation,an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artistic creation pattern symbol.
Key words: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animal patterns;modeling images;symbols;philosophical ideas.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9.
[2]〔英〕克莱夫•贝尔(周金环译).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
[3] 张碧波、张军.中华文明探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
[4] 陈戍国点校,.周礼,春官宗伯第三[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9,54.
[5]〔西汉〕刘向.说苑.卷18《辩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55.
[6]〔汉代〕司马遷.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2892.
[7]〔瑞典〕多桑(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9.
[8]〔英〕道森(吕浦译).出使蒙古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9.
[9] 道润梯步.蒙古秘史[M].卷1,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29—30.
[10]〔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M].石家庄:大众文艺出版社,1981,533.
[11] 张树国.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5.
[12] 张碧波、张军.中华文明探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4.
[13] 文物考古卷编委会.蒙古学百科全书[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37.
[14] 张树国.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3.
[15] 〔明代〕来知德集注,胡真校点.周易•系辞下[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49.
[16] [明代]来知德集注,胡真校点.周易•系辞下[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21.
[17]〔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四篇上,〔宋代〕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79.
[18] 何星亮.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M].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2003,23.
[19] [明代]来知德集注,胡真校点.周易•系辞下[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39.
[20]〔西汉〕刘向.说苑[Z].卷18《辩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53.
编者注:[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蒙古族传统动物题材图案象征研究”(项目编号:17YJA760027)阶段性成果之一。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 上一篇: 【雨花视角】蒙古族传统“安代”仪式的指号分析
- 下一篇: 安代舞——蒙古族集体舞蹈的活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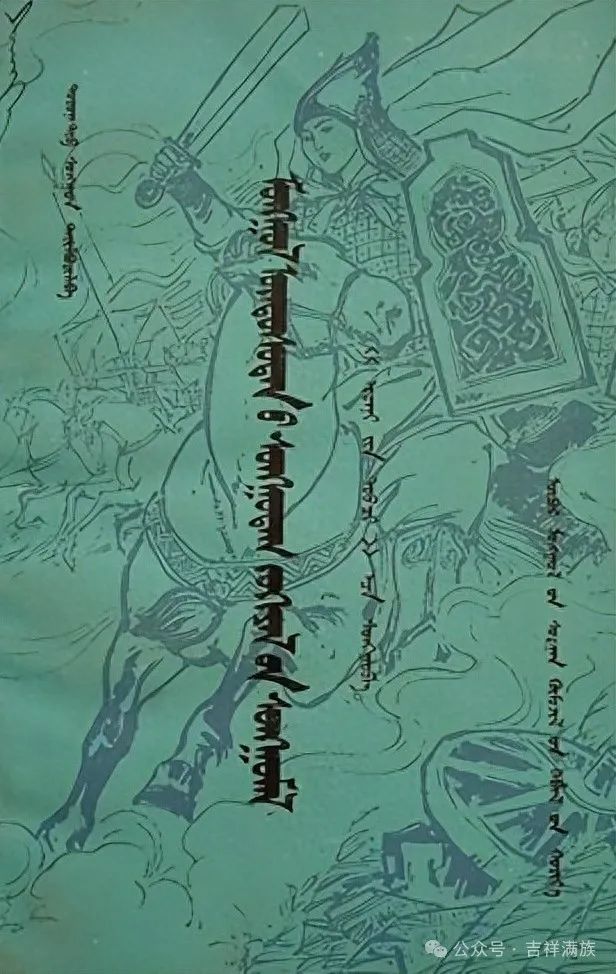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