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民族。也是继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后雄踞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民间美术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其鼎盛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时代曾横跨欧亚,贯通中西。蒙古民族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巍峨的阴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中部。在这里生活过的北方少数民族都留下了他们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当蒙古民族登上历史舞台时,也接受了其他民族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同时也因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有所变异。由于相同的地域、地理环境,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这种草原文化的许多基本特征世代相传,历经千百年保留至今。在这种文化传承和变异的过程中,扎根于人民中的民间美术则有着相对的稳固性。这已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材料和民族民俗学资料所证实。
阴山和贺兰山系,是古代游牧狩猎民族部落人民创造民间艺术的宝库。也是北方草原文化民间美术的摇篮。在这里,人们创作了数以万计的岩画,描绘出了一幅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廊。1974年在伊盟准格尔旗玉隆太出土的大量匈奴、东胡两大游牧民族创造和使用过的以动物纹饰为特征的青铜饰品(考古学上前者叫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后者叫夏家店上层文化),无论是艺术构思,还是制作技术都已达到了臻于完美的程度。也将民间美术推向了成熟期。这种青铜文化的出现,标志着草原上游牧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飞跃。“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对以后的鲜卑、蒙古以及对整个欧亚的古代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
众多的辽墓壁画和珍贵的元墓壁画以及这一时期出土的大量随葬器物都显示了草原游牧文化中服饰、马鞍具工艺等民间美术演变的轨迹。从六千多年前的赵宝沟文化和距今五千年左右的红山文化出土的陶器纹饰到距今三、四千年的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出土器物中重复出现的回纹、云纹、犄纹、动物纹,直到现代蒙古族常用的民间美术图案纹样都是一脉相承。现代蒙古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中依然广泛使用这些图案,它以各种方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这些纹样也成了蒙古人最典型的装饰形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这些纹样保持了较稳定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在民间美术的发展中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蒙古族民间美术图案艺术的源头在考古发掘中亦找到了充分的证据。
民间美术在生活中是物质文化。从它的起源直到今天,始终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性。既满足人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物质生活的需要,又具有满足精神需要的艺术价值,同时又具备了它的传统性,满足了人们精神上对美感的要求。我们可以从蒙古族服饰、刺绣、建筑、马鞍具等造型艺术、绘画和民间美术图案等方面运用考古材料与现在蒙古族的民间美术做对比,窥探蒙古族民间美术之渊源。

服饰
蒙古族的服装主要是蒙古袍。早期服饰式样单一,《黑鞑事略》中载:“其服右衽,道服领,少数为方领,以皮、革、帛制作,衣肥大,长拖地,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内,一裘毛向外,男女式样相似。”这一阶段蒙古袍的式样从考古学实物可以看出:
1982年夏发现的赤峰市元宝山区宁家营子沙子梁元墓壁画中男女墓主人对坐图。男主人居左,身穿右衽蓝长袍,戴圆顶式帽;女主人居右,身穿左衽紫色长袍,外罩深蓝色开襟短衫。
1984年乌兰察布盟达茂旗明水乡发掘清理蒙元时期墓葬,出土一件完整长袍。经专家考证应是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汪古部的墓地。该长袍呈褐黄色,道服领,肥大拖地,做工精细,衣料考究,用腰带紧束腰部,袍子上绣有以各种花卉植物为题材的装饰图案。
从以上出土文物的时代可以看出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在服饰上的传承和演变的轨迹。
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服饰的特征是重视头、胸、腰部装饰并有腰带,足上穿靴,左衽披发或编发。《周书·突厥传》云:“突厥,其披发左衽,犹古之匈奴也”。史载鲜卑族“披发左衽,故称为索头”。这种匈奴、鲜卑、突厥族的装束为契丹、女真和蒙古族所继承并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其中有些形式略有变异,左衽袍变为右衽,披发变为髻发或辫发。陕西省客省庄 140号匈奴墓透雕铜饰件、嘉峪关魏晋墓的画像砖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装束。
腰带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服饰,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记》、《汉书》匈奴传中记载的“黄金胥纰”、“鲜卑郭洛带” 就是腰带的早期形式。现代蒙古族的腰带正是继承了这种习俗。用腰带束腰是马背民族骑乘的需要,也是一种重要的装饰。
重头饰、耳饰、项饰也是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同时游牧民族的金属镶嵌和其他工艺也因此不断发展。头饰、耳饰、项饰不仅仅是装饰品,还有其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还体现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尊严和财富。
蒙古统治者在 1368年元顺帝败退漠北后直至 1911年满清灭亡,期间虽有过短暂统一,但总体上蒙古民族失去了中央集权统治。各游牧部落在政治、经济上相对独立。这长达五百年的分裂局面,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之一就是服饰的多样化。之二是各游牧部落受到地理环境的变迁、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及与许多特定民族的长久往来(如土默特部与汉族,和硕特部与西藏人,布里亚特部与西伯利亚人)使得蒙古族服饰的基本特征几乎全部消失了。
刺绣工艺
蒙古刺绣或装饰图案,是由点、线、面三种手法组成。点绣是用不同疏密的排列点组成图案。这种表现方法对丰富纹样的作用很大。通过运用点的大小、疏密、轻重、虚实等各种不同处理手法来获得不同的效果。点的方法很多,有粗点、细点、有规则点、无规则点、圆点和其他各种形状的点。在绣花毡和靴子上的点都是虚点,合起来形成虚线、虚面,主要衬托一些浮纹和主体图案。这些点有时也最能显示众多、聚散的现象。此外点还有活跃感,在密集的点状底纹上,用几种艳丽的彩布较大的点装饰,具有活泼球体滚跳的联想。这些点还给人以星星闪烁的形象感和串珠的遐想。
线绣主要是直线(垂直线、水平线、倾斜线)的运用;以长短不同、粗细不同、疏密不同的直线,做出多种变化,形成极好的图案。用不同的折线,采取粗细、重叠、颠倒的方法组成各种交叉图案,常见的有回纹、哈那式交叉图案、盘肠图案等。最多见的是卷草曲线和云纹之间的相交、相连的曲线以及犄纹和卷草纹等等。还可以用线表现各种明暗层次。线具有方向感、动态感,是曲、直、粗、细、长、短的最佳概念。横线有平稳感,竖线有肃穆感,斜线有不稳定感,曲线有弹动感,交叉线使人产生繁杂或紧密团结、纵横交错之联想。
面的运用范围较广,有完全用块面构成的,也有与其他表现方法结合运用的。面与点对照,它有巨大、整体的特征,也是点、线密集的最终转换形态。点和线要确定其位置或形态方向时,都要依附于面。面的应用上,有三角形、四边形、圆形等,它们还可以演变成多种形状,如多角形、斜方形、矩形、梯形、菱形、曲线形等等。这种蒙古族特有的刺绣工艺在出土的许多服饰中都有所表现。
建筑艺术
蒙古包是蒙古族建筑中最典型的形式,也是游牧民族最为理想的居住场所。它是由“哈那”(可折叠的木质围墙)、“乌尼”(椽子)、“陶脑”(天窗)、门和数块羊毛毡子组成。取材便利,制作简单,易于搬迁。这种建筑形式古代汉文典籍中称作“穹庐”、“毡帐”。是北方游牧民族适应游牧生活方式创造的杰出的建筑形式。公元前 5世纪左右的匈奴人就已经使用蒙古包了。之后的鲜卑、突厥、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沿用了这一居住形式。到了蒙古帝国时期(公元 13世纪),随着蒙古族的兴盛,出现了可容纳千人的巨型宫帐式蒙古包和用几十头牛牵引的车载蒙古包。蒙古包传承至今,已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象征。
马鞍具工艺
蒙古高原地域辽阔,从匈奴族或更早时期起,马就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长期以来,草原牧民早已养成了爱马、饰马的习俗。这种习俗使马鞍具工艺得到高度发展。匈奴人的马鞍具从出土的青铜饰牌上看,只有鞯而没有鞍。到辽代,契丹人已把马鞍具的制造工艺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1953年在赤峰郊区大营子出土了辽应历九年(公元 959年)驸马卫国王墓中的两组马鞍具。一组为铜鎏金金龙戏珠纹马鞍具饰件;另一组为马鞍具饰件马笼头、盘胸、缨罩、后座、鞍鞒、马蹬等一千多件。马具上饰有动物纹和花草纹图案,做工精巧,装饰华丽。
1986年在哲里木盟青龙山辽代陈国公主墓中又出土了两副完整的马鞍具。这两组马鞍具的制作工艺和装饰水平堪称精美。1988年内蒙古博物馆在锡林郭勒盟征集到一副蒙元时期较完整的纯金马鞍饰件,是从一座自然毁坏的墓中出土。据考证,墓主人是一位年轻的贵妇。马鞍鞒金饰件正中浮雕一只奔鹿,周围饰有花卉图案。而辽驸马墓和陈国公主墓马鞍上也有鹿的图案,这应视为一种文化的传承。蒙古族在继承了古代游牧民族马鞍具工艺的基础上,又制作出适应本民族征战、放牧、狩猎、出行等各种用途、各种式样、各种质地装饰的马鞍具。
雕刻与造型艺术
蒙古族民间雕刻以木雕、骨雕居多,金、银工次之。有浮雕、透雕、圆雕;多用于生活用具(家具、立柱)。生产工具(马汉刷)、娱乐器具(马头琴、蒙古象棋)。雕刻大多以动物为题材,多采用写实手法,生动逼真,把各种动物的神态、动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反映出蒙古族民间艺人高超的艺术观察力和造型能力。距今六千年前赵宝沟文化的鹿纹尊形器;距今五千年左右红山文化的玉雕马龙、玉鸟、玉龟等;阴山岩画中的各种动物图案;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各种动物纹饰牌、铜鹿、铜羊;鲜卑墓中的陶人、陶马等所展现的非凡的艺术才能正是草原狩猎游牧民族几千年世代传承又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长期积累、沉淀、演化而形成的。
绘画和民间图案
蒙古族民间绘画以藏传佛教壁画、唐嘎布画、木器彩绘为主,在各种绘画和装饰中,民间图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蒙古族民间图案中经常见到的云纹、回纹、犄纹等在距今 3~5千年的红山文化彩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器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上多次反复出现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这些出土陶器、青铜器上的纹样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美术纹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正是蒙古族民间美术图案的源头。
作者:尼格都勒为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蔡彤华为阿拉善盟博物馆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10年第 2期
来源:鄂尔多斯学研究
- 上一篇: 温格金 让雪山蒙古族手工艺术品大放光芒
- 下一篇: 唤起浓郁草原风情的——科尔沁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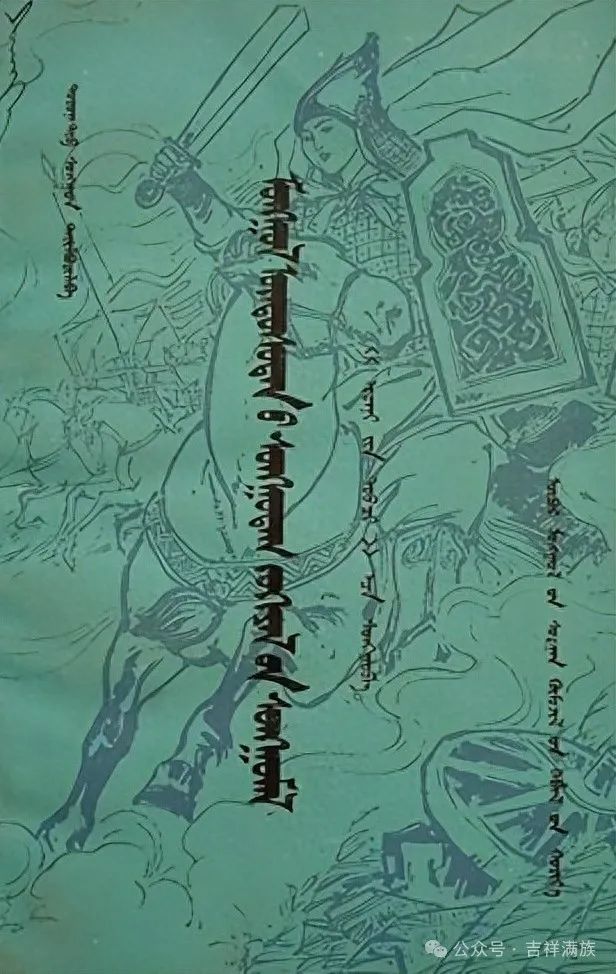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