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第1期
萧梅
内容提要:在欧亚草原这个广大的地理区间,如何进一步对草原游牧制度以及草原历史活动中的音乐贮存进行多元格局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需要接续的重要课题。秉持“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孤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观点,重思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以图对大草原由东往西不同地域、历史语境中不同族群所共享的“双声”现象及其研究作出再思考。
关键词:文明;文化 “双声”;“呼麦潮尔”;草原音乐;音色中心
(续)
二
我们已经忘了……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孤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1]
杨民康曾经在回答杨晓就其西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25年的访谈中指出:以往在中国音乐学术界所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视角,就是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为起点和文化本位,向内外两端延伸。同时,从外向内看,也还缺少一种以世界民族音乐作为起点的、与少数民族音乐之间的双向互动。而“这种现状是必须予以改变的”[2]。对此,我亦共鸣。中国漫长的内陆和海洋边界,从未中断过与外界的交往。以少数民族音乐为起点和文化本位向内外两端延伸,以跳出单一的汉族中心,无论是对中国传统音乐自身的研究还是对在中国的“世界音乐”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曾评价民康的这个立场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定位:“从学科层面上说,一方面以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音乐的联系,松动已经相对固定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范畴,在‘中外贯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胸怀下,提出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本位;另一方面,探寻如何打破中国音乐学界内部各分支之间的壁垒,形成一个互为开放、沟通嵌合的系统。……在操作层面上,以‘变异性’‘区别性’‘互文性’来观照‘跨界族群’所引发的不同关系,不仅使这一范畴成为观察和思考中国和世界民族音乐中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中介和环链;其范畴本身,还明确了各类音乐文化的动态研究与其对象动态的语境之关联。”[3]
回到《中国呼麦暨蒙古族多声音乐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的发言,由“申遗”开始。由于中国和蒙古国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过程中协调和步骤上的不一致,“呼麦”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归属仅刻写了中国。[4]围绕这个问题,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有各种议论。而中国的许多学者,也极尽努力,挖掘出该“乐种”自古就在中国的蒙古族与汉族中存在的证明(这些努力无疑是卓有成效并丰满了我们对该乐种的认知)。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牵涉到名录国别归属的政治议题。因为无论从“呼麦”的称谓与形态,在此前都不是近代以来中国境内蒙古族“显在”的乐种。笔者曾经读到来自“图瓦在线”(Tuvaonline)的一篇文章,该文报道了图瓦喉音歌唱(throat-singing)代表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功表演以及他们在世界范围中的影响,包括人们对该歌唱艺术所感受到的震撼;还宣布了作为驻教科文组织常设机构的阿塞拜疆代表埃莉奥诺拉·侯赛因(Eleonora Huseinova)将积极介入和推动图瓦喉音艺术入选文化和遗产保护名录的决定。该文同时指出,图瓦之所以难以入选“名录”的最直接原因是该国隶属于俄罗斯,因此“无法”获得直接向教科文组织申报的资格。此类现象亦并非孤例,亦因此引发了国际学界近年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名录的实施应如何考虑少数族裔身份地位的反思和批评。
但透过名录之选的纷争,我倒更愿意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伴随着呼麦“申遗”的前前后后,这个原来在中国版图上珍稀的、流传在阿尔泰山萨彦岭一带,跨越蒙古国、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等多个中亚民族与地区的、以一人同时唱出持续低音及其上泛音旋律的歌唱艺术,会一下子如春风吹生般在内蒙古地区显示出茁茁生机。由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乐手组成的各类乐队几乎都将“呼麦”作为标识,而频繁巡演于国内外舞台。近年来,他们频繁地在国际艺术节中获奖,与国际经纪公司签约,甚至在图瓦举办的喉音大赛中获大奖。相比于蒙古族的另一个“代表作”长调而言,呼麦在当下可以说已形成了另一种族性的象征性声音。就在这次研讨会组织的专场呼麦音乐会中,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首届呼麦演唱专业的学生表演了几乎包括蒙古国、图瓦的各种呼麦形式。当晚,恰有来自图瓦共和国的文化部长和总统夫人出席。在音乐会后,来自图瓦的总统夫人起立向全场听众发表感言:“我非常激动地在这里听到了图瓦的声音。”面对这些年轻歌者精湛的技艺,“谁的呼麦?”之问油然而生。然而,如果这些歌唱代表了一种在声音符号上的想象和认同,可以肯定它绝非一种对特殊声音技巧的猎奇和追求。我们虽然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证据说明呼麦声音本身的特殊性对爱好者的吸引,但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支撑这种认同的心态所依据的乐感和审美结构。为此,我非常欣赏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智慧地将“呼麦”与“蒙古族多声音乐”互为注释的做法。两者合一的研讨,恰恰是基于在蒙古大草原由东往西,尽管有不同的蒙古族支系与部落,有异于蒙古语族的突厥语民族,却大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共享的声音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选择“双声”,即由一个持续的低音声部加旋律声部而形成的“双重声音结构”(所谓声部之“多”并未改变这个双重性的基础)。这个声音的形态结构是一种文化特质,我们如果以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待这种特质,这块土地上任何一种与其结构相似的东西“突然地”成为一种族性的象征是不足为怪的。
20世纪90年代,莫尔吉胡撰写的《“潮儿”现象及“潮儿”音乐:试论阿尔泰蒙古古音乐文化圈》[5]即以这个特质出发,试图构拟草原音乐文化圈的起源与发展。直至今日,这位年迈的老人还在执著地以“多纳茨”(doughnats)现象为视角,力图观察和挖掘蒙古族音乐文化的起始与衍化。在研讨会上,老人跟我说起许多“双声”音乐在蒙古族同胞中流传的生动故事,包括歌王哈扎布在出访日本时,因文革之后第一次能够公开歌唱“潮尔道”而涕泪交加的往事。哈扎布的激动,说明了人声“潮尔”在蒙古族人中所享有的高贵地位,亦让我再次受到草原情怀的洗礼。但是我依旧不敢触及“始源”,因为我认同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我总觉得与其在音乐形态的层面上去追究源于某一特定地域或族群(部落)自身内部的“原生性”考证,不如就阿尔泰山脉的呼麦(浩莱潮尔)、吹奏“楚吾尔”(冒顿潮尔)、弹拨托布秀尔(托克潮尔),锡林郭勒的人声潮尔(潮林道),科尔沁的弓弦潮尔(抄儿)、四胡,以及遍及广大草原被蒙古族、哈萨克诸族群所共享的口簧等系列双声结构,进行其特质共性以及内部支脉历史过程之区别性的研究。所谓“一方面探讨作为音乐核心的‘双声结构’为何以及如何在这一广阔的地理范畴内出现,另一方面考察该核心结构如何与在地(local)文化互动而被塑造为多样的表征”[6]。包括历史及当代语境中,由文化认同而跨越“政治边界”,进而在“作乐”过程中的互文建构之考察。“它同样要求静态和动态的结合,要求在‘形—义—用’层面互通的流动中考察其为何得以持续传承和传播,并不断建构蒙古族双声音乐的形态学及其文化释义。因此,它就是一个生长性的并需要持续关注的历时性研究。”[7]
这种考察和研究我视之为文明与文化对话过程的探讨。
[1]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页。
[2]杨民康、杨晓:《西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25年回眸——杨民康研究员学术访谈》,载《音乐探索》,2012年第1期。
[3]萧梅:《问学无捷径,求知如生命——杨民康民族音乐学》,载《民族艺术》,2012年第4期。
[4] 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公布,“中国蒙古族呼麦”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5]莫尔吉胡:《“潮儿”现象及“潮儿”音乐:试论阿尔泰蒙古古音乐文化圈》,载《音乐艺术》,1998年第1、2期。
[6]徐欣:《内蒙古地区“潮儿”的声音民族志》,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
[7]同⑧。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萧梅(1956~ ),女,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民族音乐学教研室主任,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音乐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博士研究生导师。
音乐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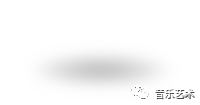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