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元朝后忽必烈和成吉思汗一样体认到,制定严明的法典是让政府能有效管理的关键。
不管是乾草原上的酋长,还是汉人国君,历来都是透过创製并施行新法,为自己在人民心裡构筑统治的正当性。忽必烈拟定法典时,并未以蒙古法律取代汉人法律,反倒是修改汉人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大法」相契合,藉此,同时得到蒙古人、汉人百姓的支持。这法典是他赢得子民效忠、拥护的另一项法宝,也是他最后击败对手南宋的另一项利器。
忽必烈汗政府保障地主的土地所有权,降低税赋,改善道路和通信。为进一步赢得民心,蒙古人减轻南宋的严酷刑罚。蒙古人将中国的死罪由 233 项减少为 135 项,几乎减少了一半。就连犯行理当处斩者,忽必烈汗也很少淮予处决。他在位的 34 年期间,有 4 年未留下处决纪录。
处决人数最多的一年是 1283 年,处决了 278 人,最少的年份是 1263 年,只有 7 人;但那 4 年处决纪录付诸阙如,有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没有处决犯人。忽必烈在位 34 年,处决总人数还不到 2500 人。他当政时的年平均处决比例,比起今日中国或美国之类国家,还更低了许多。
整体而言,他所设立的法律、刑罚体系,比起南宋的体系,法与罚更为连贯一致,且更温和、人道得多。只要切实可行,他即以罚锾代替体罚;他并且制定大赦办法,对悔过向善的罪犯予以大赦。同样的,蒙古当局致力于根除严刑逼供的行为,或可说至少大幅限制用刑。蒙古法律清楚表示,官员得有确凿铁证证明某人犯罪,才能予以用刑取供,若只是涉嫌,绝不能迳行拷问。
1291 年颁布的蒙古法典明文规定,官员必须「先以理智分析、推断案情,绝不能遽然施予任何拷打」。相对的,就在蒙古人著手限制用刑范围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却通过法律,将刑求的适用场合,扩大到更多无需证据的罪名上。其他国家的刑求方式残酷且五花八门,例如将人绑上肢刑架(以转轮牵拉四肢使关节脱离的刑具)、以巨轮压碎人体部位、以大钉刺穿人体、各种烧烙方法,蒙古人则限制刑求只能以笞条殴打。

笞刑示意图
蒙古法律的温和与乾草原文化的习俗,以某些古怪的方式呈现。汉人当权者常将罪犯黥额,让他一辈子带著犯罪的标记。蒙古人认为额头是灵魂所在,因此主张就连罪犯的头也不可凌虐。凡是已有刺青刑罚习俗的地方,蒙古当局淮许其继续此种刑罚,但言明前两次犯罪,得在上臂刺青,第三犯在颈子刺青,就是不淮在额头上刺青。
蒙古人不淮新的地区,或原本没有刺青刑罚习俗的少数民族施行这类刑罚。蒙古当局不允许将犯行写在身体上,而偏爱写在罪犯家门前的牆上,好让整个城镇的人能仔细盯著他。他们还实施假释制度,获假释的囚犯得每个月向当地官员报到两次,以接受行为审核。蒙古人讲究个人对群体的责任,因此囚犯要能获释,有一部分得看他是否愿意加入附属的执法机构,运用他的知识或犯罪经验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罪犯。
罪犯,乃至其所有家人,都得在文件上签名表示已收到判决,若对诉讼过程有所反对或不满,也须表达出来。为保存判决纪录,还必须按捺指纹,附在文件上。只要切实可行,蒙古官员总是尽可能让纠纷在最低层级就解决,不必动用到官员介入。因此,家族内的犯罪可由家族自行解决,宗教团体僧侣间的纠纷可由该宗教的僧侣解决,某行业内的犯罪可由该业界的代表开会解决。
为了协助民间自行解决纷争,蒙古当局鼓励印製犯罪学书籍,好让人民个人和那些小型联席会可以依循。在刑法范围裡,他们还针对官员亲赴犯罪现场,蒐集、分析、汇报证据一事,订下最起码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如何处置、检查尸体,以从中蒐集到最有用的线索,且检查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并且必须画图呈现伤口位置。
蒙古人的法律程序不只改善了执法品质,且符合了所有人(不只是受过教育的菁英阶层)都应了解法律、且能依法行事的最高原则。对蒙古人而言,法律不仅仅是裁定有罪无罪或施加刑罚的工具,还是处理问题、团结社会、维持安定的凭藉。
蒙古人不用作诗、书法这种古典学科教育官员,而提倡在不同领域培养更为实用的人才。从媒人、商人到大夫、讼师的各种行业,他们都制定了入行门槛,要求最起码应具备的知识程度。在每个领域,蒙古人的方针似乎都一样,他们致力将每个行业标准化,提升其水准,同时务使各色人等都能进入该行业,受益于该行业。
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境内如此多的人民,照理似乎只能透过以漫长科考过程遴选出来的旧式汉人官员,协助其治理国家,但忽必烈不愿如此。他不只未沿袭科举旧制,反倒废除科举,转而从汉人以外的各色外族人口,特别是穆斯林,寻找辅政之才,甚至若有欧洲人可用,他也延揽入朝,马可.波罗就是一例。

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
成吉思汗认为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官员娴熟「城市法律和习俗」,而忽必烈就和其祖父一样,从三弟旭烈兀所统治的波斯境内,引进许多这类人才。他一再遣使请求教皇和欧洲诸王派学者和博学之士东来,都未得到回覆。
但忽必烈心知不能过度倚赖单一民族或少数民族,且有心让不同族群相互制衡以利掌控,因此不断的将汉人和外族人合组成多元民族的行政团队;这些外族人包括吐蕃人、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
蒙古人让华北汉人、华南汉人、外族人这三大族群,在各部门裡各占一定比例,使得每个官员身边都有来自不同文化或宗教的同僚。一如成吉思汗不计出身,而根据能力和成就,从社会最底层拔擢人才出任最高层的领导职;忽必烈的政府也不断从最低贱的行业,例如厨师、门卫、文书员、通译,拔擢人材。拔擢出身卑微者,让他们能进入新工作领域,这两项作为使他们对蒙古统治者更为倚赖、更无贰心,且减少蒙古统治者与所统治人民的直接往来。
忽必烈汗不用刻板而科层严明的汉人官僚体系管理地方事务,而是施行成吉思汗的那套决策方法,透过大型会议、政务委员会、不断的商议来决策。只要可行,不管在哪个层级,蒙古人都捨官僚体系,以仿照乾草原小型忽里台的政务委员会代替。地方政务委员会得每天开会,任何新措施都必须得到其中至少 2 名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政务委员会得针对问题辩论,达成共识(审订按:元制中称这种合议制为「圆座」);决策由群体决定,而非单一官员。

忽必烈汗
依汉人标准,这是极无效率且不可行的体制,比起由单一官员决策、人民遵行的作法,太过浪费时间和精神。蒙古人还在多种领域推行小型委员会;病人不满意诊疗结果,可向由医界代表和非医界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申诉讨公道。蒙古人还组成类似团体,以解决从军人到乐师等各种行业有关的纷争。
旧式行政体系倚赖不支薪的学者官员,但这类官员却向需要他们服务或批可的百姓强索费用,藉此为生,蒙古人则雇用支薪官员来处理较低阶层的行政庶务。蒙古人将境内的薪资标准统一化,同时视地方生活水准的高低而有一些薪资级差。
共识决委员会和支薪文官这两项措施,未在中国成为定制,随著元朝灭亡即人亡政息。明朝一赶走蒙古人,随即恢复科层制官僚的旧制,废除委员会作法,改採由上而下的统治。自此,中国未再试行这种集体参与决策的治理方式,一直要到二十世纪民国创建者和共产政权创建者,才又努力重新引进地方政务委员会、辩论、支薪文官、公民参政的作法。
为促进帝国境内商业交易的速度和安全性,忽必烈大力推广纸钞。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纸钞交易已经完全上轨道了。他形容这种钱以桑树皮製成,形式如纸张,此时的大部分欧洲人仍不知道纸这种东西。纸钞呈长方形,有数种大小,上面印上面值,盖有朱砂印。纸钞的首要好处,就是比当时流通的笨重钱币,更方便使用、携带。
马可.波罗写道,纸钞通行全帝国,「拒不使用者,将招来死刑之罚」,但大部分人「非常乐于用纸钞付帐,因为任何东西,包括珍珠、贵金属、金、银,都可以用纸钞购买」。在波斯的蒙古统治者试行过元朝的纸钞办法,但未成功,因为当地商人不习惯这种外来的概念,商人因此心生不满,差点引发让蒙古统治者都没把握能镇压住的暴乱。统治者不想施行失败,颜面无光,最后撤回纸钞发行。
纸钞一通行,信用与金融崩坏的可能性随之升高。为了稳定市场,特别是维持放款的稳定,蒙古推出一项重要的创新措施,即立法允许宣布破产,但为防止利用破产逃避债务,商人或顾客顶多只能宣告破产两次。第三次就可能得遭受砍头之罚。

至元通行宝钞
蒙古人自始至终拒斥汉人的某些文化,例如儒家学说和缠足,但货币制度的改善,说明他们还是非常欣赏汉文化的其他部分。
忽必烈愿意深入探索中国历史,从中汲取切实可行的观念和制度。忽必烈建学校,恢复汉人翰林院(由国内硕学鸿儒组成的机构),以推动汉人某些传统学术和文化。他于 1269 年在诸路创设蒙古字学(即教授蒙古语的学校),然后 1271 年在汗八里创设蒙古国子学(即用蒙古语教授的国立大学)。他增设新部门,聘请学者,要他们记录当代大事,编纂、重印古籍,管理档案资料。
蒙古朝廷所设的翻译官,不只有蒙语译史(审订按:蒙古朝廷设有译史,负责处理公文及书面翻译等工作;另有通事负责口译),还有阿拉伯语、波斯语、畏兀儿语、党项语、女真语、吐蕃语、汉语、其他数个较不为人知之语言的译史;但面对如此纷然杂陈的语言,他们工作时还是会碰上费解的难题。只靠既有的畏兀儿蒙古语字母,蒙古人很难记录下广大帝国所需的所有行政资料。
在平日的行政上,译史得能拼写出汉地城镇、俄罗斯王公、波斯高山、印度圣人、越南将军、穆斯林神职人员、匈牙利河川等不同语言的名称。蒙古帝国人民所操的语言如此纷杂,忽必烈于是展开知识史、行政史上极具新意的一场实验。他决心创製一种文字,俾能「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并将这任务交付吐蕃喇嘛八思巴(Phagspa)。
1269 年,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製出 1 组共 41 个字母的文字,上呈忽必烈。忽必烈汗诏以八思巴字为帝国官方文字,但并未强迫所有人使用这蒙古新字。他允许汉人和其他所有人民继续使用各自的文字,心想这新文字以其优越性终会取代旧文字。汉人学者热爱自己的古老语言,怎肯为了这新创的蛮夷之字而捨弃。元朝国势一衰败,这蒙古文字最后遭大部分人民弃用。
历来的农民葡匐在各级政府官员脚下,生活裡最私密的层面任由他们掌控。蒙古人将农民以约五十户为一单位,组成名叫社的组织,藉此打破这古老的官僚体制。这些地方单位对农民生活既负有极大责任,又具有极大权力。它们监督地方农事,负责改善地力、管理水利和其他天然资源,在饥荒时提供存粮赈灾。整体而言,它们的角色形同地方政府,兼具成吉思汗十进位制组织和中国农民传统的特色。
社还负责为农民孩童提供某种形式的教育;蒙古人致力消除文盲,认为如此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忽必烈汗创设公立学校,让包括农民子弟在内的所有孩童,统统得以受教育。在这之前,只有富人有閒暇、财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因而得以代代支配不识字的广大农民。蒙古人认识到农民小孩在冬天时才有閒学习,而教授时不用文言文,而是用方言,教授的是较实用的课程。
根据元朝史料,忽必烈在位期间,共设立了 20166 所公立学校。这一数据可能是官员为美化政绩而有所夸大,但考量到当时没有哪个国家如此大张旗鼓推行普及教育,蒙古人这项成就还是很了不起。在西方,得等到下一个世纪,才有学者开始以方言书写;将近 500 年后,才有政府负起让平民大众的孩童受公立教育的责任。
本文摘自时报出版《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 蒙古帝国创建前,中国与欧洲未曾往来,而当成吉思汗去世时,他已藉由商贸与外交使两者连成一气,至今未断。 自由贸易、知识共享、多元宗教、世俗法律、外交豁免权……成吉思汗打造的蒙古帝国,构筑了现代世界的基础。 「最会说故事」的人类学家魏泽福,费时五年,深入禁区,颠覆世人对于蒙古帝国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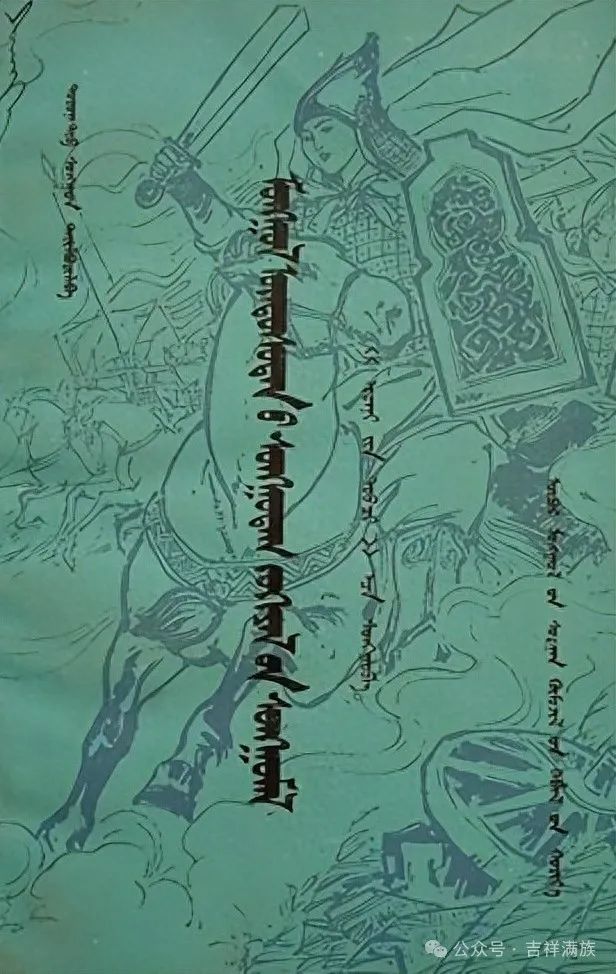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