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儿门,位于甘肃靖远县中堡乡营防村,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寺儿湾石窟(即红罗寺)隔河相望。它的东面是关爷山,西面是沙岩壁立的黑崖山。营儿门就坐落在这两山之间的一个极普通的小山沟里。如今,营儿门作为“门”的形象已荡然无存,仅有一堵元末明初时由蒙古人夯筑的土墙还矗立于横切沟口的红崖之上。它像一位历史老人,向前来寻根问祖、求神拜佛或考古参观的人们讲述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营儿门原住着一户马姓人家,人们常常戏称他们为“马鞑子”,又流传着许多诸如“七人七马过黄河”、“马鞑子占天下”之类的传说。这些传说在靖远、景泰一带虽脍炙人口,流传久远,但却从未引起人们深究的兴趣。1994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本清光绪年间由邑增生马凌云撰修的《马氏家谱》(以下简称《光绪十六年谱》)。该谱序言中一段讲述营儿门马氏民族渊源和姓氏来历的文字,唤起了我们对那些传说的回忆和深思。1995年初春,在景泰县我又看到了清乾隆五十二年由马氏后人为“马太母”初入芦塘立的墓表(以下简称《马太太母之墓表》)手抄件,是讲述马氏宗族发展和人口迁徙情况的。随后又陆续看到了马氏族人撰修的其它家谱、族谱以及他们为祭奠祖先绘制的神主,铸造的钟、磬等。这些文字的、实物的资料把我们吸引到对营儿门马氏民族渊源和姓氏来历的考证研究之中了。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综合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肯定而明确的结论:营儿门马氏原本不是汉族,而是元末明初时流落于此,而后隐姓埋名、逐渐汉化了的一支蒙古族人的后裔。
营儿门马氏的来历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它的民族渊源;二是“马”姓的来历。对这两个问题,《光绪十六年谱》记载得十分清楚。该谱序言这样写道:“太祖元始,本系前元国姓。兄弟二人名铁礼棉、铁礼秀,元末时由汴都而北迁,至红罗以南渡,率水浒而走马,向山曲以胥宇,住扎营儿门,为始托之地,由斯易铁为‘马’。”这里的“太祖”指铁礼棉、铁礼秀。“前元”是指公元1260年由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所建立的元王朝。“国姓”即国之皇族之姓,正如汉以“刘”为国姓,唐以“李”为国姓,宋以“赵”为国姓一样,前元国姓,当是成吉思汗家族之姓——奇渥温。“易铁为马”,“铁”是名的第一个字,不是姓,易铁为马是误记,正确地说,应该是易“奇渥温”为马。“前元国姓”、“易铁为马”,这就说明了营儿门马氏的民族渊源和姓氏来历。同时,“前元国姓”,“由汴都而北迁”,还说明了营儿门马氏祖先在“易铁为马”以前的社会地位,即他们是前元皇族的支系。关于这一点,民国6年由马门儒生马建基撰写的《马氏族谱》(以下简称《民国6年谱》)讲得更为明确:“太祖之所自出,原属元(宗)室苗裔。”汴都,汴梁,是今河南开封的古称,因在五代和北宋时,均为定都之地,故又称汴京、汴都。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汴梁被金人所占。1214年(金贞祐二年),金宣宗因惧怕北方蒙古势力南侵,又把国都从燕(即今北京)迁于汴梁。1234年,即南宋端平元年,汴梁被蒙古军从宋人手中夺取,直至元末。汴京一直是蒙古贵族生活和驻军的重地。据史料记载,汴京近城被辟为牧场,民间只能通行蒙古语等。马氏祖先驻进汴都,并“历皇祚九十春秋”而北迁(见《民国6年谱》),说明他们的地位是极高的。
那么,马氏祖先究竟是哪位皇族的后代呢?对此,几个家谱均有记载,但都含糊不清。20世纪50年代由一个叫王介夫的人所撰写的《马氏族谱》,在其序言中写道:“溯马氏原系铁木耳之本姓。”另一本在20世纪60年代马玉书撰写的《马氏族谱》也写道:“马氏其先世以国为姓,系铁木耳后。”这里的铁木耳究竟是指谁呢?已找到的家谱、族谱均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不过,从《光绪十六年谱》关于元末时“由汴都而北迁,至红罗以南渡”的记载中,我们大致可以猜测,“铁木耳”可能就是察罕帖木儿或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因为,从《元史》记载来看,元末时,从河南起兵,最后到甘肃兵败的皇族就是他们,而且兵败的时间正好是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这和几个家谱记载的马氏祖先“水浒走马至红罗以南渡”的时间完全一致。说他们是皇族,因为察罕帖木儿曾祖阔阔台、祖乃蛮台、父阿鲁温为成吉思汗四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代。而扩廓帖木儿是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后收为养子,在察罕遇刺身亡后,“兑其父兵”,与明军对抗直到兵败甘肃,北遁和林。
马氏祖先为什么要“由汴都而北迁,至红罗以南渡”呢?对此,几个家谱记载均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如新中国成立初族谱序中模棱两可地写道:“元末时干戈扰攘,烽烟四起,不无迁地为良之计。”《民国6年谱》序中也含糊其词地说:“元德既衰,举玉干金枝之盛充作琐尾流离之于。”等等。有的家谱、族谱甚至采取了不应该有的回避态度。
其实,马氏祖先的北迁、南渡不是什么神秘之举,也不是马氏祖先一个家族的单独行动,而是在一个人所共知的大历史背景下,在明王朝推翻并最终取代元朝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作为元王朝统治集团上层必然要做出的历史选择和命运归宿。
公元1227年8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结束了他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一生,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留给了他的后代。这个帝国经过15帝、163年的统治,又被新兴的明王朝所取代。就在帝国大厦行将倒塌之际,当年追随成吉思汗南下、平定中原、掌握权力、过着奢侈豪华生活的“黄金氏族”们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起来抗争,以图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在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失败之后,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不无迁地为良之计”。马氏祖先的北迁,实际上就是整个元王朝统治上层被迫北迁的一部分。
马氏祖先的北迁始终同依靠地主武装起家的察罕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为挽救元王朝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和信阳人李思齐在镇压红巾军的过程中崛起于豫东。遂战河南,平河北,击关中;又复汴梁,平山东,因功官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河行台御史中丞。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察罕帖木儿被山东降将田丰、王士诚刺死,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之。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明军攻下大都,顺帝率后妃、太子逃到上都,元朝遂亡。而扩廓则拥兵数十万,据守太原,对明军构成巨大威胁。洪武元年(1368年),扩廓被徐达、常遇春所败,西奔甘肃。次年,徐达又总大兵出西安,捣定西,取扩廓。扩廓方围兰州,又回兵定西,于沈儿峪(即今定西巉口)与徐达屯兵会战。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扩廓兵败,明军擒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1860余人,将士8.45万余人,马、驼杂畜数以万计。扩廓又携妻子数人北渡黄河,奔和林(今蒙古国境内)。(以上均见《明史·扩廓帖木儿传》、《明史·徐达传》)
扩廓兵败,把元军及追随他们的朝臣都留在了甘肃。除被杀和被抓者外,其余皆四散流落、自行逃命,营儿门马氏祖先就在这流落、逃亡者之列。“至红罗以南渡”。“红罗”即寺儿湾石窟所在地红罗山,与营儿门隔河相望,山下是黄河古渡口之一,“七人七马过黄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不过,《明史·李文忠传》中说追元嗣君北走,至红罗山下的事,是指山西古兴州一路的红罗山,不是甘肃靖远的红罗山。
这里的红罗山究竟是地名的巧合,还是后人的附会就不得而知了。相传,马氏祖先兄弟二人及随行者逃至红罗山下的共七人七马。在前有大河,后有追兵,眼看就要束手就擒的紧急情况下,他们向左手崖上的佛窟祈祷:“我佛如能保佑弟子过河脱险,愿以终生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弘扬佛法。”话音未落,只见河面上鬼使神差地出现了一座浪柴浮桥。七人七马喜不自禁,叩头谢过佛祖,踩着浪柴,策马过河。当明军追至河边时,浮桥却自行散去。无可奈何的明军只好仰天长叹:“天不灭鞑子!”这个故事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氏祖先确曾在这里过了河,这一点红罗寺和红罗渡口的存在多少是个明证。红罗寺早在唐代就已开凿,至今仍保存两尊唐代塑像,不过那时叫古刹寺,元末明初改为红罗寺。这一改名是否与上面的故事有关,尚无材料证明。红罗渡口也是自古就有,而元以后则对马氏家族实行优惠:凡马氏家族人要过河,均减免过渡费,这也是真的。鉴于此,我们对上面的故事也只好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了。
这里似乎有个讲不大通的问题:扩廓兵败本来就在黄河以南的定西巉口,而马氏祖先等流落逃命时却出现在黄河之北,还要设法南渡,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一点在《民国6年谱》中已有交待。该谱在追述马氏祖先的行程时说:“由金台而启行”,查定西、榆中、兰州一带的现地名,找不到叫“金台”的地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金台”在黄河之北。也就是说,扩廓兵败时,马氏祖先等不在战争前哨阵地的巉口,而在作为后防的“金台”。沿黄河之北寻找“金台”,很容易使人想到当年作为元军后防的兰州王保保城。该城位于中山桥东北朝阳山东侧台地上。据史料记载,为元至正二十八年左丞相、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败逃甘肃次年所修,以阻明军北进。城郭至今依稀可辨,南北210米,东西370米,残存东垣、北垣7段,残高6米,宽4米,东南开门。“王保保城”为后人起名,当时叫什么无从得知。距该城不远,有宋人修筑的金城关。后人因此而把筑于“台地”上的王保保城叫“金台”是有可能的。马氏祖先的“金台启行”,很可能就是由王保保城而启行。沈儿峪交战,以金台为后防大本营,控制兰州,并作为北撤的退路,这是作为精明的军事指挥家的扩廓帖木儿完全能够想得到的。
南渡以后,马氏祖先以营儿门为“始托足之地”。据《民国6年谱》记载,他们“托足”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和败逃的扩廓帖木儿取得联系,以图东山再起。该谱写道:“倚黄流为尺堑,始停住营儿门以固圉,继税驾芦塘以开疆。”芦塘在景泰县境内,当时归靖远管辖,这里是从兰州到蒙古的重要通道之一。也许他们估计芦塘可能还掌握在蒙军手中,同时估计扩廓帖木儿可能从芦塘逃去,故派人去芦塘联络,打探虚实,可是他们估计错了。明将徐达当时也是这么估计的,并派兵去芦塘堵截。而作为精明的军事家的扩廓帖木儿的行动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他没有去芦塘,而以“流木渡黄河”后,直奔和林去了。这样,即使马氏祖先的联络行动未能实现,也使徐达的围追计划扑了空。
芦塘联络行动的失败,迫使马氏祖先不得不放弃—切北撤计划。摆在他们面前的生死攸关的惟一选择就是隐姓埋名,实行汉化。实行汉化首先必须改为汉姓。为什么要以“马”为姓?对这一问题牵强附会的解释很多,但最可靠的还是从蒙古民族的性格、心理以及他们的爱好和生活习惯上作的解释:蒙古族爱马。马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又是生活中的伴侣,放牧、打猎、旅行、作战、娱乐等无不与马联系在一起。他们被称作是马背上的民族,马背上打天下,马背上坐天下。所以,他们对马的赞歌也特别真挚和热烈,说它是“强盛之国的象征”、“草原英雄的光荣”等等。以“马”为姓,正好体现了他们的这些特点,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自己民族性格、民族习惯的珍惜和忠诚。
北迁,南渡,指马为姓,这就是营儿门马氏的渊源史。
指“马”为姓以后,马氏祖先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但随着成家立业,人口发展,营儿门渐渐无法满足他们对生活资源的需求。于是,他们很快就实行了南渡后的第一次人口迁徙。从《光绪十六年谱》中“葬太祖于汤家寺白马庙后祖茔”的记载看,第一次迁徙是在太祖铁礼棉、铁礼秀手中完成的。就是说他们在营儿门住的时间并不长,约30年左右。太祖去后,营儿门并没有丢,留给他们已成年的子女居住。太祖则上了骟马塬(今曹岘、若笠一带)。汤家寺是太祖坟茔所在地,不是居住地,居住地在田家咀头。从几个家谱的记载看,马氏祖先在骟马塬居住的时间大约为百年左右,这和汤家寺白马庙后祖茔坟头四层排列也正好相符。一层一代人,共四代,按人口学统计规律25年一代人计算,也正好是100年。在此期间,马氏宗室随着人口增加,开始分房头。最初的分房是以铁礼棉、铁礼秀的五个儿子为起点的。相传,铁礼棉生二子,长子留住营儿门为大房;次子随其父上骟马塬,为二房;铁礼秀生三子,均随其父上骟马塬,形成三至五房。这五个房头分割形成之后,随着人口的再发展,宗室繁衍,各自内部还不断进行分房出阁,但这种分房出阁并没有影响马氏宗室最初形成的五大房头的基本格局。而这五大房头的基本格局后来又成为马氏宗室向外发展、人口迁徙中选择和组成新的村落的血缘依据,并一直沿袭至今。
在骟马塬居住百年之后,马氏家族因人口发展和对生活资源需求的扩大,不得不寻求和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基地。《光绪十六年谱》写道:“次则又移居碾子塬住坐。始有上塬、中塬、下塬之分。”就是说,他们迁徙的第二个目标是与骟马塬仅一沟之隔的碾子塬。
向碾子塬迁徙,是指马为姓以来马氏家族最大的一次迁徙行动。从几个家谱的记载和民间口传的情节看,这次迁徙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房头为单位组织起来的联合行动。在骟马塬住坐时,马氏宗室虽已形成了以亲缘关系和长幼次序为基础的五个房头,但还未形成以房头为界限的居住村落。而迁入碾子塬时则不同了。迁徙时是联合行动,选择和组建村落时则是以房头为单位的。具体分界是二房居中塬,三房居上塬(又称山头),四房和五房居下塬(又称山背后)。这种分界一直沿袭至今。二是带有明显的抢占的性质。碾子塬虽然辽阔,但并不是无人居住的荒塬,在马氏家族未迁入之前,这里已有人群居住和耕种。马氏家族的迁入,必然与原住人家发生矛盾和冲突。
这时的马氏家族已今非昔比。第一,他们已拥有发展起来的人口优势;第二,他们仍保留着蒙古族不肯驯服的强悍性格和体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经过百年岁月的流逝,马氏作为元朝“余孽”的概念和威胁已经渐渐淡化,他们存在的合法性也已经逐渐得到认可和巩固。因此,腰杆子硬了,敢于向别人挑战,敢于为生存空间而与当地人抗争了。所谓“马鞑子占天下”,正是发生在这次迁徙中的事。
有一个“劐肚爷”的故事讲的正是这个内容。故事说:马氏家族在迁入碾子塬时,与碾子塬原住农牧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惊动了靖远(当时叫靖虏卫)、会宁两县县长。因当时碾子塬在靖远和会宁两县交界之地,归属问题尚未解决,故由两县县长出面调解。两县县长把冲突双方代表召集到一个叫涝刺滩的地方。在百般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两县县长就以戏言难为双方:既然你们不听调解,那就抢占吧!谁占的归谁所有。但是有个条件,抢占者必须先劐破肚皮,让肠子流出来,然后抱着自己的肠子跑,跑到哪里,哪里就为谁所有,否则无效。话音未落,只见马氏家族人群中跳出一位年方二十上下的青年,二话不说,拔刀劐肚,肠子涌出,又用双手捧回肚里,抱着肠子起跑,从山后奔中塬,再从中塬占到山头,眼看着整个碾子塬就要被抢占完了,靖远县县长着急了,大喝道:“难道靖远人都死光了,叫你大(爹)占完了不成。”这时,一位靖远人才如梦方醒,追赶上去,推倒了这位青年。两位县长本是戏言,不料被马氏这位青年来了个假戏真做,演下了这出英勇悲壮、足以使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悲剧。从此,上塬、中塬、下塬无可争议地成了马氏族人的天下,这位青年也无可争议地成了马氏族人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马氏族人赢得了争夺生存空间的胜利,而他自己却永远长眠于被人推倒的那个地方。他牺牲后,一直伴随他生活、并最后和他一起跑完“占天下”路程的一只爱犬,七天七夜不食,也病饿而亡。如今,这位被族人敬称“劐肚爷”者及他的爱犬的坟头仍完整地保留于云台山下何家湾腰岘的一簇生机勃勃、永不萎谢的山刺丛中。历次平坟改地,周围的坟头都铲平了,但无论是马氏族人还是族外人,都不忍心平掉这座坟头。凡路经此地者都要低头凭吊,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这位英灵的怀念和哀思。
移居碾子塬之后,马氏家族中占据山背后的四房和五房很快又发生了新的分裂,以马太太母为首的五房远迁芦塘。从此,马氏家族最终形成了一个房头占据一个地方、自成一个村落的格局。
五房迁入芦塘的原因,口头传说和家谱记录相距甚远。马氏族人中一直有“先有营儿门,后有芦塘城”的说法。说马氏祖先“托足营儿门”时,一天,山洪暴发,冲去了营儿门的大门。洪水汇入黄河,把大门漂到下游的芦塘,被芦塘人打捞上岸。此时,芦塘刚筑成新城一座,还未来得及做城门,遂将营儿门的大门试安其上,不料分毫不差,正好合适。事情传到营儿门后,马氏族人遂去芦塘讨要,芦塘人不想还门,就提出划地交换。马氏族人也正为营儿门太小,无发展余地犯愁,就接受了芦塘人的条件,于是才有马氏族人的一支迁入芦塘的行动。
《马太太母之墓表》则写道:“马太太母者,靖远西乡人也,明季万历年间以子讳大明即寿官太公也,入芦塘军,因而太太母陆迁于斯。”这就是说,马太太母迁入芦塘是因为儿子入“芦塘军”的缘故。
该墓表继续写道:太太母初人芦塘时,“又携一嫡侄,讳大定,并侄妇李氏以来。后于天启岁,大定太公独回西乡,奉养其亲嗣。”顺着这一线索,从山后保存的雍正二年马氏四房人为祭奠祖先而绘制的《马氏神主》上,我们找到了“独回西乡”的大定公的名位,并有他带到芦塘的妻子李氏的名位。他没有带李氏一同回来,是因为家中还有一房妻室王氏在。这就确凿无误地证明马太太母就是从山后迁出的。
山后为什么又叫“西乡”?其实,西乡不单独指山后,而是包括骟马塬、碾子塬一带的总称。明朝时,靖远关于“乡”的设置不像现在这样复杂。以靖远城为中心,城南的叫南乡,城北的叫北乡,城东的叫东乡,城西的叫西乡。当时芦塘也归靖远管辖,属北乡范围。所以马太太母实际上仅仅是从西乡迁到北乡而已。
《神主》上惟独没有马太太母及其丈夫、儿女的名位,是因为他们是五房头人,而《神主》是四房头人绘制的。
围绕马太太母的出走,至少在铁礼秀的后代中间还发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民国6年谱》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始祖以为,古往今来,可大可久之业,而基于无逸之一念。苟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这段近乎辩理的文字,是针对马太太母及其大明、大定迁徙的。而反对迁徙的大传则主张:“察天时,相土宜,暴霜露,斩荆棘,上绳祖武,绵家声于弗替;下裕后昆,致家道于大康。”这与太太母的主张显然是不一致的。争论的结果以各行其是而告终。太太母迁入芦塘时的年龄,从大明公已从军成家的情况分析,至少在40岁上下。大定公于天启年间“独回西乡”,他去时只带李氏,别时却已有子秉驯。秉驯又到从军娶妻生子的年龄,至少得20年时间。秉驯入川“奋勇阵亡”,妻守一男讳君礼,且又受太太母之素教,到了“事亲孝,事君忠”的年龄,少说也得15~20岁。这样加起来,太太母至少得活75~80岁才能做到这些。以年龄推算,太太母从靖远西乡入芦塘的时间大约在明万历二十年以后,即公元1592年以后。万历共48年。万历之后是泰昌,泰昌之后是天启,两个年号共8年。大定于天启年间返回靖远西乡,他在芦塘居住的时间约30年左右。所以,太太母迁入芦塘的时间估计在万历二十年以后是有道理的。以此推算太太母的生年大约是明嘉靖三十一年,即公元1552年左右。而她去世的时间大约最早在明崇祯元年,最晚在崇祯五年。
马太太母迁入芦塘,以她们的刚毅和干练开创了马氏族人生存的新天地。至乾隆年间,芦塘马氏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一门望族。至今,人口已达3000之众。
- 上一篇: 阿富汗的蒙古人后裔哈扎拉人
- 下一篇: 蒙古族后裔村——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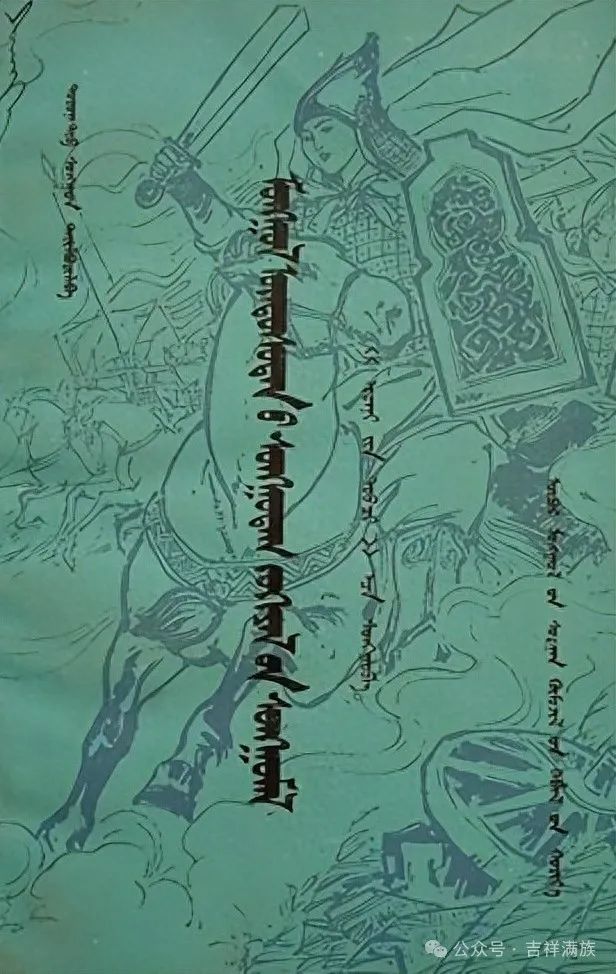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