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达斡尔族与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的对比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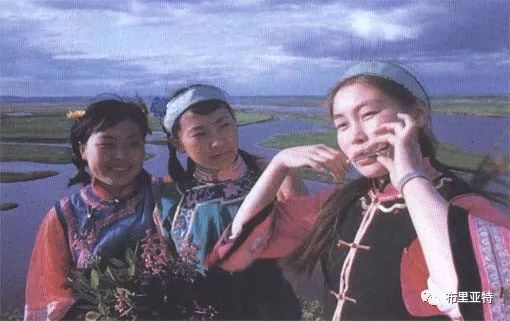
每一个民族的研究必须要做到完整和系统,因此有必要对覆盖该民族所有成员繁衍生息的地域的整体情况加以探讨,否则研究就难免有偏颇性,其研究成果只是局部的和没有普遍意义。研究达斡尔人,不仅要研究聚居于我国的达斡尔人,还要研究因历史原因而留居在俄联邦境内的达斡尔人。这就需要弄清生活在俄联邦境内的达斡尔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背景和现状。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笔者于2003年6月和2018年6月前后两次应邀参加了俄联邦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有关东北亚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国际研讨会召开的时间是:在会议研讨过程中,笔者有针对性地采访了多位社会科学院的俄罗斯专家、伊尔库茨克布里亚特专家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学术观点。
有一位资深的伊尔库茨克布里亚特历史学家Tatiya namihAilovna malanova说:“伊尔库茨克布里亚特由当初互不相关联的四个部落(或分支)组成。其中一支是由bohen家族、巴尔干斯家族和其他一些家族形成的,当地人称之谓“达斡尔布里亚特”。获得这一称谓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语言词汇里有较多的达斡尔语成份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习俗、服饰与达斡尔族相近和相同”。根据笔者多年从事研究达斡尔族的语言、文化、历史、族源、经济(主要是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方面)、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所得的结论与这两次赴俄联邦境内调查所发现的有关信息资料和所见所闻结合起来分析发现:组成伊尔库茨克布里亚特的四个分支中的“达斡尔布里亚特”这一分支是俄联邦境内居住的达斡尔人的一部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证:

一、语言学方面
从语言学方面来看,他们的语言词汇中保留着诸多达斡尔语单词,这方面与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和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相比截然不同,存在质的区别。如:夏天叫“那吉日”、鞭子叫“米那”、掛摇篮的皮绳叫“敖鲁宫”、雨叫“胡日”、接吻叫“敖吉贝”、道路叫“特日古勒”、佛叫“巴
日肯”、柳蒿芽叫“昆必乐”......等等,都与达斡尔语一模一样,而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和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语言词汇中无这些词语。

二、历史学方面
从历史学角度来说,达斡尔族迁居于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贝加尔湖周围的广袤地区经历了较漫长的历史过程。是达斡尔族的不同姓氏的部众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和不同原因,以同一个目标汇聚于一处的迁徙过程,这一过程按时间顺序叙述如下:
最早的迁徙发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4年)。这一迁徙历史事件的发生与达斡尔族的远古祖根鲜卑人息息相关。我国多数史学家都认为达斡尔族源于古代的“契丹”民族,但反过来说,“契丹”的前身是什么呢?李桂芝编著的用于大学历史教学的丛书《辽金简史》中讲述:“后世治契丹民族史和辽史者,也多认为契丹为东胡系统东部鲜卑宇文部之裔”[1]。“乌桓的渐次南下,南匈奴的内迁和北匈奴势力的衰落,使我国北方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其第一个后果就是鲜卑人的南下与西迁。鲜卑人起源于大兴安岭的中段与北段地区。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东麓发现的鲜卑石室,为早期鲜卑人居住地之一,它为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提供了可靠的证据。”[2]“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乌桓人南迁近塞,居于鲜卑山的鲜卑人南下到达乐水流域,占有了乌桓故地,这就是后世的东部鲜卑。居于大鲜卑山(即石室所在的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人也随之南迁至大泽(呼伦湖、贝尔湖一带),这是鲜卑人的第一次大迁徙。”[3]“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的乌桓入塞和永元(公元89—104年)初北匈奴的西迁,给鲜卑人带来了第二次大迁徙的机会。东部鲜卑势力发展到塞外,留居在塞外的乌桓人则逐渐融入鲜卑。迁居大泽的鲜卑人走出大泽,经过九难八阻,到达蒙古草原的西北部”[4]。广义的蒙古草原包括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周围的广葇草原地区。关于这一点,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G·N·Rumyanzev说:“贝加尔湖西边的安加拉河流域曾经生活过鲜卑人,至今还有鲜卑人耕作的遗迹。贝加尔湖周围曾经生活过达斡尔人,是达斡尔人的故乡之一。巴尔虎金地区有达斡尔人种过地的遗迹”。从这些历史记载和历史学家们的论述可以说明,当时在贝加尔湖周围、外兴安岭以南和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生活过鲜卑人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后裔的一部分——达斡尔人、蒙古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锡伯人......一直居于此地。这是第一次迁徙所留下的最早的达斡尔人。当然也有上述其他民族的先人。
第二次的迁徙发生于公元7世纪。上述提到过的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人南迁大泽时,在原居住地留下部分人看守故乡。这些未迁走的部众,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约在公元5世纪末,被中原史书称作“室韦”。
做为拓跋鲜卑遗裔之民的室韦各部,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靠狩猎、采摘生活。这些室韦部落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人口变得越来越多,生存空间也变得愈加狭小,不仅如此,当时的室韦各部还遭受着突厥属部的欺压。因此,室韦各部为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为了摆脱突厥属部的欺压,纷纷走出了原居住地,向不同地区迁徙。据考证,达斡尔这一部分先人的达姤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迁徙发生在唐初,分别奔向了东、西、南三个不同的方向,其中一部分沿着黑龙江向东迁徙,尔后进入了乌苏里江,与生活在今兴凯湖附近的一部分鄂温克人相邻而居。今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共同的姓氏“乌力斯”即来自于所居住的乌苏里江地区的江名。(“乌力斯”是达斡尔、鄂温克先人对“乌苏里”的变读)史载,7世纪中叶,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父子先后发动了两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唐高宗李治对曾支援过高句丽的靺鞨各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当时作为靺鞨十六部之一的鄂温克先人及与之相邻的这部分达斡尔族先人怕受到战祸殃及,沿乌苏里江,溯黑龙江,迁徙至精奇里江流域,他们依旧相邻而居生活。这些历史实事表明:东徙的这部分达斡尔族先人,早在1300多年前就已经生活在精奇里江流域了。
第三次的迁徙发生在公元12至13世纪,这一时期正是辽亡、金鼎盛时期。
辽朝灭亡时,多数契丹人融入汉族中成为汉人的一部分。但也有一部分人念念不忘自己是鲜卑人的后裔,并早就听说部分契丹属部和属国人生活在黑龙江流域,从而也往北迁徙,来到黑龙江流域与这部分人会合在一起。其中有一部分是契丹大贺氏部落人。
第四次的迁徙发生于17世纪中叶。
1643年7月,沙俄侵略者的铁蹄就踏入了黑龙江流域达斡尔人的家园。起初,善良朴实的达斡尔人热情地接待这些异邦外族人,并视为座上宾招待他们。可是,这些侵略者在吃饱喝足以后,抓捕达斡尔人的首领作人质,逼迫达斡尔人向他们交纳所谓的“实物税”貂皮,并抢掠达斡尔人的财物。当达斡尔人认清他们的豺狼本性后,在其首领拉夫凯、桂古达尔等人的领导下,毅然拿起最原始落后的武器,向入侵家园的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击,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和态度。
日本历史学家池尻登在他的著作《达斡尔族》中写道:“鉴于这种局势,清朝为了保护原住民,掐断俄罗斯侵略军队的粮源为目的,下令达斡尔及索伦族大力迁移到黑龙江以南嫩江流域。”[5]当时,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生活的达斡尔族共有三十多个姓的族人。靠近黑龙江北岸的二十几个姓的达斡尔人响应清朝的号令,迁到了嫩江流域。但是,远离黑龙江而居的部分达斡尔人,怕被沙俄侵略者屠杀,把自己说成是布里亚特人或鄂温克人而留在了原地(或迁徙到贝加尔湖右岸)。关于这一点,日本历史学家池尻登在他的《达斡尔族》一文中写道:“随着俄罗斯的高压,达斡尔族的一部分人离叛清朝依附了俄罗斯。其中根特木尔事件就成为清政府日后决心向北征战的原因之一。”[6]自贝加尔湖附近西迁的达斡尔人有阿尔丹氏、达斡尔氏(达斡尔族中的一个姓)、扎拉日氏、掛尔佳氏、祁布祁日氏的族人,还有少部分敖拉氏、莫日登氏、何音氏、鄂嫩氏、郭布勒氏的族人。
综上所述,第四次迁徙后,虽然多数达斡尔人都回到了国内,但还有一部分达斡尔人仍然生活在贝加尔湖周围地区和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其中,贝加尔湖以西、伊尔库茨克地区生活的达斡尔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这
一问题,鄂温克旗的娜牡丹女士给笔者叙述其母亲家族的搬迁史时说:“我母亲是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人。我姥爷健在时明确说过,他们这一家族是从阿穆尔州迁到伊尔库茨克地区定居的达斡尔人。”

三、民间传说和宗氏、血缘关系方面
从民间传说和宗氏、血缘关系来看,达斡尔族和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有共同的有关萨吉哈日迪汗的传说。Bohen和巴尔干斯家族老人说的有关萨吉哈日迪汗的民间传说和达斡尔族民间传说非常吻合。各个民族对于祖姓和祖氏的称呼上虽有不同,但都表达了远古祖先的共同地域和共同血缘的两重性,并且具有其世世代代的继承性和稳定性,它对于研究早期的氏族社会及其祖源,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
达斡尔族的“哈勒”相当于汉族的姓;达斡尔族的“莫昆”相当于汉族的氏。
达斡尔族(中国境内的)有二十多个哈勒,即:郭布勒、敖拉、莫日登、鄂嫩、鄂斯尔、陶木、德都勒、沃热、精奇日、杜拉尔、讷迪、吴然、索都尔、苏都尔、乌力斯、阿尔丹、鄂尔特、胡尔拉斯、卜图克、克音、毕力扬、何勒图、尼尔登、萨玛格日,其他还有清朝时期因立战功,被朝庭赏赐的外姓奴隶的加入而出现了刘、李、陈、田、徐......等外来姓。无独有偶,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也有郭图勒、莫日登基(merdengi)、敖拉基(aolgi)、何音格勒德基(hengeldgi)等姓。这与乌兰乌德的布里亚特和中国鄂温克旗境内的布里亚特有质的区别,而与达斡尔人的郭布勒、莫日登、敖拉、何音哈拉很相似,只不过后加基字。因为,俄罗斯文化中习惯上在人名、姓氏、地名后都加基、夫、亚等附加词的习惯,想必生活在俄境内的达斡尔人也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而记姓名时附加上述字词。如考斯基、捷尔仁斯基、奥斯托洛夫斯基等等。

四、经济学与生产方式方面
从经济学与生产方式来研究,16至17世纪以前(俄罗斯未越过乌拉尔山脉占据西伯利亚以前),在贝加尔湖附近和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生活的少数民族中除达斡尔族以外,其他民族都是以打猎和放牧为主的游牧民族,唯独达斡尔族是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定居民族。关于这一点,俄罗斯历史学家E·B·冈索维奇在他著的《阿穆尔边区史》中写道:“从波雅尔科夫的报告看来,在哥萨克第一次出现在阿穆尔河上时,他们遇到了沿勃梁塔河流浪的使鹿通古斯人;接着,遇到了乌尔河上的通古斯人,这些通古斯人已经饲养家畜;在乌姆列坎河流入结雅河的地方,他们第一次遇到了从事耕作的居民,哥萨克称他们为达斡尔人。”[7]这两次赴俄考察后笔者发现: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人也种地,他们使用的农耕工具和达斡尔人用的农耕工具很像。而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和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都以畜牧业为主。这也说明,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就是达斡尔人。从种烟程序和方法以及加工烟的工具、工序看,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和达斡尔族的种烟程序、方法以及加工烟的工具、工序基本相同。

五、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方面
从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来对比研究,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穿的民族服饰和达斡尔族穿的民族服饰很像,例如,穿的长袍前后左右都开襟;男人扎腰带的方式也和达斡尔人一样把腰带的两头别在腰部的左右两侧,其两头稍稍往下搭拉。另外,妇女的发式也有部分相似之处。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的居住院落格式和房屋建筑式样与中国境内达斡尔族的居住格局和房屋建筑式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包括围房屋四周建长方形院落,并用碗口粗的圆木扎成障子做为院套,有些房子屋顶处无烟筒,其烟筒设在房屋两侧。他们也和中国境内的达斡尔人一样,吃柳蒿芽炖菜,这也是他们传统的菜肴之一。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妇女穿着的服饰上刺绣的图案与中国境内达斡尔族的有相同之处。

六、宗教信仰方面
从宗教信仰来讲,他们也和达斡尔族一样信萨满教,他们也把萨满说成是“雅德根”,且“雅德根”的服饰中其帽顶缝有一只雄鹰。帽子周围还有一些毛絮儿,这些方面与中国境内的达斡尔族“雅德根”很像。而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的布里亚特人和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主要信“东正教”和佛教。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境内的达斡尔族的族源与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的族源是相同的。当然,这只不过是前期研究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察时间仓促,所见所闻有限,还需要继续做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最后的更加确切的定论。这里需要明确提出的是:由于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与俄罗斯族混居几百年,故其语言、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惯皆俄罗斯化比较严重,尤其是年轻人对其几百年以前的祖宗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语言也忘得一干二净。因此,俄罗斯的文化熏陶已渗透到他们的骨髓里。再加上政治和领土问题,官方始终不承认俄联邦境内有达斡尔族的存在,故一部分“达斡尔布里亚特”人中虽有承认原民族称谓的想法,但公开的民族成份确认时只能把自己报为布里亚特人。其周围的真正的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以及他们这一部分人私下里都认为这一分支伊尔库茨克布里亚特人应为“达斡尔布里亚特”。伊尔库茨克布里亚特的其他三个分支中伊赫列特家族和包鲁克德家族是卫拉特蒙古人。他们和中国内蒙古西部的卫拉特人至今有亲属来往。关于这一点,是俄联邦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资深历史学家tatiyanamihailovnamalanova和ъазар同时告诉笔者的。由于考察时间短暂,另外两个分支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需要继续探讨和研究。
还需补充的是:从祖传的家谱来说,中国境内的各哈勒都有自己近四百年的家谱,伊尔库茨克“达斡尔布里亚特”也有较完整的家谱;但是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和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虽有家谱,但都是新建的,只能将祖辈追溯到百年以内,这一点也是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作者简介:玉山,男,达斡尔族,呼伦贝尔学院教授,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历史文化(侧重达斡尔族文化)。
- 上一篇: 【呼伦贝尔】列巴与布里亚特
- 下一篇: 布里亚特女孩子出嫁前的一趟庄严必修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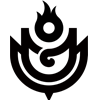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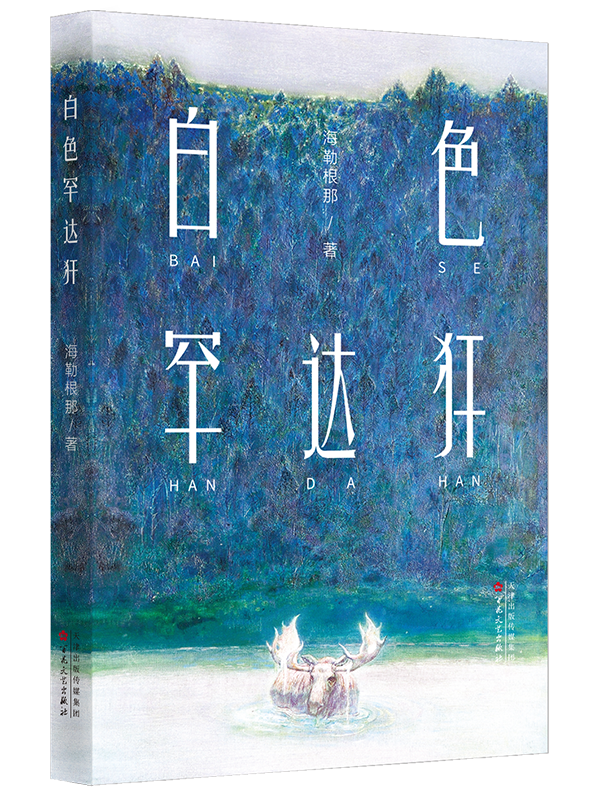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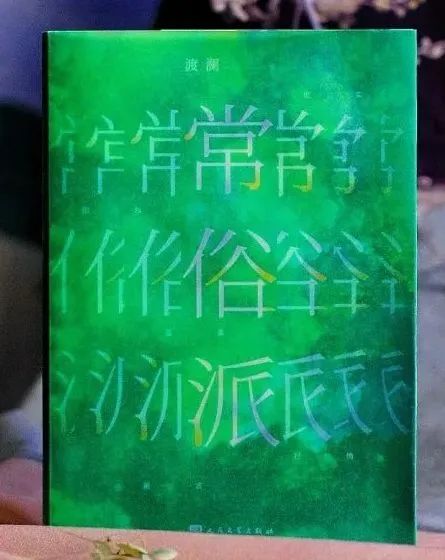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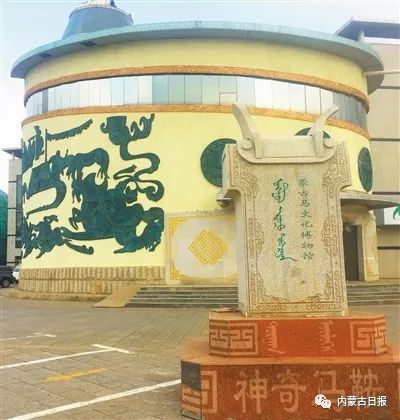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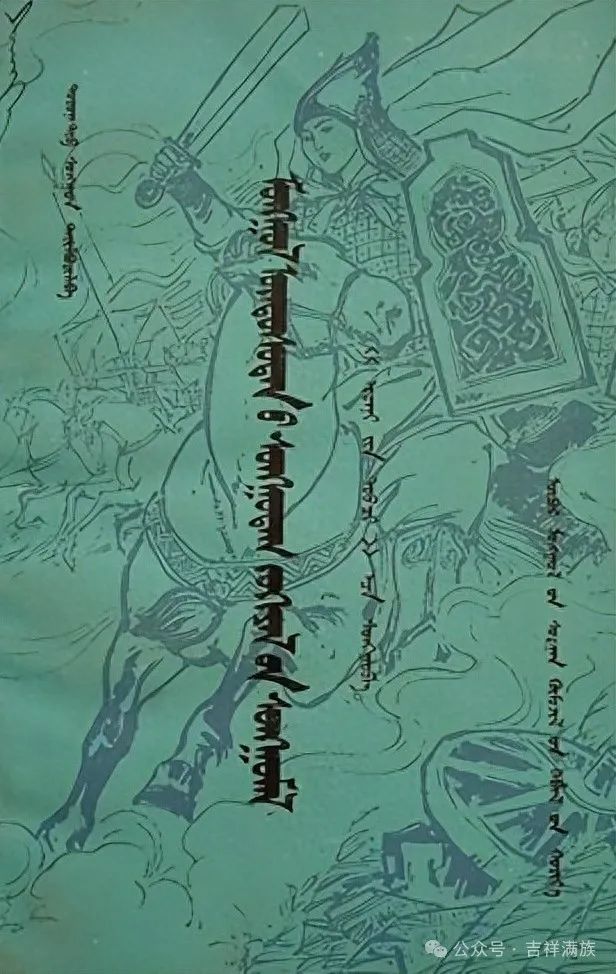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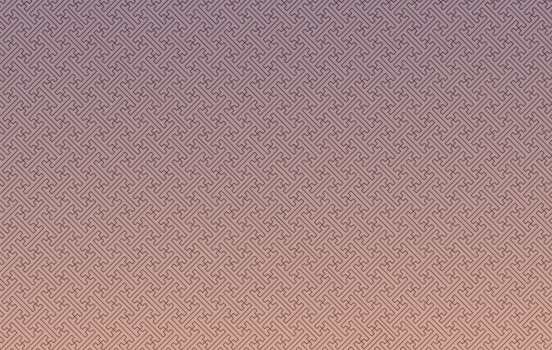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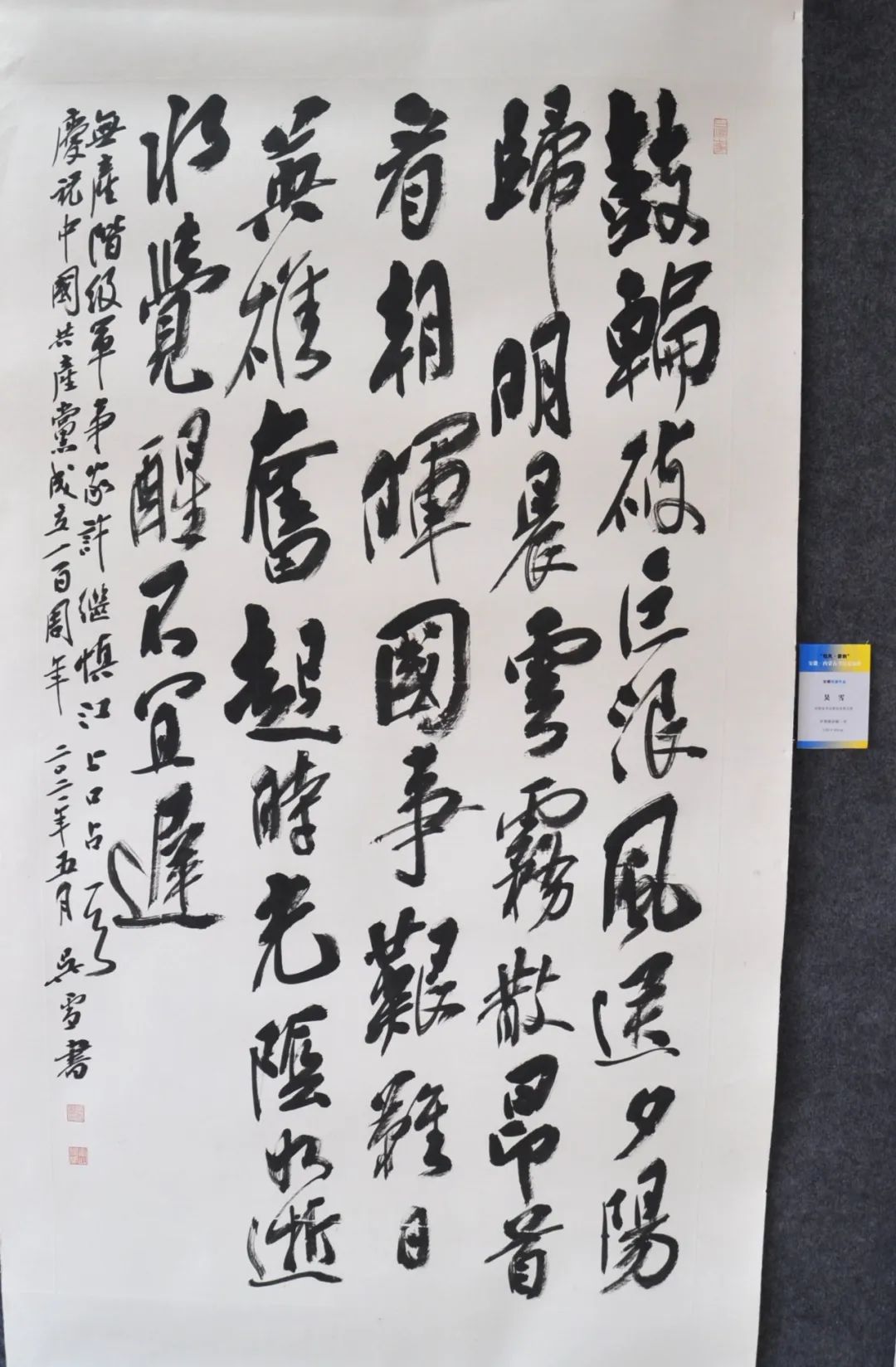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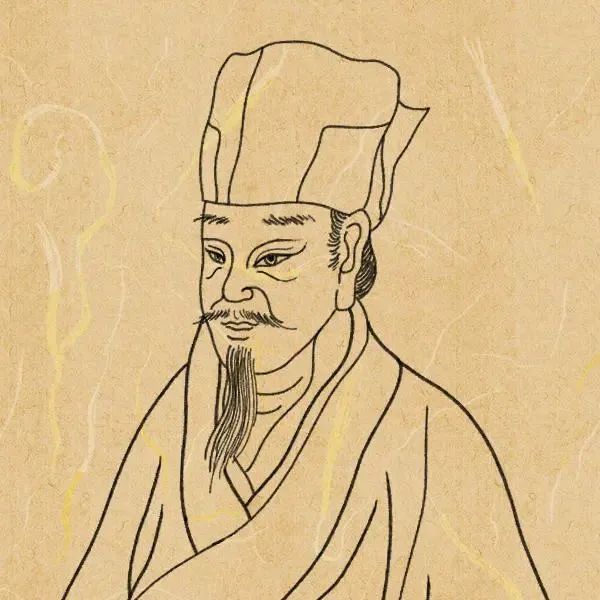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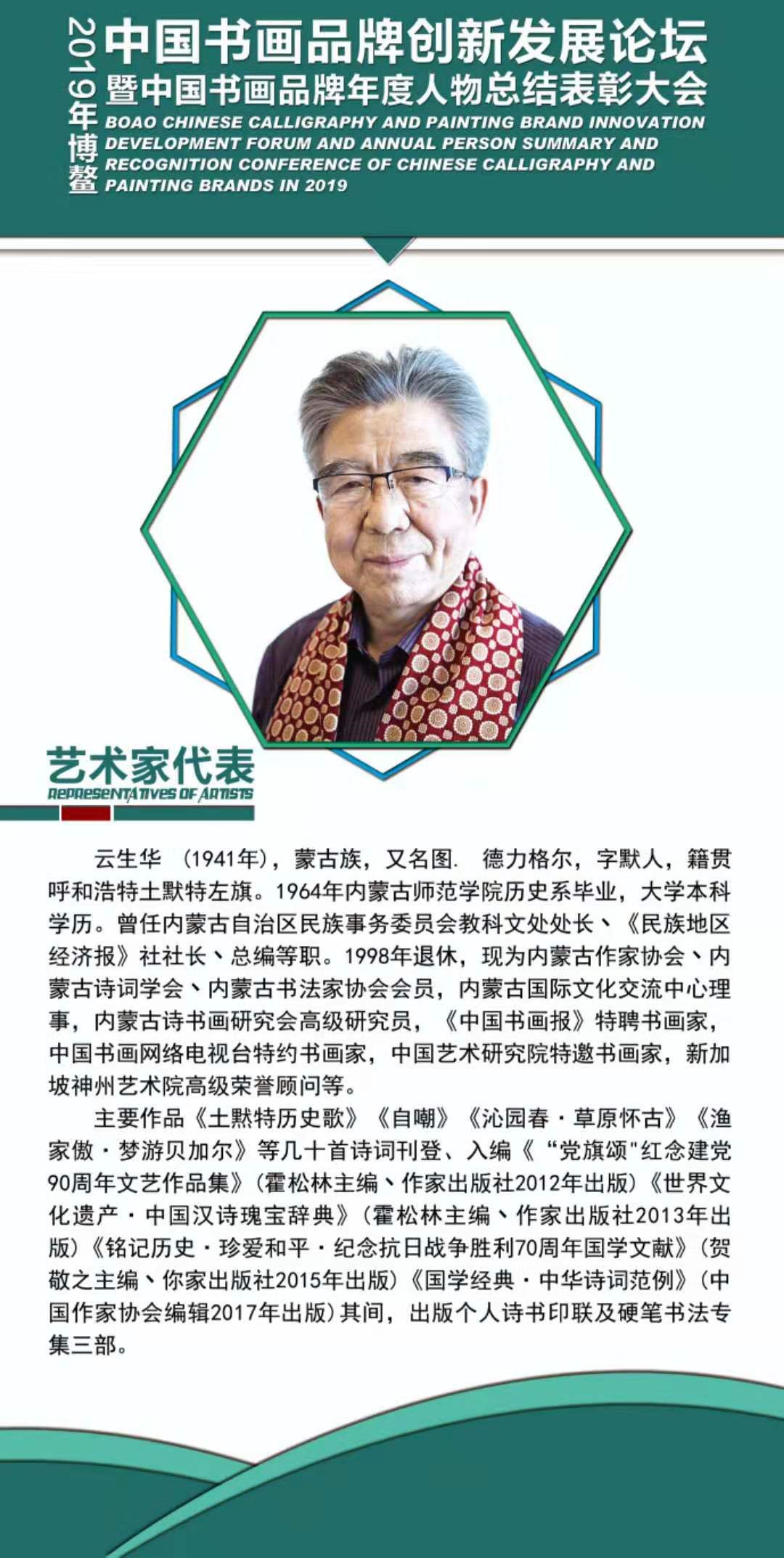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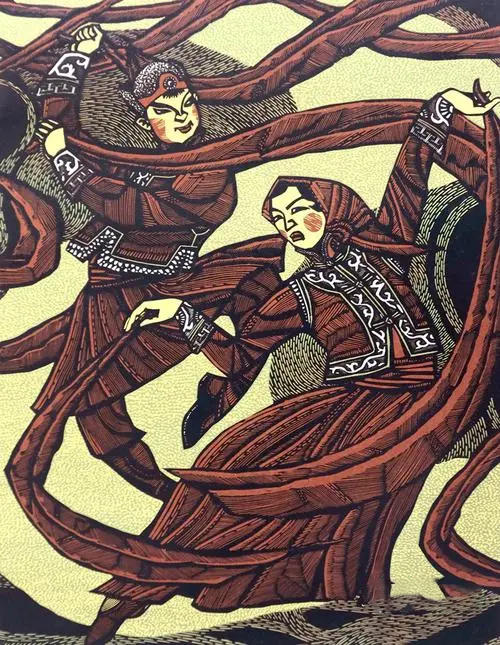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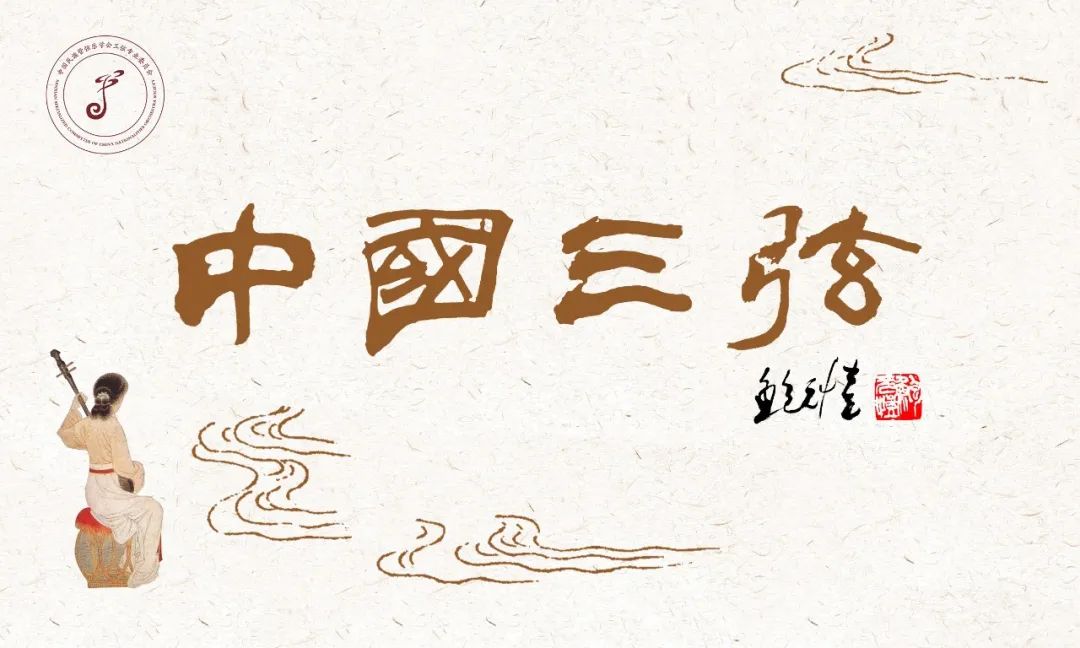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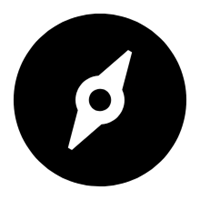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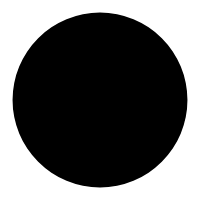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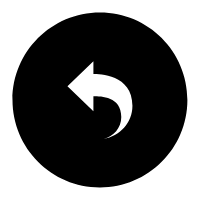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