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在盟委、行署的正确领导下,在内蒙古文联的有力指导下,阿拉善文艺事业取得了大发展、大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和优秀人才。他们辛勤耕耘,努力创作,为阿拉善文艺百花园催生了一朵朵盛开的鲜花,以文化人、以艺润心,彰显了新时代文艺价值和精神,共有35名作家艺术家加入了中作协、中美协、中书协等国家级文艺家协会,321名作家艺术家加入了内蒙古各文艺家协会。他们是我盟文艺创作的骨干力量和优秀代表,也是全盟文艺界学习的榜样。
为了使全盟文艺界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创作出更多文艺精品,涌现出更多优秀人才,盟文联从即日起,开设“阿拉善艺苑名家”栏目,推介阿拉善在打响北疆文化品牌中做出贡献的文艺家和代表作品。

个人简介
宝音巴图(笔名:纳·苏黎),1965年出生,蒙古族,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人,本科学历。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培训班学员。先后在阿右旗蒙古族中学,阿拉善蒙古族完全中学工作。盟级教学能手、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作家协会、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阿拉善盟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2002年散文《大地的烙印》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2008年获第四届全国“苍天的驼羔”诗歌朗诵会一等奖。2012年诗集《九宝之韵》获第二届全国“朵日纳”文学奖。2015年获锡盟黄旗文联举办的全国性“陶尔干察哈尔”诗歌朗诵比赛二等奖。散文《地火》获《花的原野》杂志社举办的《文学那达慕》比赛三等奖。《母亲的黑木箱》获中央广播电视台民族节目中心蒙语部和《花的原野》杂志社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蒙古文散文、报告文学征文大赛三等奖。《天箭》获由《花的原野》杂志社和锡盟文联合办的首届“巴图孟和”杯全国蒙古文短篇小说大赛二等奖。2019年《迷失的冤魂》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策克”杯《花的原野》文学那达慕大赛散文一等奖;《因果》获全盟“胡树其”杯短篇小说比赛二等奖。2001年获自治区学习使用蒙古文工作突出奖。2007年获“阿拉善盟十大诗人”称号。2008年被阿拉善盟文学艺术联合会授予“功勋诗人”。2016年,获蒙古国作家协会“文学功勋奖”。
2012年出访参加蒙古国国际诗歌盛会并进行文学交流。2017年应邀参加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37届世界诗歌大会。
主要作品:1986年开始用蒙文字发表作品。在《花的原野》《潮洛濛》《内蒙古青年》《鸿嘠鲁》《科学与生活》《锡林郭勒》《内蒙古日报》《十月》《南充文学》等杂志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800余万字。著有诗集《北斗星韵》(民族出版社,2005年),《九宝神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天堂之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沉默的背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1年)。散文集《大地的烙印》(民族出版社,2004年),《天之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人之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游动的印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1年),《心灵的光芒——宝音巴图的散文温和小说集》和《两棵树的爱恋》(散文集)。诗歌《我的母亲》、散文《大地的烙印》曾选入高中蒙语文课本,《鸣沙山》曾选入初中蒙语文课本。《大地的烙印》被译为汉文发表于《十月》杂志,同时选入《中国西部散文精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散文《大地的烙印》《此路漫漫》《微型散文》,诗歌《我不知道》《过去的将来》《人之本性》等译成斯拉夫蒙文、英文,俄文、德文等文字传播到国外。诗集《九宝神韵》《诗歌的安慰》《肖像诗》《慧树之果》和散文《草原风声》《梦开始的故乡》(英文版)等在蒙古国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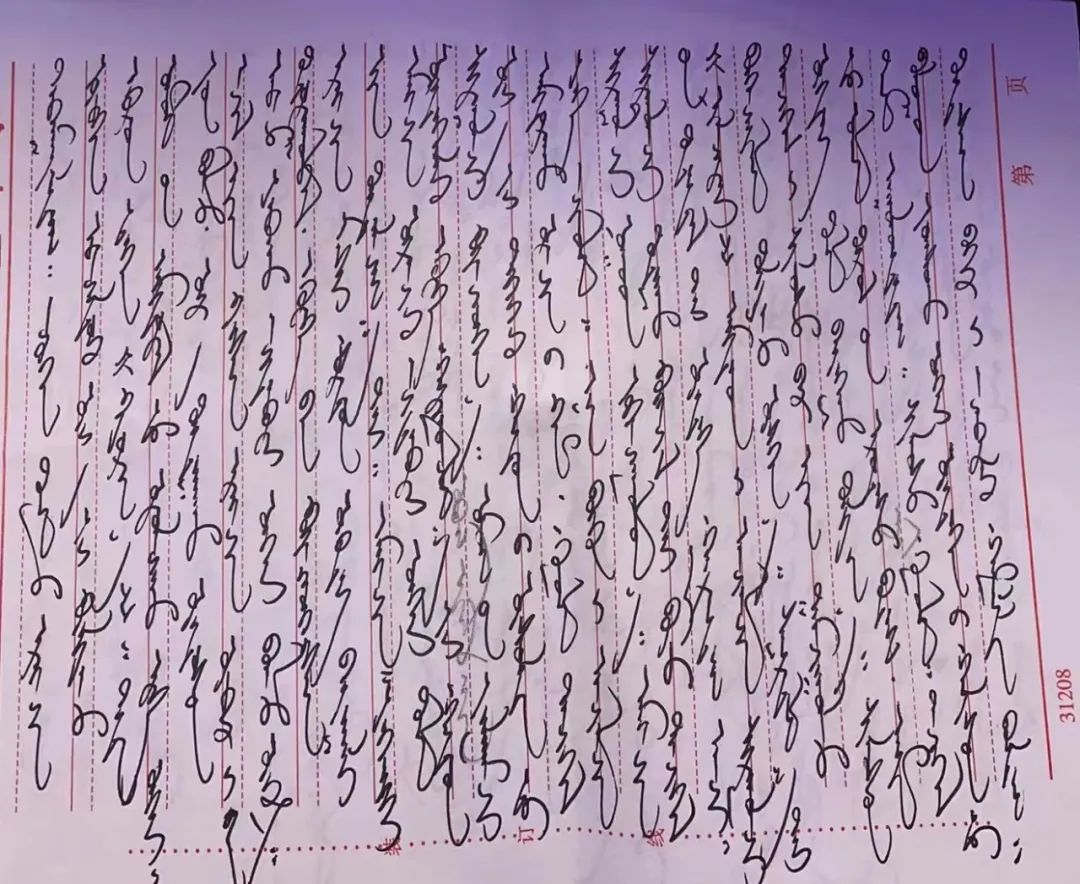
那一年我冒着酷暑回到久违的故乡。我家位于车辆犹似白天的星星一样稀罕的大漠戈壁之隅,我只好徒步穿越茫茫的戈壁滩。行囊里塞满了从城里买来的哄阿妈和几个弟弟的零食和礼品。我背着鼓鼓的行囊和从路边牧人家讨的一壶酽茶,趁着太阳还早,朝着自家的方向疾步走去。一望无际的金色沙梁犹似牧羊阿妈布满油渍的袍襟,在顽皮的戈壁蜃幻里绵延起伏着,迷迷蒙蒙的。
当姗姗西沉的一轮太阳犹似天空中独颗红色的痣寂寞地悬于西部远山顶峰,金色的铁莫图高原沐浴在一片火红的霞光之中时,我来到了冬营地的家园旧址上。由于家里人赶着畜群上了夏营地,这里空无一人。
我家蒙古包的遗址依旧清晰地跃入眼帘,像一轮月环。家乡的老人们称毡包坐落过的旧址为大地的烙印。大地的烙印,是啊,他就是一记大地的烙印,就像一枚圆圆的印章烙在那儿似的,真实而又生动。
我像个来自远方的客人一样盘腿坐在“大地的烙印”的西首,喝着茶,抽着烟,一股温暖而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我曾经的家园啊。灶火余烬似乎还在,温温的。地灶左边有一只羊拐骨(羊拐即羊踝骨,宽凸面叫背,宽凹面叫心,窄凸面叫目,窄凹面叫耳。蒙语中分别叫做绵羊、山羊、马、骆驼,多用于羊拐游戏)以马的形状面朝北立着,犹似嘶鸣的马儿在怀念远去的主人。看得出来,这只羊拐骨原本是用锁阳(一种沙漠植物)的汁子染红的,如今在烈日疾风下已经变得枯黄。相传,羊的踝骨留在故土上落成一匹“马”,以从六百公里远的地方都能够听得见的声音嘶鸣着呼唤主人,一等就是三十年。因而,蒙古人只要碰见落在牧人家园遗址上的“马儿”小心翼翼地捡了起来,无比珍爱地揣在怀里。
我向一半已被沙子覆盖了的驼圈举目望去, 二十几年前,我家遗弃了这座冬营地,寻找了一处理移动的沙丘较远的地方开辟了新的冬营地。然而,那桀骜不驯的沙魔犹如脱缰的公牛一样疯狂地撒野,不知不觉就逼到了驼圈后墙。待我们赶敖特尔从夏秋牧场游牧返回来的时候,圈栏的一半已被沙子埋没。为了挖掉那些沙子,我们一家老小要折腾好几天的工夫。到后来那些移动的沙丘干脆就挡不住,把整个圈栏都给埋住了,小范围的这一场人与沙漠的战争最终以人的失败而告终。百般无奈的我们只好再度迁移他处,被无情的沙漠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就这样,我们家族三代人不移牧场在一个地方扎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地方曾经是儿女成长、驼畜繁衍的福祥家园,而如今却······”母亲含着热泪说着这些话,将蒙古包卸下来驮在驼背上,向家园遗址祭洒着奶汁,充满悲情的告别故土。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然而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历历在目。从那时起,我去远方求学,像一个来去无影飘忽不定的游客一样在这条戈壁小路上来回往返,一眨眼就是二十几年。那时候我还小,是个还没上过学堂的黄毛小羊仔。如今已经历了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见了些世面,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城市里背靠桌椅素面朝天,消磨着青春岁月和平淡的日子。似水流年,过得可真快啊,岁月犹如顽皮的驼羔一样,一蹦一蹦地离我们远去······
我怀着沉重的思绪走到空荡荡的圈栏跟前。这里曾经是驼羔欢叫奔腾、驼奶香气扑鼻的喧嚣之地,远远地就能看得见那片紫黝黝的圈栏围墙。而如今这在岁月深处默默静立的牧营似乎依然能闻得到那杜松、檀香之香味所不能比拟的缕缕暗香,沁人心脾。虽然主人已经搬走了,但往日生活圆满的烙印却完整的流了下来。
蒙古包座址、圈栏遗址,还有蒙古马的蹄印,都是大地的章印。在蒙古人游牧生存过的地方,这些“章印”都留下了永恒烙痕。回想起用毛毡子围蒙的大东方洁白的圆印,从东方大地一直烙到太平洋彼岸的遥远世纪,我的内心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点奶汁的甜味,又有一丝胆汁的苦涩。那时候,那一枚刻有“以苍天的力量······”字样的帝国玉玺所到之处畅通无阻。而那代表和象征了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力量的帝王玉玺如今在哪里沉睡?也学已经和它昔日的王朝一同一去不复返地湮没于历史的深处。只有这守望着祖先家园的大地烙印——毡包遗址,寂寞地留了下来。大地的烙印,我们从蒙古故乡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寻找得到它。我从许多古今中外的游记中读到,在古老的帝都哈拉库伦遗址上完整的留存下来的只有一座青蛙石雕和一片毡包遗迹这两样历史的见证物。蒙古包的遗址是苍狼大地永恒的烙印啊。
蒙古人曾经豪情万丈地向世界宣布“这就是我的家园啊!”并把生命的印痕烙在了脚下的土地上。曾几何时那叱咤风云的铁血传奇已成为了草原的往事,然而这大地巨大的烙印在多少年的风霜磨砺中都不曾消失,在苍天之下书写了永远的辉煌和奇迹。
而今天,帝王的一颗玉玺对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的是在辽阔的故乡任何一处都留有温馨烙印的和平家园。从毡包天窗享受明媚的阳光 ,从她的哈那(蒙古包木质墙)墙眼眺望世界,美丽的生活像在火撑子之火上沸腾的这大地洁白的明珠,在这圆月弯刀般的钢圈烙印上包容着马背民族的历史、传说、文化和思维,同时也包容着这个英雄的民族不屈的呐喊声。
蒙古民族是一个有着圆形态文化沉淀的民族。蒙古包是圆的,火撑子是圆的,畜圈是圆的,马蹄是圆的,就连牧鞭在空中卷起的弧形和在马背或驼背上呆久了人的双脚走路的姿势都是圆的······蒙古人甚至把宇宙变幻也认作是圆的。于是就像地球环绕着太阳旋转一样,他们在祭拜天地祭拜敖包的时候,也要顺时针环绕敖包三圈,在赛马、赛骆驼的时候先朝着吉利的方向环绕祭天香坛三圈,在游牧迁移他地时环绕家园三圈,以祈吉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奇怪的是,这种原始而朴素的民俗与宇宙行星的运动规律竟是惊人的相似。众所周知,圆周是始发点和终结点最后走到一起的几何图形。人类的历史和大千世界的发展规律也是如此。当人类文明发展到它的巅峰时期时,因由自然的或自身的灾难劫数,而将又重返回到自己的始发点,宇宙的所有一切也将返回到原始形态,这就是圆周文化所包含的深远哲学思想。蒙古人就是这样一群驰骋的蓝天这人。他们一个个都是星相学家,而他们的这种哲学无疑是从大地的烙印开始的。
我在家园旁边的灶灰堆前静默了一会儿,信步来到一座名叫乌兰啸仁的又高又尖的沙丘顶上。北方清新的野风争先恐后地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在城市的喧嚣和工业烟雾中晕乎不堪的身心之疲劳似乎在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西南边冬营地房舍犹如挑担子买卖人的筐子一样无精打采地耸拉着。我们戈壁人入住平房还是前不久的事。其实,先前我在冬营房子的阴凉处乘凉片刻再走也是可以的,但是蒙古包的遗址——那苍天般的大地烙印深深的吸引了我,使我情不自禁地走到了这已经被主人遗弃的家园废址上。站在乌兰啸仁的顶上可清晰地看到那些荒凉的圈栏和立着三块鼎锅时的毡包旧址。记得有一次,我们兄弟几个想把那鼎锅三石搬过来玩耍,母亲一听变了脸,大声呵斥道:“你们敢!那是祖先的家园守望石,不可以随便搬动。鼎锅石是刻在大地烙印之上的三个字,印章哪有无字的印章······”我永远也忘不了阿妈说这番话时的威严而深沉的目光。鼎锅三石怎么就成了大地之印上的三个字,我当时没弄明白,也没敢问母亲,在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不解之谜。现在我似乎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也许,那就是“蒙古人”三个字吧,我不知道。我把旅途的疲惫忘在乌兰啸仁沙丘上,继续赶路。似猫须般的几颗沙竹仿佛在沉思着什么,抑或是向我点头致意,在风中轻轻的摇曳。我的故乡就没怎么下过雨,与风调雨顺之年久违多时了。儿时的那些茂密得犹似骆驼跪卧的黄蒿、芨芨、霸王草和沙拐草丛如今以消失得无影无踪,要说二十年前这里是如何如何的芳草萋萋绿色遍野,连鬼都不信了。大自然是多么的脆弱啊,在如此短暂的岁月里竟然变成了这个模样,夜夜入梦的故乡似乎一夜之间黯然失色。这是真的吗?此刻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瘦成了皮包骨的几峰母驼领着驼羔安详地卧在太阳风下反刍着。骆驼的眼里有泪水。相传,骆驼是爱流泪的动物,现在大概更加爱哭了吧。我多么想用骆驼的眼光望一眼故乡啊。童年时代,门外奔腾着驼羔,奶桶里溅溢着奶汁,偶尔丛蒙古包哈那墙眼向外眺望,只见一片茫茫青雾横渡漠野,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童年啊。而如今······如今不要说挤几个母驼的奶了,连驼羔也养不活了。唉,我童年的故乡一直成长在梦的岁月里,不知不觉竟到了如此境地,悲啊!我想起了弟弟前不久给我写的一封信:“故乡一年比一年旱,不得不游牧他地,而且游牧的次数比以往多得多了······说不定哪一天一驼群一不留神就从大戈壁消失呢······现在把失去了骆驼的人家都往农业灌溉区搬迁呢,牧驼人家要学种田了······”
这样,蒙古人新的旅居生活要开始了吧。被几百年的岁月风尘吹打得精疲力竭 的蒙古人的游居生活难道还未到结束的时候吗?难道他们命中注定要永远地在历史的风景中飘忽不定地游走吗?那么现在把我们明月般的大地之印要烙在哪里呢?
蒙古人从毡包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四方形的砖瓦房,昔日辉煌的蒙古包如今已是空荡荡的,因为它们的主人已经涌进了城市,移居他乡。而蒙古包也成了一种怀旧的象征或民族风情的见证,更多地出现在旅游观光区或都市饭庄里。听说,在美国的大城市纽约也出现了蒙古包,成为那些金发碧眼人的娱乐场所,有的人甚至为此感到自豪,说蒙古包已经开始在繁华地球金色的怀抱和霓虹灯下的不夜城里过夜了。
只可惜,搬到纽约的蒙古包,它的主人并不是蒙古人。想来,蒙古人引以为自豪的大地之印虽然越洋过海在太平洋彼岸落了脚,然而那“印子”的主人却已改变,在人们的眼里成了财源滚滚的“摇钱毡包”而已。那么,曾经的帝国玉玺如今难倒成了异域人手中把玩的观赏物了吗?纯洁无暇的蒙古包变成了银色的宝葫芦,离开主人孤独的远去了吗?穿越了千万年风雨沧桑的毡包宫殿难道从命运的脊背上滑落了吗?蒙古包是大地的一颗洁白的痣。据说白痣最容易被弄脏,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一点点地被玷污了······
天边漂浮着一片厚厚的白云,是蒙古包飞到天上了吗?突然,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那一枚大地的烙印正在渐渐的远离我们而去。誓要把宇宙坐穿的誓言已经被昨夜长风吹走,火焰燃舞的故土上我们还能够留下什么呢?在不知不觉中,正在失落我们原生态文化的人们,现在还需要什么?
啊,我看到了如大地银钉一般矗立在视野中的蒙古包,似乎闻到了炊烟的味道和奶茶的芳香。我仿佛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修补着骆驼缰绳蹒跚起立的身影,又仿佛听到成熟了许多的弟弟们轻轻的叹息声。大地洁白的毡包烙印似乎向我跑来,又似乎离我远去······
灭亡,我最亲爱的灭亡,我们奔你而迁移着。人类的末日,在等待中,急不可待地欢跳着。毁灭,我最挚爱的毁灭,我们迫不及待地尾随你。灵魂被折磨的地球摧毁,手捧哈达迎接我们。终点,我最尊敬的终点,我们嫉妒而暗恋你。历史与未来的终结,微笑着招引我们。死亡,我最绚丽的死亡,我们不顾忌一切地走进你。大自然永久的覆灭,像食苗虫似的招引我们。
人间最后一条小鱼,嘲笑人类的愚蠢而紧闭双眼。地球仅此一棵树苗,愤怒人类的贪婪而撕碎叶片自焚。天空中唯一的雏鸟,惊叹人类的丑陋而拔光羽毛裸奔。江河仅存的一滴水,洗不净人类的堕落而飞向外星、不归之路!
贪婪,好似牵着温顺驼的缰绳,缓慢地牵引着我们,向衰落、破碎、灭亡——恰如乌龟——不知不觉地迁移着。
贪婪,是一切罪孽的“永恒的巢穴”。
我们在超载的罪孽中,向漆黑的地狱——不管是否情愿——如驮着超重货物的驼队,摇晃着前行。
人类贪婪的列车,早已呻吟着启程了。它,只有一个驿站。那就是灭亡。
贪婪的根源,是人的本性。贪婪的旅程,则是苦难。贪婪的边境,竟是灭亡!
地球,是母亲,是眼睛。
我们却在惟一母亲的胸膛上,东钻西挖,使她失明。
地球,是苹果,是奶牛。
我们却分割她,啃食她,抢夺着吮吸她的乳汁……使她变成了干瘪瘪的皮口袋。
时间与距离,从人类醒悟的边缘,已起航远行。
思念的价值,已从幻想的警戒线,走出去很远。
当我们忘记历史,面对自己的丑陋、泪水变成鳄鱼的眼泪,觉醒自己从哪里来、又走向何处时,或许会感到世间的末端,竟是死亡之路……
我们微笑着,吃喝着,欢愉着,玩耍着,兴奋着,疯狂着……也许就会这样消失。(这或许是佛祖恩赐于我们的福分,或许是悲剧乐章的前奏曲!)
我们高歌着“地球母亲”,吟诗着她,宣言着她,宣传着她……却在吞噬着地球母亲。埋藏着自我。(这或许是,说与做,永远无法统一的,我们本性的宿命吧!)
我们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留意,什么都不爱惜,什么都不设想,什么都不信仰,只在“任我做,胜过天”的肆意中,将未来逸想成今朝、将明天幻想成昨日,或信奉自己乃万能者,用高傲狂妄慰藉着自己,在“有而无,无而有”(就这样掠夺着子孙后代们的福气)的意念中,带着无尽的懊悔与内疚,将消失在悬崖沟壑里。(这也许是我们过于冷酷无情,过于自私暴利而导致的孽债吧!)
我们。就是我们,在二氧化碳漂浮的天庭下,在有害分粒子蔓延的大地上,在黄沙肆虐的包围中,在无穷享乐的幻想中,在索求膨胀的忧愁中——在小小“蜥蜴”脑壳似的“地球村”里,如拥挤的蚂蚁,为了生命的延续,抢夺着土地、掠夺着资源而生存。尽管如此,这个“村”的人,却无休止地相互歧视、彼此挑衅,永不停息地侵略对方、彼此残杀。
造孽,人类从未在意过它。当面临死亡,灵魂却在发颤,才会走进庙宇……在佛祖面前,腰弯得茶壶似……向上苍祈祷……但为时已晚。地狱在这边,抑制不住地大笑。
违背了誓言的人,上苍都会鄙视他。对享乐着魔的人,魔鬼都嫉妒他。被破坏、侵占诅咒的人,死亡正走向他。被斗殴、阴谋笼罩的人,他的大脑已枯竭。吃尽食物,往碗里吐唾沫的人,他的命运之神早已弃他远去。
真正的恶兽到底是谁?是狮子?还是狼?不是,是人类自己。
(人,是野兽性与人之本性的连体,野蛮与文明的尺度取决于哪个略高一筹。)
(人,是佛与魔的截线,宇宙的命运取决于哪个战胜于彼此。)
人类,擅长将一切臭名嫁祸于他人。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占为己有,将罪恶全都推诿给他人的高手。这一切的一切,不管是百舌鸟还是蚰蜒,它们一清二楚,也能公然作证。
世界上凡是能吃能观赏的:花草、树木、五谷、果实……人类早已成为它们的“主人”,吝啬在园子里,不要说让苍蝇靠近,就连细菌骚扰,都令他们难以承受。
成千上万只鸟儿,筑巢繁衍,鸣唱大自然“交响乐”的自由家园——森林,我们强制地将它掌控,监督。我们用它做柜子,做棺木。还用它盖房子,点火引烧。
我们从白云连绵的草地、星星乘凉的河流,抢夺了牲畜、羚羊群的一切。在土地上,我们盖茅房、挖窖、脐带脱落、埋藏尸体。用水源,我们种植粮食、和泥、擦洗鼻子、清洗血渍……
从昂首仰望天空、目睹历史变迁的山脉,我们将飞禽走兽、山神占为己有。
尽管如此,人类从未满足过。在哪里,餍足欲望,运走原石,发泄欢愉,绺窃腹地,秘藏军队、弹药,还“仗势欺凌” 着花草。
鸟儿飞翔的天空,星星穿梭的宇宙……已是我们的。在哪里,我们驾驭飞船遨游,喷洒烟雾。发射火箭,较量彼此的强大。
海洋湖泊,我们毫无顾忌鱼虾的存在,将它掌控在“手掌里”。(因为我们是个将不知廉耻及愚昧,扔在疯狗嘴里的圆团)。
在哪里,我们划船。从哪里,我们获取食物。
五畜的幼崽,我们从没让吃饱过母乳。我们偷吮着。用这乳汁,哺乳自己的孩子,酹祭愿望,解毒,满足着胃口。
未到终结,未到止境。
被视为思念象征的银色月球,如今人类却,像切西瓜似的将她七切八分——各自占领命名——抢夺分割。向浩瀚的宇宙,肆无忌惮地“进军”多年。(对这无休止的“占领侵略”,只有上苍明了何时才是终结。)
人类的足迹,从未烙印的原始土地,宛如上苍最后之谕,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难以觅寻到。
未到至极,未到尽头。
从天堂到地狱的距离,从世间到宇宙的辽阔,从万物到微尘的零落,从阳光到空气的空洞……人类,统治着一切、政权着所有、奴隶着全部。
遐想飞到的地方,手就能伸到——从这个意义上,人类,或许是宇宙间绝无仅有的奇迹。
手到之处,一切骤然间变模样——从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智慧,或许有着难以想象的魔力。
对恭维不敬者,毁灭性地镇压(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从这个意义上,人类,或许是个无法复制的权势顶峰。
被视为障碍着,将他镇压,将他跪拜于自己的脚下(不管是山岭还是海洋)——从这个意义上,人类,或许是傲慢的极限。
世间万物,理应是人类的;山脉森林,应为人类温顺地服务;蚂蚁开洞,需人类许可;鸟儿唱歌,须人类应许;羚羊繁殖,祈求枪林恩惠;山羊出场,恳求政府允许。
世间唯一的主人,理应(也许是无可非议的)是人类。他,决不允许有其他的主人。如果谁幻想成为主人,与他决一雌雄的战斗,他,随时准备着(会不顾一切的)。
一切能获取的,凡是能得到的,一切能占领的,凡是能享用的,人类早已于自己权限内收复,枷锁。如今,只剩下向死亡进攻了。
为了超越彼此的生活,人类,无时不痛苦。贪婪地互相攀比、嫉妒、轻视、敌对……甚至相互厮杀,向灭亡的边缘轰隆而去。
财富,权利,名誉,欲望,或许是人类永不懈怠的追求。人类的根源,远比这“钻燧”。(人,这个动物,有过百分之百的满足,从他归天的灵魂,都难以寻找到)
就像初之雪,被人类的呼吸污染似的,不要说人类的魔爪,就连人类幻想窜到的地方,一切都瞬时被污染。
我们,如黑笔芯,一路污黑而来。狭窄的胸、恶意的心,化作黑乌鸦,翱翔在洁白的天空中。但我们却未察觉到,那只黑乌鸦,竟是我们贪婪的化身,却诅咒它、厌恶着自己的黑影子。
(乌鸦与人,到底谁最黑?虽说乌鸦黑,但对自己的幼崽、对大自然是纯洁的报啼鸟。但是人,不管是在乌鸦的眼里还是在针茅的眼里,却从没被看作是洁白的!)
猪,不是自己想肥胖而肥胖。不是喜欢筑起圈棚,混杂于尿屎中,除了吃喝“无所事事”地躺着。将猪变成这副“模样”的“罪魁祸首”,无可非议是我们自己。还在狼吞虎咽它的肥肉时,将懒惰、可恶、脑残、命运欠佳的……耻笑为“蠢猪”,又何足挂齿。以此类同,将鸡狗等动物的天性磨灭,把它们比喻成丑陋的化身,满足自己的猎奇心,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之事了。
这,不是人类的弊病,而是习性,确切说是人类真实的本性。
猪与人类,到底谁愚蠢、谁阴险,在时间秤砣上说事的计时,也许即将来临……
佛祖祭坛前点燃的千盏灯,一丝都没能将罪恶人的心照亮。人,不是从外表而是从内心需要,照耀。
将大脑,交付于“金钱元帅”;被贪婪,长生不老似的俘虏;用今朝的幸福,交换着明日的苦痛;忘记给予,只知索取的“竖立动物”;将摇篮我们的蓝色星球,凌辱得七零八碎;慷慨赋予我们空气、水珠、太阳、土地、草木的星球,虐待成疾病的“前言”。
哎呀!请你们静听:金属世界“饥饿蜥蜴”的牙缝里,我那苦命的地球母亲,每一天,都在难以忍受地呐喊挣扎着!被高傲愚蠢的“地狱”爪子撕碎的她,每一刻都在祈求着保佑,我那哀痛的蓝色星球!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悲惨,我们的苦痛已微不足道。当我们面对地球的崩毁,我们的灭亡早已微乎其微。
世界三大宗教,未能净化人类的本性、拯救人类。
非凡而完美的教诲,未能开化人类的智慧。
释迦穆尼、耶稣、穆罕默德,对人类信任的背叛,感到厌恶沮丧,被迫做出用正义之战,拯救人类的决策(也许是决定)。
人类,宇宙“黑脑壳虫子”(说是上苍之称)。
祭拜佛祖,用钱银供奉;驱赶妖魔,用钱财迎合;安抚亡魂,用纸币超度;祈求福分,用金钱指引;驱逐罪孽,用钱币指路……想用金钱解决所有。
不要说世间的万物,就连微妙的细胞,甚至畸形的预兆,都想变换为金钱而茫茫行星,发出耻笑的光芒。
以发扬的名义,将本性践踏在脚底下;以兴盛的名号,将故乡埋葬于十八层地狱下。
将上苍与佛祖,驱逐到委屈、厌恶的边缘,反过来像啄食的小鸡,忙着弯腰磕头,祈福。
佛祖手足间,不知用什么途径弄来的几张“斑驳纸”敬上,竟妄想洗净自己的罪孽。好似贿赂法院的判决,能逃脱了似的,闹腾着。
我们,为了明天,交换今天而活,(真因为这样)在今天与明天里,我们无存生活过。永不死去似的生活着,最终却在无存生活中死去。“万物智者”悲惨的夙愿,就这样,像年复一日的茶饭或愚昧之人的错误,重复着。
开采,砍伐,捕捞,消耗时……跃跃欲趣。
“真理门前,谎言驾临”,压迫真理、让邪恶猖狂。
濒危时代黄金锁门,被敲响的噩兆,或许这样临近着!
被丑陋、恶毒、贪婪、狡猾深侵的人类本性,令安康的山脉作呕,到了喷吐烈火的地步。韧性的大自然,抵不住人类形色的灾害,无奈地摇晃起脊背。
人类灭亡的“狗吠声”,也许就这样逼近着。
人类,将本性的光明,用野蛮的贪婪撕碎;智慧的蕴藏,为囤积财富绞尽;令远古苍穹给予我们的美丽富饶的世界,变成了嫉妒、门路、奉承、贿赂、偷窃、枪杀、掠夺、侵占、淫秽、愚昧的毒瘤繁衍的垃圾桶,向灭亡的终点,如发射的子弹、安息的生命,紧握不归旅途的缰绳,将岁月抛弃于身后。谁也解救不了我们。佛祖挽救不了我们,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更拯救不了我们。
宇宙沧桑,或许变成燃烧的火球;海洋湖泊,或许变之百沸滚烫;永恒的生活,或许变成瘟疫繁衍的巢穴;宝贵的生命,或许成为苦难的游荡;未知的命运,牵着“鞍鞴的马”等待着我们;谜语似的未来,在我们醒悟的每个细胞里,敲响警钟!
但是……可是……
所谓高智商的人类,做了梦魇似的,未将这一切放入心。
就这样,“聪明”行走。我们已,一无所剩。只留下,向地球母亲宣誓的了断了……
如今,我们在随时爆发的火山口上,拥挤、任性、迷惘,甚至举杯,一起兴奋着。
厚颜无耻的动物,是人类。
罪孽的眼,想用纸蒙骗的,佛祖慧眼下暄软的“穿衣服的猴子”,是人类。
吮吸着宇宙万物精华,无尽止繁衍生息的“世间红虱子”,是人类。
为了索取而发狂,将周围掠夺一空的,慧眼被蒙蔽的大自然杀手,是人类。
无所无知地,令智慧变愚钝。无所无爱地,使心灵之花熄灭。迷失于苦难的荒野时,为何要委屈。淹没于痛楚的苦海时,为何要悔恨。夏季三月,不该遐想为六月。活不到百年,为何要积累千年的资产?幸福流逝,福分告终,苦难竟未终结。
宇宙,从无有过永恒。永恒不了的宇宙,围绕爱的轴心旋转。爱荒芜的世界,充满遗憾、分离。给予我们一切的苍穹,我们需要用挚爱爱她。
当尽有一滴水枯竭时,当仅存一粒米消化时,当仅此一棵树跪倒时,当尽活一条鱼闷死时:
我们需要什么,什么又是无价之宝?孽债为何那样的苦痛,在生死最终天平上,我们有所醒悟时……在宇宙的终结里,将会“幸福安康”的!
至此,人类需要考问自己!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请你们静听!天在呐喊……地在呻吟……哎呀!我们情愿向毁灭……向灭亡……向覆灭……向终点……丁当,丁零当啷地跚跚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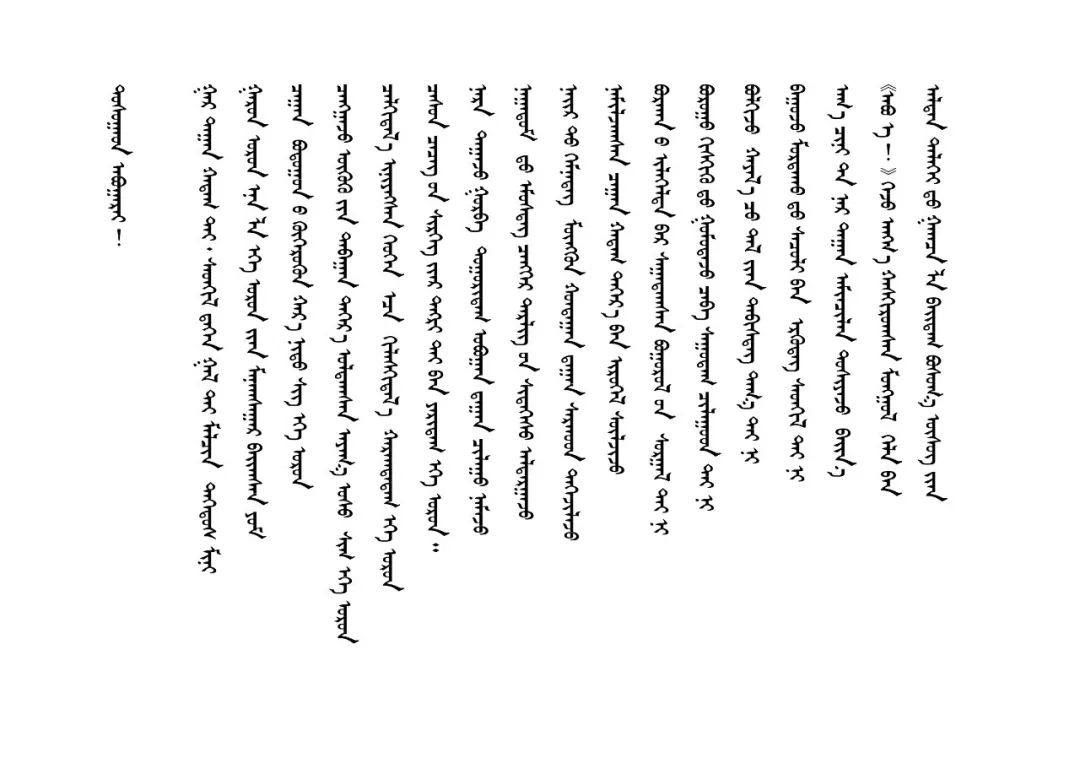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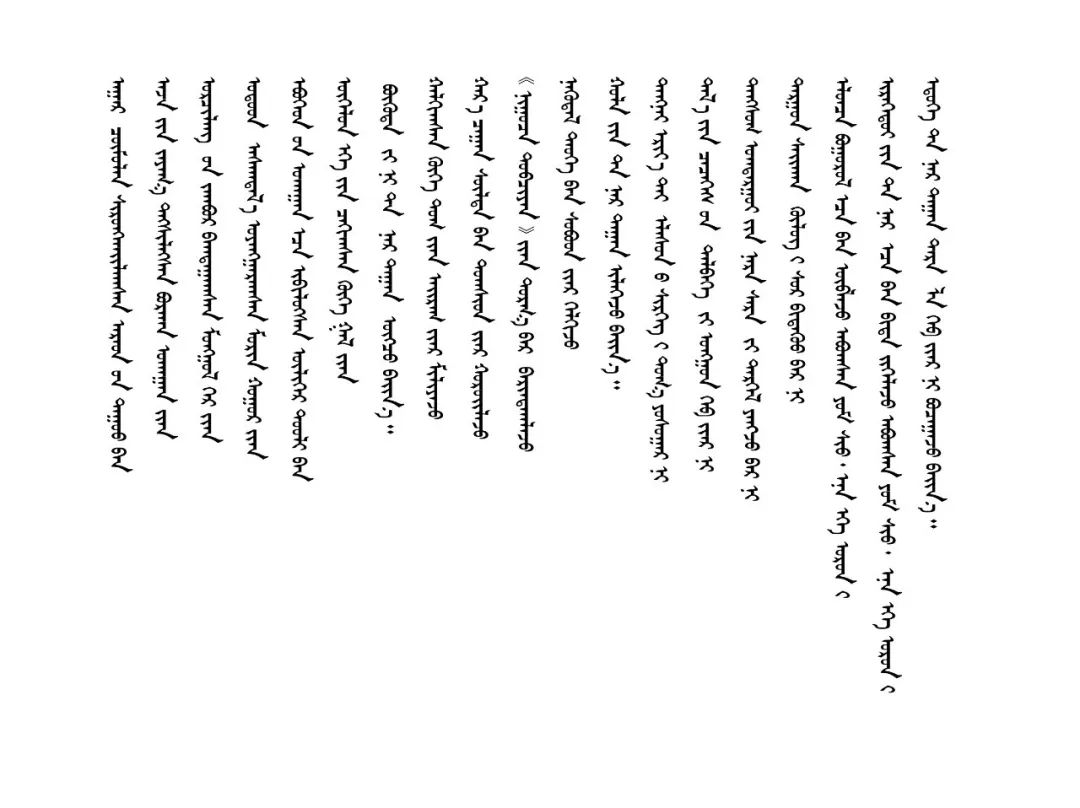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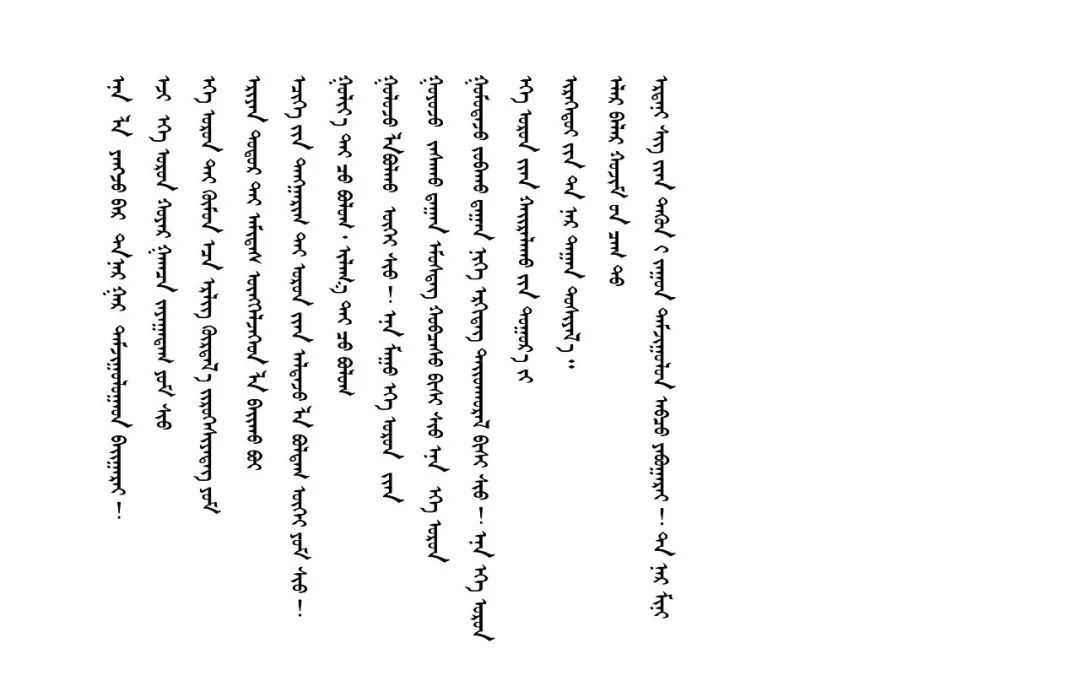
发表于《 阿拉善文学》2005年第1期
代表作三
图文来源:阿拉善盟作家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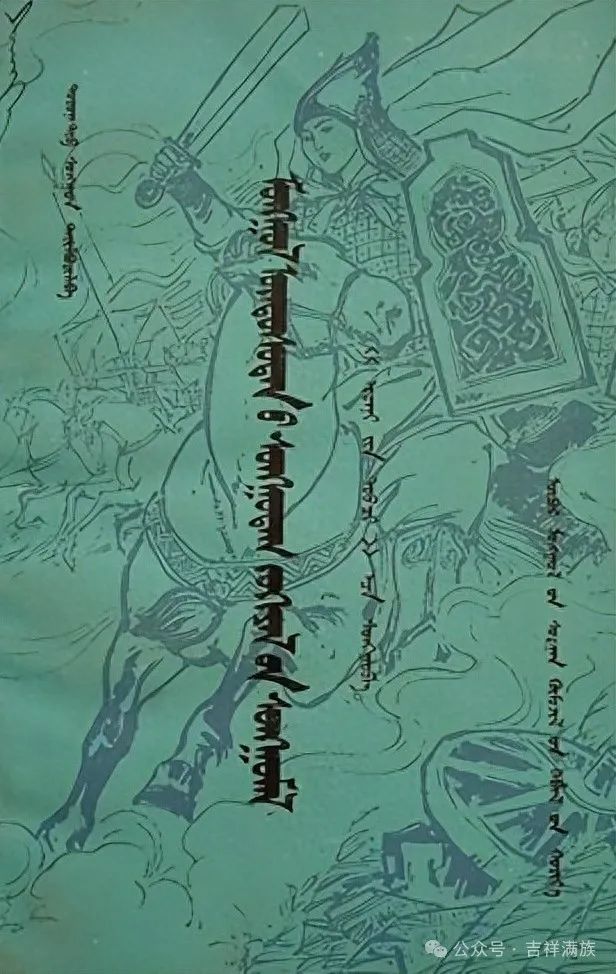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