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介
胡晓燕,笔名胡斐,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少年文艺》《读友》《草原》《朔方》等报刊杂志,出版儿童文学作品《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部分作品入选《中国年度儿童文学》《中国年度童话》《新世纪文库.内蒙古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等选刊。
获奖情况:诗歌《他们必须被铭记》荣获第二届“夏青杯”全国朗诵文本大赛二等奖;组诗《日常生活》上榜《草原》杂志社主办2018年内蒙古诗歌排行榜;组诗《盐源色彩记》荣获《星星》诗刊杂志社主办“与诗同行,走进盐源”诗歌大赛一等奖项;同时荣获盟内“阿.巴特尔”“桃花诗会”等各类大赛征文奖项十余次。


我们都爱桃花
白杏花
春天的软
弹着陶布秀尔唱歌的男人
夜袭
爱从一朵花荡漾开来
关于扁桃花
沉默
贺兰山上
隐身之人
关于科仁努都
据说乡村大夫治好了很多奇怪的病,所以秋天的时候我动身去那个乡村,找找大夫。
他们说秋天很美,尤其在我的家乡,那片胡杨林所有的叶子都开始变成金黄色,它们映衬着水蓝的天像在用颜色吟诗。这意境听上去很美,大家都在啧啧地赞叹,有人痴迷地瞪大了眼睛像遇到了一见钟情的恋人,舍不得离开。
我就在那个时候发现了自己奇怪的症状,我不喜欢那没完没了的金黄色,也不喜欢小风微微地贴着脸颊吹过。早晨的时候一只黑色的硬壳虫爬到了我的袜子上,我很生气,凶狠地把它丢到了门外,还用恐怖的语气吓唬它,再来就让它消失。傍晚坐车回家的路上,有一只刺猬被我们的车灯照着,一动不动地趴在公路上,我用一根棍子赶走了它,愤怒地想它浪费了多少时间啊。回到车里,简在看月亮,他说很美的时候,我回答他,月亮就是一个豁口的铜盆罢了。
那么你瞧,我大概真的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吧,症状就是对身边的一切都开始没心没肺。从前我有太多的喜欢和爱,某一天之后,它们像漏水的瓶子,越来越空。简说,我们去医院吧。我不喜欢那些白色的房子,觉得那里冷冰冰的。
再后来,简就送我去找那位传说中的乡村大夫。那是个遥远的地方,但它的名字又轻又软,云朵村。很少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我就在傍晚跟着一只南飞的大雁出发了,它恰好每年都要路过那里,它记得那个村子。我跟着大雁的指引,坐了很久的火车,又转乘了一趟汽车,坐在高高的驾驶楼里,我想起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了要嫁给开大卡车的人,因为坐在上面一定能看得更多。再然后是遇到突突的拖拉机,它左扭右拐在乡间小路上,我又徙步旅行了一小段,终于找到它了。
大片收割的田野袒露着肌肤,那些在田梗边整齐站着的白杨树在向更远的地方望过去,我暗自嘀咕,再远的地方有什么呢,还不是一样。
乡村大夫呆在自家的院子里,不是在等我, 她只是背着自己的药箱,在给牵牛花检查一下健康情况。
那些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拨开放的牵牛花,淡淡的粉,淡淡的蓝,没有生病的样子,闻一闻,味道很好。它们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整个需要盛开的季节里,它们都是活蹦乱跳的,早早醒来,晒会儿太阳,和小风打打架,晚上也会安静地睡着。它们一点也不让人操心,麦婶往红砖砌的矮墙边丢下种子的时候,己经预言了,这群孩子很结实。
牛仔裤己经皱巴巴,照了照镜子,脸上也变得脏兮兮,所以我放下行李,把自己重新整理了一下。
那是我生病期间才冒出来的念头,穿漂亮的衣服不再让人兴奋,相反,我觉得自己变成一件等待打包的礼品盒之类的东西,早晨起来对着镜子,我总在想,我又得整理自己了。有小小的烦,像四处找食的蚂蚁,就在那样的阳光洒满房子的时候,在心里走来走去。
所以,我把自己弄干净一点,出门去追乡村大夫。我想如果我好的更快一点,那些漂亮的衣服就不会被乱七八糟的丢在衣柜里了,它们在买的时候,花费了我不少精力呢。
麦婶说跟着树篱一直走,就能遇到她。我就跟着那些小树的踪迹,躲着那几只不断纠缠的黄的黑的大狗小狗,找到了另一户人家。门槛很高,我没注意磕了一下,我有点生气了,不是为了疼。
可是一只羊懒洋洋地卧在那里,被大夫抱着它的脖子,正在喂它吃点草和菜叶之类的食物。羊吃得兴高采烈,我看不出它会有什么病,相反,它很享受眼前的一切。温柔的抚摸,鲜嫩的食物,它像住在宫殿里的孩子,安逸地被大夫照顾着,偶而咩咩地唱一两句。
我也忘了自己的疼,也忘了自己的生气,遇到一只童话里会出现的羊,到底是件奇妙的事情。
我问那位乡村大夫,这只羊怎么了。她说昨天它不爱吃东西了,快饿瘦了,是我发现的。我给它吃了点药,你看,它现在怎么样?
我当然得说它好得不得了,这是实话。我看不出它昨天还是一只气息奄奄吃不进东西的羊。
于是乡村大夫更得意了,她背着自己的药箱,又要出门去别的地方。我说大夫,你等等我吧,但我被柏婶拉住了。那只羊是柏婶家的,柏婶说你一定得喝碗荼再走,吃吃我做的油饼,还有新炒的小油葵。我没办法,于是眼睁睁地看着乡村大夫自己走了。
我和柏婶坐在她家木头的小板凳上,喝荼,吃瓜子。那些小小的油葵在舌头上艰难地打转,要费一点功夫才能剥开一点点。这在以前,我肯定吃两颗,就讨厌它们了。那天还好,我的病像是去外面溜达了,它不在,我就慢慢地吃了不少,并且觉得油葵的香粘在舌尖上,那里像长了一座小植物园,甚至能感觉到它们挤挤挨挨长在田里的样子。
转眼就要黄昏了,我终于借着这个跟柏婶说了再见。
临走我问柏婶,大夫给那只羊吃了什么药呀?柏婶眼角的皱纹里都立即盛满了笑意,她也不知道大夫喂羊吃了什么药,不过羊好的很快。
她附在我的耳边,怕别人听去秘密似的,轻轻告诉我,兽医来看过了,我们也给羊吃了他开的药。
我也笑了,比柏婶笑的还大声。我揣着这个秘密回到麦婶的家,我们坐在傍晚的微风里吃饭,乡村大夫有些唠唠叨叨,嘴里含着菜不停地说着话,比如城里的汽车能跑过豆芽吗,豆芽是她养的一只狗,额头上有细长的一溜白,我说不知道,汽车应该很快,但也有慢的让人心急的时候。她又说我有一条粉色的裙子,天热的时候我就穿它。我说你明天还要去给谁看病呀,她说秦爷爷,他老是躺在床上,不愿意出去晒太阳。
麦婶终于不耐烦大夫的话那么多了,她说百依娜,你安静地吃会儿饭。
于是,乡村大夫稍微地安静了一会儿。她扒拉了两口饭,又用黑白分明的眼睛瞄了麦婶两下,看麦婶其实没有真的不让她说话的想法,她说,阿姨,你和我一起洗澡吗?
我答应她,吃完了饭一起洗澡。
她飞快地咽下了碗底的饭,跑出门去抱那些粗硬干燥的木柴,拖着一根进门的时候,她还在吭吭哧哧地用劲呢。我要去帮忙,她不肯,麦婶也摇头,不是在跟我这个远来的人客气,她说不知道为什么,百依娜那么喜欢做这些事情。为了让她高兴,我们就都不理她了,让她一个人去忙。
那个月亮慢慢醒来的时候,那个传说中的乡村大夫——六岁的百依娜抱来了一堆木柴,麦婶在灶塘里烧着了火,她还要拿一把小蒲扇在旁边扇风。我们看着那红红黄黄窜出的火苗,锅里的水渐渐冒出小泡,一朵一朵从边沿升起来,像养了一群鱼的小池塘一样。
调好了温热的水,我帮她洗着小小的身体,她咯咯地笑着,停不下来。我是被水蒸气蒙了眼睛么,以前每天夜里就觉得干涩的眼睛,那会儿却是温润的。简说你看电脑太多了,你看电视太多了,似乎是,又似乎不是。
简是先提到乡村,才提到大夫的吧。他说起她,带着乐不可支的表情。她给所有她认为有病的病人们看病,并且往往药到病除。
我给六岁的的乡村小大夫讲我的症状,不喜欢风,不喜欢落叶,不喜欢陌生人看我的眼神,不喜欢飘在整条街上的音乐,有时候觉得浑身没力气,常常只想睡觉,可是夜里的时候,我又总是睡不着。我脑子里像奔跑着一座复杂的城市,停不下来。
她当然不懂我在说什么,可她带着很想治好我的神情,用大夫的语气说,你吃一个糖,睡一觉,就好了。这个小大夫不管牙的事情,她每天晚上睡觉都得要一颗糖,吃完了就安静地睡着了。
一颗糖可以算是药么,我悄悄嘀咕,不过还是把它含在嘴里。嚼着草莓味的糖,睡在铺满月光的房子里,虽然辗转了一会儿,可是一觉睡醒,己经是十点钟的阳光在照着了。
这很好,我没有在做梦的时候醒来,不需要瞪着天花板,拼命地数绵羊,再让自己睡着。这己经很好。
百依娜背着自己的小药箱出门了,那是个曾经装过了果冻的塑料小包,现在里面塞满了瓶瓶罐罐,她带着它们像在翻山越岭,跨过乡村特有的高高的木头门槛,小药箱被碰得唏哩哗啦的,她觉得自己很忙,大人们纵容着她,放心地吃她给的药,愉快地看着小大夫,一天天在这座乡村走来走去。
我跟着小大夫去给秦爷爷看病,那座老旧的房子,地上都是凹凸不平的小坑,我负责抬出了老旧的躺椅,放在院子里阳光最多的地方,然后就在一边,看小大夫喂躺椅里的秦爷爷吃药。她给秦爷爷吃了一颗果仁巧克力,看起来她的药箱里,都装着一些甜蜜的药,不会苦,还会让人有幸福感。
城市里也流传,甜的食物会给人更多的快乐,那么这一条倒是可信的。
所以秦爷爷那天很舒服地晒着太阳,我觉得那些白色的胡子也在笑,因为它们抖得很厉害,小大夫很小心地用手指去碰他们,她想知道它们有多少岁了。为了它们的年龄,秦爷爷讲了一些故事,它们很好听,不过在旧时光里呆久了,有一些尘土,风一吹就光鲜了。我决定离开乡村的时候,要把那些故事也一起带走。
时间走得很从容,角落里的枣树伸着细细的枝梢,像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不久前它们还挂满了油亮暗红的枣子,在绿色的叶子里躲躲藏藏,揪一颗放进嘴里,好像秋天浓烈的汗液都在里面,水水的,脆脆的。
就在那会儿,我久违的想象力又像兔子一样,从草丛里跳出来,吓了我一跳。我并没有吃到暗红色的枣子,可描述它们的词语却自己跳出来了。
我们心满意足地回麦婶家去,小大夫带着一点成就感,一路上都不肯让我攥她的小手。她不时地停下来,跟她的病人们说说话,花很可爱,羊很柔顺,狗们很热烈地用肥厚的舌头舔她的手心,大人们会揪揪她的小辫。
一座乡村好像都很骄傲,也小心地呵护着这个明朗的孩子。谁知道她会不会哪一天改变主意呢,像我一样,没有遇到喜欢的开大卡车的司机,就去喜欢别的人了。她也许走到一座城市里,就做了别的事情呢,不再是一个温柔的大夫。她会偶而想起,小的时候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会觉得害羞又不舍得吗,就像我现在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里,乡村大夫领着我四处溜达。我们像两棵长了脚的树,走过越来越空旷的乡村,在风里,会不由自主地哗啦啦唱起歌,幻想遥远的地方,住满了泉水,它们也在悄悄的旅行,顺着只有它们才知道的路,一直走到乡村的面前。那时候一座乡村会对它说什么呢,它会邀请它住下来么。还是告诉它其它的路,让它继续它的旅行呢。
简是说过,一座乡村的宁静和童真,会治好你的病呢。
我就是这样在一座乡村里,慢慢丢掉了那些没心没肺的症状。乡村小大夫是有魔力的吧,虽然她只给我吃了一些糖。
到我觉得自己己经痊愈,我于是悄悄离开了那座乡村。小小的大夫还睡在她的梦里,我深怕她用小手搂住了我的脖子,就那样用雾蒙蒙的眼睛看我。我会伤到了她吗,不忍心走,却还是得坐着拖拉机坐着大卡车坐着鸣笛的火车,回到我生活的地方。简还在那里等我。
那个乡村大夫的传说,是在那个秋天的时候,有些忧伤地写下了结尾。
但我说简,我可能得了另一种关于想念的病,因为我常常想到云朵村,还有它的小大夫。那时他只是温柔地说,你继续生病吧。我会照顾好你的。
城市也可以变成一座乡村,这样也很美。是童话里的故事。
创作谈:我的第二种形态
胡斐
我们生来是有束缚的,从身体的同一性就已经显露端倪。两只眼睛一张嘴,一个鼻子两条腿。不管我们怎么谈论个体差异,都还是同一棵树上的果实。这种生而为人得到的单一,是怎么显露出真正的不同呢?个性,思想,如何理解万事万物,用何种方式表达感受。这庞杂的内心世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我的写作动力,大概都来源于这种对不同的探索。
写作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就像老人们常说的,腌咸菜,同样的缸,同样的菜,同样的盐和水,不同的手会腌出不同的味道。他们常说这是手气,在我看来,炒菜,画画,音乐,长跑......人总能发现,在众多的事情中,有自己擅长的,也有自己无法胜任的。很多年前,我胡乱写着粗糙的诗歌,却从中发现了对写作是有把握的。不多,够不上成为伟大的作家,但还有点,所以就渐渐成了码字的人。我从不说自己是作家,我只说自己是码字人。一个字一个字码起城堡,河流,浪花,春天,怪诞,忧伤,美好,这些纷杂的东西,和自己的内心相连,也意味着对世界的敞开。
对我来说,写作是我的第二种形态,就像会变身的汽车人。生活不断重复,可是对周围的观察和反思让我跳出其中,看更远的风景,懂更复杂的人,体会更跌宕的情感。每一次的创作都是一次新的发现,每一次的发现都让我更加深入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我喜欢这种不同,我会一直写下去。
图文来源:阿拉善盟作家协会
图文制作:魏 然
审 核:赵秀萍
- 上一篇: 【阿拉善艺苑名家】第三期 书法家 ③ 戴秀峰
- 下一篇: 【阿拉善艺苑名家】第一期 作家 ⑤ 黄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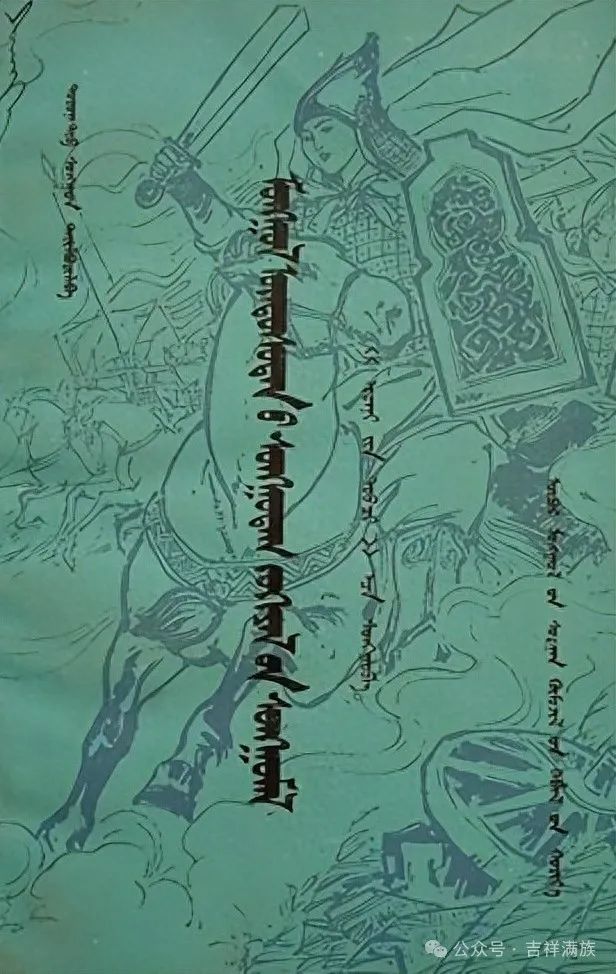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