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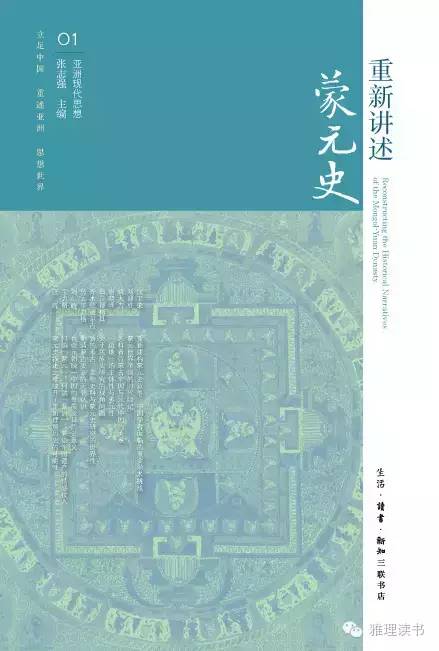


首先我很感谢《亚洲现代思想》刊物做这样一个活动,我略微讲几点感想。今天讨论里面,有一个话题我觉得是跟历史叙述有很大关系,虽然大家都做历史实证研究,可是,我们听下来就觉得,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蒙元史,真是错综纠葛,难以找到一个完全统一的叙述,何止是蒙元史如此,别的朝代实际上也是如此,只不过蒙元史由于它的特殊性,造成了叙述上的更大的困难,而这个叙述上的困难在我看来也变成蒙元史研究的一个魅力所在,对我们今天很有意义的一个魅力所在。这个是魅力是什么呢?今天上午我记得宝力格教授提到的世界历史叙述当中,比如说弗兰克他们在讨论,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建立全球体系之前也存在着一种全球体系。不是一般意义的区域史,而是在全球史的框架下存在着不仅仅是区域的而且是全球性的体系,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当然也是有争议的。全球化是跟现代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是一个以现代欧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但是如果在此之前的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是散落在各处的区域史、王朝史,而是已经有某种网络性的全球特征的话,那么,蒙元史所提供的历史认识上的重大可能性和潜力就是存在的。至少我看晚清书籍的时候,像魏源去做《元史新证》,有九十卷,甚至四库馆臣、钱大昕等,他们来做元史的时候都有对外部世界重新认识的意愿,通过蒙元史,不仅仅是要认识蒙古,而且是要理解另外一个世界,这一点,与中国人怎么去认识和理解世界历史有关的。

蒙元史的难以叙述在现代史学里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说当年魏特夫和冯家升提出的所谓“征服王朝”和“渗透王朝”这一套的概念,引起很大的争议,很多史家说不存在什么“征服王朝”,所有王朝都是征服的,不过是这种类型的征服,还是那种类型的征服,诸如此类。但不管怎么说,蒙元史的特点首先它是几个矛盾体。
第一,它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漠北王庭和中原王朝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王朝;在它占领中原之前,在漠北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制度,占领中原之后并没有把那套制度完全放弃,这样就形成了经常提到的“二元体制”,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都是,分四等人制什么的,还有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尊儒教,一方面还尊奉基督教、佛教等等,是一个多元宗教的体系。再加上大家常常讲的,它的行政体制跟自然区域之间形成区别,所谓的犬牙交错,十个行省加上藏区,它的路府州县和自然形成的区域之间是故意错开的,以防止地方性的认同,进行“大一统”化。它的政治结构似乎有“大一统”特征,但里面又没有收拾干净。那更不要说它是大蒙古国的一部分了,元朝也只是蒙古世界的一个部分,并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中央王朝。今天无论是对清代历史还是蒙元历史的再探讨,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今天全球化、区域化重新提出了“何谓中国,何谓亚洲”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今天上午姚大力教授、唐晓峰教授实际上都提出了相对于现代国家制度的一个不太一样的另一套叙述,从边界到主权到认同——只有现代国家制度需要这样的概念而且用这些概念来结构我们对历史的叙述,而蒙元史提出了另外的叙述的可能性。它的认同包括政治的体制都可以是多元的,形成了不可以在单一线索上进行叙述的历史,这就使得政治共同体、族群、区域和世界体系之间构成了犬牙交错的勾连的关系,这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现代世界。我们都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地式微,或者说旧式的认同政治出现了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重新提出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亚洲”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蒙元史的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世界和理解我们自己都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第三,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或者说使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显得很有必要性。我记得上一次开会,在芝加哥大学,姚大力老师也在,我们一块讨论,都引用到雍正的一个论述,实际上它是一个新的“正统”论,雍正《驳封建论》说:
“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
这个话挺有意思的,清朝似乎是把中原王朝与蒙元的“正统”重新综合起来了,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今天讨论的蒙元史里面,就会发现其实也挺复杂的。在元朝的历史里面,到底怎么确立元朝的正统,怎么去界定自我,任何一个王朝不管用不用中国传统的正统论,但事实上都要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借用“正统”这个理念。当年在元朝征服中原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取南宋的时候,围绕“正统”有很大的争议,比如《刘整传》讲,他劝伐宋的时候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圣祖说现在我决定了要伐取南宋。去打南宋不光是为了财富土地人民什么的,这是当时一个确立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方式,也变成了指导自己叙述历史的方式。统治者需要叙述自己历史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从政治需求变成了历史叙述的一个部分。我看元朝的汉族士大夫围绕元朝正统问题也有很多讨论,实在是个复杂的问题。我看谢修端的《辨辽宋金正统》的时候,他的一段话给我一个提示,他说不光是元朝,无论是谁想把自己的“正统”性说圆都是很难的。
就是说,怎么去确定正统,哪个朝代都会碰到,你要硬去说某个朝代为“正”,另外一个“不正”,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议。可见,在历史叙述上,尤其是中国历史,有着强有力的正统理论,所以编织起了一个王朝相继的谱系,但是深入进去一看,这是很困难的,而蒙元史在所有的叙述当中是最困难的。恰恰是这个最困难,提供给我们重新理解自己历史的可能性,因为它重新把历史打开,重新让我们理解历史叙述上的多重性和其他可能的叙述。我们今天为什么去问“何谓中国,何谓亚洲”,显然,我们不能再按照过去传统的历史叙述来回答“何谓中国”这个问题了,我们今天确实面临一个再叙述的问题。

最后一点,在历史叙述上,从我们现在的讨论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一个是族群,一个是它背后的宗教和文化,这三者是我们讲得很多的东西,当然,说到蒙古社会,实际上游牧、农耕等生产方式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讨论到的问题。放到今天语境里头重新去叙述历史,还涉及到所谓的世界史,为什么很多人都很有兴趣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对以民族国家为叙述历史的范式感到很怀疑。大概一、二十年间,在国外的历史学界也有很多人讨论帝国史的比较,产生出了一些成果,也导致了一系列的争议。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纽约大学Robert kupper, Jean kupper夫妇写了一本书也叫《the Empire》 帝国,他把俄罗斯帝国、蒙古、罗马全都看作是帝国史,把今天的美国也作为帝国来对待,换句话说,他所说的帝国只是一个容器,没有实质,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到这个容器里来加以叙述,他们以此来强调近代十九世纪以来所谓“民族国家”本身的虚幻性,实际上“帝国”从来没有消失过,到今天也没有。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我觉得最大的争论点在于,如何理解现在的政治体和经济的关系及其与十九世纪以前所有的政治体和经济之关系的不同,这一点是核心,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结构“中心-边缘”关系的模式跟传统的帝国模式之间差别很大。我们到底承不承认十九世纪发生过所谓的卡尔·波兰尼说的“great transformation”,如果我们认为它发生过的话,那民族国家主权这一类的东西就不是一个简单可以抛弃掉的东西,需要去理解它跟整个经济生活和组织社会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传统的方式之间的差异。这个是争议非常大的问题。
从我们今天的这场讨论,我收获很多,因为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都跟我们今天讨论所希望涉及的问题有密切关系。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再深入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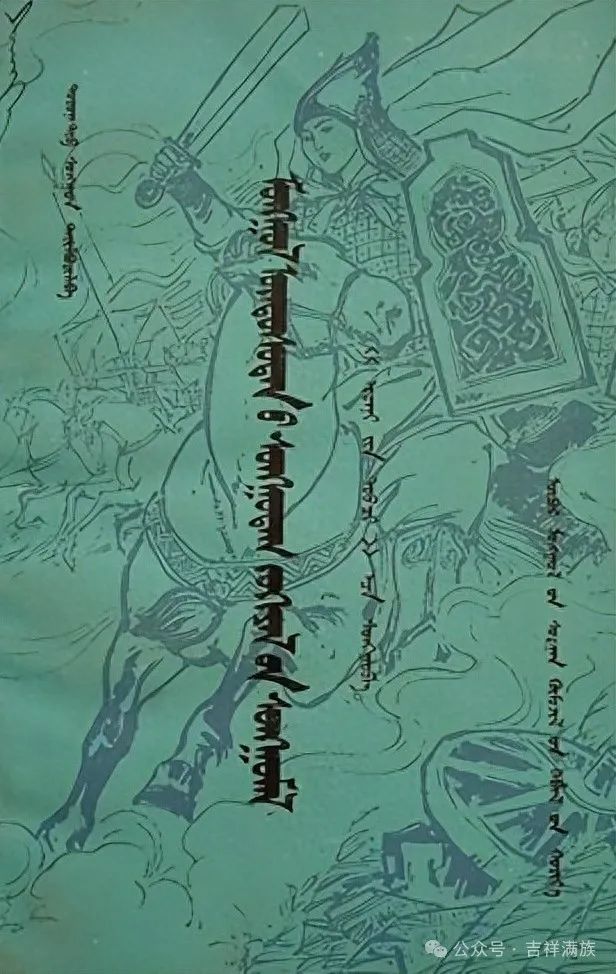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