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陀与苏鲁锭(上)

(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的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1507―1582))
记得小时候,呼和浩特的寺庙还相当破败,虽然也是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部门并不那么上心,也没有如今天有数以亿计的“善款”支持以返修寺庙重塑金身。烧香拜佛者大多都是老人,青壮年极少,孩子更是没有,“那是封建迷信”的教条还很深入人心。
近年来,大召、席力图召、五塔寺等寺庙已经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了,一到“佛诞节”、“佛灯节”等佛教节日,上灯上香者摩肩接踵,很多父母带着年幼的子女前来,让孩子们在自己示范下履行宗教仪式。
有人说这是文明复兴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封建残余沉渣泛起,有人说这是进步,有人说这是倒退,各种争论从未停息。
面对争论,又有人说,这样的现象该如何评价,不该是现在的事,而要等一段时间,在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回过头来进行分析,才能有些中肯的结论。毕竟,当代人说当代事,身处局中,难免当局者迷,只有当时光将一切沉淀下来后,有了身处局外的可能,才会旁观者清。
这样的说法,笔者总是有些怀疑,就如历史研究一般,后人以后人的眼光看前事,虽然有旁观者的“位置优势”,却也会陷入到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误区,用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形倒推前事,又进入另一个局中而难以自拔。
正如钱大昕所言:“读经易,读史难。读史而谈褒贬易,读史而证同异难”。谈褒贬为何容易?因为可按照自己的感情或者情绪来说话,不需费力;证同异为何难?因为这需要比对不同史料,细致分析历史细节,既要走出历史之局限,又要设身处地的体察历史中的人和事,做到身处局中而置身事外,岂能不难?
比如,本文要谈的问题:藏传佛教给蒙古人带来了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似乎早有定论。无论是学者论断,教科书的编写,还是民间闲谈,都在强调一个事实:藏传佛教几乎摧毁了蒙古民族。
那么,是怎么摧毁的呢?
其一,佛教摧毁了斗志,使得善战的蒙古人陷入衰弱,成为人人可欺的弱者;
其二,佛教使得大批青少年和壮年出家为僧,使得人口萎缩,濒于灭亡;
其三,佛教使得大量物资用于修建寺庙,大量的财富作为供养捐献给寺庙,生产无法发展,社会处于无活力的状态。
而看到清末的蒙古人的状况,这三点都靠得住:清末民初之时,蒙古地区经济极端落后,不仅普通牧民大多陷于赤贫,即使王公贵族,也多有负债累累者。曾经踏破大半个世界的蒙古铁骑早已成为传说,蒙古兵不但不能抵御西方现代化军队,即使面对内部的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军、捻军、回民军也往往一败涂地,朝野早有“蒙兵不能战”的共识。尤其是人口,清初时,蒙古人口有2169446人,而在清末则是1715818人,减少了20.9%的,而这是在清朝总人口先后突破一亿、两亿、三亿乃至最后达到“四万万五千万”背景之下。
与之相对的,则是蒙古地区寺庙林立,僧侣占人口比例巨大的现实:外蒙古有寺院2600座,僧侣10万余人,内蒙古有寺庙1800座,僧侣15万余人,平均每旗有寺庙30-40座,僧侣人口占人口比例平均达到30%到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乃至60%。
佛教如此兴盛,而笃信佛教的蒙古民族却如此衰颓。清朝官方的《清朝理藩院档》中也承认:“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教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
于是,在清末,有识之士无不对佛教大加挞伐,文学家尹湛纳希在他的巨著《青史演义》中,便借助评论历史,对佛教进行抨击,认为“沉迷于玄术,佛教盛行”,便会导致“国政废弛,世道禁锢”乃至“社稷倾覆”。《蒙古风俗鉴》的作者罗布桑却丹更是直斥道:“英雄的宝剑换成了手中的念珠,无畏的勇士变成了跪叩的懦夫,健康的人无谓地向佛像乞求佑护。人人手持念珠诵咒,家家喇嘛念经祈祷,敞开死亡的大门,面朝永不回首的方向。”一些王公贵族也认为,蒙古“贫弱之根,实积于此。急欲图强,非取缔宗教不可”。

(蒙古的第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大召(伊克召),明神宗赐名弘慈寺,清太宗赐名无量寺)
如此证据确凿,藏传佛教几乎毁灭蒙古民族的结论还有什么争议吗?
且慢,藏传佛教如果是清朝开始统治蒙古各部时开始传入蒙古,这个结论并无不妥,如果不是,就必须弄清,在清朝之前,藏传佛教给蒙古带来了什么?
元朝时,蒙古皇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但随着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元室北遁而建立北元,佛教很快便远离了蒙古人。恢复了游牧的蒙古各部,重新拾起了原始宗教萨满教,直到二百余年后的1578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引入蒙古,蒙古人才与藏传佛教再续前缘。
从1578年佛教传入蒙古,到1759年最后一个蒙古汗国准噶尔汗国被清朝灭亡,这之间又是近二百年,这段时间内,藏传佛教是否使得蒙古人陷入了人口锐减、武力颓废、社会活力大衰的境地呢?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结果恰恰相反。
从人口而言,因为元明之际的战乱,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蒙古人口一度锐减,约有160万左右。1480年,达延汗实现了蒙古本部的“中兴”,大型战乱基本停息,人口开始回升,到明末的1634年,达到200余万,这期间已经有佛教传入的66年,人口并未锐减。1635年漠南蒙古被清朝征服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坚持到1691年,漠西卫拉特蒙古更是到1759年方才并入清朝版图,这段时间内,虽然有很多战争,但人口仍在稳步上升,史书中有大量因为人口滋生,牧群繁盛导致牧场不足而贵族发生摩擦乃至内斗的记载。尤其是卫拉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从其孕育时期起,便全民笃信佛教,但其鼎盛时期,能够达到“控弦近百万人,驮马牛羊遍山谷”的程度。
再说战斗力,藏传佛教传入之后,无论是可以控制各部的北元大汗,还是在某一地区称雄的蒙古首领,都能够对明朝造成很大威胁。扎萨克图图门汗(明朝史籍称为土蛮)、呼图克图林丹汗(明朝史籍称为虎墩兔汗)、内喀尔喀的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明朝史籍称为炒花)等都是明朝边将谈之色变的“强虏”。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从努尔哈赤的1593年到皇太极的1635年,共用了42年时间,相对于人口、经济、幅员远远高于蒙古的明朝,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的39年,抵抗时间之长,不但并不逊色,且犹有过之。准噶尔汗国在立国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多次击败俄罗斯和清朝大军,最后灭亡时,也是抵抗激烈屡仆屡起,乃至于乾隆皇帝不得不下令进行灭绝屠杀,“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雍正皇帝归并青海时,和硕特蒙古起而抵抗,各大寺庙的喇嘛也从军参战,在郭隆寺一战中,数千喇嘛与清军激战,战败后退入山洞,被放火烧死也不投降。此战清军仅腰刀砍缺者就有三四百口,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将作战经过写成奏折呈递雍正帝,其中便言道:“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雍正帝在朱批中也表示了惊骇:“实属奇事,方闻此等英勇之喇嘛。”
还有社会活力,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之后,给蒙古带来的非但不是停滞和落后,反而是进步和发展。
在佛教传入之前,因为常年的战乱,社会财富难以积累,知识阶层几乎扫地以尽,莫说平民,即使贵族也大多是文盲,文字几乎失传,历史濒于断裂。而在佛教传入后,形成了脱离战争与生产的知识阶层——僧侣集团,因为笃信佛教,内部的战争一般不会波及寺庙,使得寺庙成为文明的保护地,僧侣们可以安心研究学问。各寺院均设有经学学部、医学学部和时轮学部(即天文学),并有着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喇嘛不仅仅是祭司,而且还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医生,甚至是世人的心脏和头脑,也是他们的权威人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蒙古语言、文字得以规范和传承:1589年,喀喇沁翻译僧阿尤喜为转写藏语和梵语创造阿利伽利蒙古文;1648年,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创造适合于卫拉特蒙古语语音特点的托忒蒙古文;1686年,喀尔喀蒙古的札那巴斯尔参考藏文和梵文,创造索永布蒙古文。
文字的规范使文化得以发展,蒙古史诗《格斯尔可汗传》、《满都海彻辰夫人传说》等便是在佛教传入后,开始有了手抄本和刻印本,得以传承至今。作为蒙古史重要文献的《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阿拉坦汗传》、《阿萨拉格齐史》、《恒河之流》、《水晶珠》、《金轮千幅》等也都是在佛教传入后,才撰写出来并得到妥善保存,而《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金轮千幅》等史书的作者,本身就是喇嘛。
同时,因为寺庙的特殊地位,使得围绕其产生了一个个市镇,成为商品集散地,贸易得以兴盛。今天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便是因著名寺庙大召的兴建而成为当时漠南蒙古重要的城市,人口最高时达到十万之众,成为明蒙贸易的枢纽。而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也是以大寺院扎尔固寺、海努克寺为中心,形成“人民殷庶,物产饶裕”的“西陲一大都会”。
尤为重要的是,藏传佛教的传入,使得蒙古社会一些陋习得以消弭。例如,萨满教有血肉供神的传统,不但祭天时要宰杀大量牲畜,甚至要以童男、童女为供品,贵族死后,也要进行人殉。曾就有史书记载,佛教传入前,因一个贵族幼儿夭亡,其母亲竟然用一百名儿童殉葬,在屠杀到四十名时,因为民众骚动和一些贵族的抗议才作罢,可想而知其残酷。佛教传入后,以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供佛也采用乳制品,而严禁杀生祭祀,贵族去世请喇嘛诵经49天,一般牧民死诵经7天。还有一种陋习,那便是因为常年战乱和物资短缺,有些地区的萨满教甚至有儿孙杀害年老的父祖,流放体弱的父母的教义,而佛教戒杀生、报四恩的教谕,使得这一陋俗不复出现。
现在,也许可以的得出一个结论,从藏传佛教传入到蒙古不再以国家的形式存在的近两百时间内,文化、人口、尚武精神、社会活力等等并没有衰颓的迹象。
可在清末,蒙古民族确实衰颓了,而且衰颓得触目惊心,原因何在?难道藏传佛教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责任是有的,但只能算“从犯”,或者说,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上一篇: 【出彩赤峰人】当代散文大家、草原剑客——鲍尔吉·原野
- 下一篇: 贡桑诺尔布与近代蒙古族历史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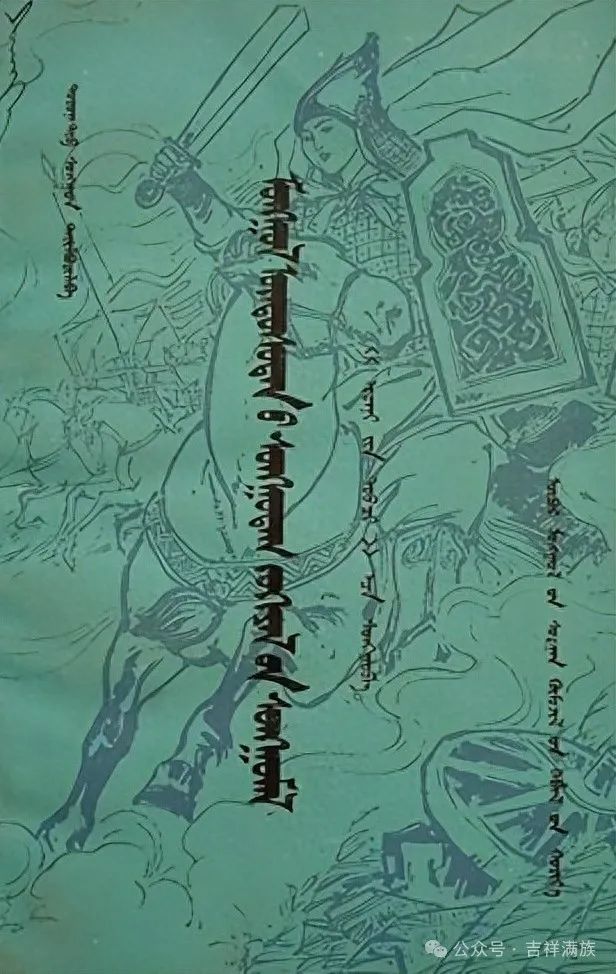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