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内容目录
诗集 | 音乐创作 | 学术思考 | 摄影作品

蒙古地区近当代“民族”[ündüsüten]概念及其社会认同
摘要:“蒙古民族”[mɔηgɔl ündüsüten]概念的出现和使用与近当代中国历史和民族政治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在近代蒙古地区,“民族”[ündüsüten]概念的流行和使用无疑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内政治、汉人文化思想界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直接影响。蒙古民众和精英在传统的血统、部落、种族、宗教等概念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了“民族”概念,并为传统的部落、部族赋予了新的意涵。本文通过系统考察蒙古地区近当代蒙古文文献与汉文文献记载,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深入阐释了“民族”[ündüsüten]概念在近当代蒙古地区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叙述形式及其社会认同的多线性、模糊性特征。
关键词:蒙古地区;“民族”;社会认同
在世界近代历史,尤其是18 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文化格局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始终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民族的形成,民族与国家的利益融合、权力重叠及其内部的张力和冲突过程充分说明了世界政治、文化环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民族主义从18 世纪最后25 年开始发生,由瓜分波兰和美国革命开始,通过法国大革命,到对拿破仑征服普鲁士、俄罗斯和西班牙的反应,它正式形成。”[1]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思潮与社会运动为中国近代社会组织———“民族”的发育和生成提供了外部环境,对一直将西方文化作为榜样的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后果。
在清末以来的中国“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讨论中,学界基本形成了共识:近代中国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在西方外来帝国主义的逼迫和殖民政策下生成的爱国主义或内部种族主义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1)中国正式使用“民族”一词是19 世纪后半期,进入20 世纪后开始大量使用;(2)“民族”的出现,适应当时国内反封建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需要;(3)受到了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从19 世纪开始,亚洲许多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蓬勃发展,西方和日本文化的传入,势必给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中国以很大的影响。
韩锦春、李毅夫认为,“民族”一词最早见于1895 年第二号《强学报》上。彭英明又将时间推前了20 年,其依据是王韬1874 年左右撰写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后来,还有学者指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十七年(1837 年)九月刊上登载《约书亚降迦南国》篇,写道:“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至于这是否就是汉语中第一次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一时很难作出定论,也许未来还会有新的发现。在世界与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的大背景下,近代蒙古地区的“民族”概念也经历了其独特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关于近代蒙古地区“民族”概念的生成,学界讨论甚少,至今尚无详细的考证和分析。
由于历史文献和资料的严重缺失,对其进行准确考证和详细分析,并不是一件易事。众所周知,对一个词语或概念的追踪和研究不一定能够充分说明和解释其所生成的社会环境和认同、意识和行为等诸多特点。但对近代蒙古社会“民族”概念的讨论和考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从古至今,蒙古地区社会组织概念有很多,如“蒙兀儿”、“蒙人”、“蒙古人”、“蒙地”、“蒙古族”和“蒙古民族”等。在这些概念生成、演变和使用的时间上,我们只能作出古代、近代和当代的粗略区分,如“蒙兀儿”在14 世纪前泛指蒙古人,“蒙人”、“蒙地”等概念普遍应用于清朝统治时期。
(一)汉文文献中的“民族”概念
清末在汉人社会中流行的“民族”概念与当时的文人墨客、留学生群体,尤其与留日精英有着直接关联。例如,孙中山在与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说道:“夫共和主义岂平手而可得,余以此一事而直有革命之责任者也。况羁勒于异种之下,而并不止经过君民相争之一阶级者乎。清虏执政于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2] 他在《灭汉种策》中还写道:“不闻咱们祖宗说么,八旗兵,以御外则不足,以防家贼则有余。故无论何地,苟有蠢动之机,捕风捉影,不问其事的实不实,立即屠他全城。”
在近代“民族”概念及“民族—国家”意识在东方的生成问题上,人们自然而然联想起西方国家。从地域角度作出判断的话,蒙古地区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在内蒙古地区出现的可能性远比喀尔喀蒙古地区大,因为清末时期的喀尔喀地区仍处于传统性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体制下,而内蒙古地区随着清朝统治的快速衰落,社会结构性变迁加剧,不同阶层、不同族类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为阶级斗争、民族主义提供了条件。从社会阶层角度看,由于蒙古精英阶层始终站在社会纷争与族类冲突的前沿,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情绪激发,最有可能接受和使用“民族”与“民族主义”,所以在蒙古上层精英阶层中形成的概率远比一般民众群体高。由于清末蒙古地区王公和上层僧侣、社会精英有绝对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威,蒙古民族意识的形成有了可靠的群体与社会阶层保障。
近代“民族”概念在蒙古地区的出现,同样与当时留日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与日本国有密切联系的蒙古社会精英有关。冯克认为,在当时留日学生中流行的民族主义观念“对中国学生的政治术语发挥了持久的影响。
这个概念在字面上意指‘种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基于种族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3] 20 世纪初,一定数量的蒙古上层和精英到日本留学,出现了最早的留学生群体。尤其在东蒙古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历史原因,一部分蒙古上层精英与日本上层和民众有着持续的联系与往来,当时的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曾在1903 年秘密访日,并得到日方高层的接待。回国后他立即着手改革旗务,兴学练兵。他在崇正堂开学典礼上说:“我们蒙古民族,在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之地,席卷欧亚两洲,灭国四十……本王父祖相承,历当大清皇朝的爵位和俸银,当此国家多事之秋如不协助国家,使民众习文练武,实在于心不忍。”[4] 这可能是近代蒙古地区王公精英提出“民族”概念的最早记载。
在此之后,蒙古上层精英、国家议员在各类信件、报刊和通电中逐渐使用“民族”一词,但总体上使用率并不高。例如,1919 年4 月2 日,广东旧国会议员恩克阿穆尔等致电北京政府蒙藏院等,发表《促蒙人猛醒》,称:“传闻蒙古被人煽惑,误解民族自居主义,外蒙宣布独立。骤听之下,不胜惶惑。……盖国以民为本,民以自治为本,若夫被治于人或受保护于人,其一切生命财产供他人之牺牲,政治上之主权受他人之缚束,如波兰、犹太、朝鲜等民族。非自决无以图存,故民族自决者,亡国之民所当猛醒急起者也。”[5] 蒙古上层精英纷纷阐述了对“民族”的理解和看法,并强调了民族自决的重要性。
20 世纪20-30 年代,蒙古地区民族主义进入了巅峰时期。西蒙古最著名的“泛蒙古”民族主义运动是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领导的自治运动。1933 年,德王在百灵庙蒙古自治通电中指出:“当局所谓富强之策,直我蒙古致命创伤。痛定思痛,能不伤感?!处兹今世,民权一经剥夺,民生势必致困,民族益衰弱,夫岂不知?我蒙古拥护国家之热诚从不少衰,且尝盼望中央,善于扶助,建设一新蒙古。”[6] 重点阐释了蒙古民众的遭遇,表达了对当权者和国家的不满情绪。
(二)蒙古文文献中的[ündüsüten]概念
在蒙古地区蒙古文文献中,[ündüsüten](民族)词语的出现明显晚于汉文文献。清末喀喇沁地区蒙古精英,近代蒙古族著名史学家、翻译家和诗人尹湛纳希(1837-1892年)在他著作中多次论述过汉人与蒙人问题。例如,他在《青史》的“前论”中论述道:“以语言而论,讲汉语提倡韵脚,讲蒙语讲究对字头,讲藏语注重语调明快,讲满语注意词句的搭配。”[7]“汉族人的发祥地是中原,蒙族、满族的发祥地是塞外,回族发祥地在中国西部。”[8]他对蒙古人与其他族之间的语言、地域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整个著作中多处提到“蒙古人”、“蒙族”和“汉人”等概念。但在他的《青史》、《一层楼》、《泣红亭》和《红云泪》等多部作品中却从未出现过[ündüsüten](“民族”)一词。在另一位喀喇沁近代蒙古族哲学家、博学多闻的民俗学家罗卜桑悫丹(1875-?)的一部珍贵的蒙古族志书著作———《蒙古风俗鉴》中曾提出过几个与“民族”相关的概念:[mɔηgɔl hun](蒙古人)、[mɔηgɔl irgen](蒙古庶民)、[mɔηgɔl gajar](蒙地)、[mɔηgɔlodom](蒙古血统)、[mɔηgɔl ogsa:]“蒙古族”、[mɔηgɔle:mg](蒙古爱玛克),但从未提及近代意义上的[mɔηgɔl ündüsüten](蒙古民族)概念。罗布桑悫丹写道:“在明代,靠长城居住的喀喇沁蒙古人首先向汉人出租边缘、偏僻、河沿滩头之地。”[9] 他认为:“在清代,汉人转入蒙古人的很多。按来源分:(1)汉地商人变官吏属民者;(2)满人公主带来的随从;(3)从内地买来的汉地佣人。”[10]
进入民国时期,尤其在1919 年之后,蒙古地方青年学人和精英开始接触和翻译汉语“民族”概念,并开始使用[ündüsüten](民族)一词。曾在1925年(民国十五年)10 月25 日至1926年4 月期间出版发行,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金永昌主持兴办的《内蒙国民旬刊》(蒙古文)提到了[ündüsüten](民族)一词。例如,《旬刊》最后一版(第八册,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十日)的“蒙旗政治制度向来依据军事力量而建立”部分中写道:“我们蒙古民族,被称为游牧国家,被世人视为勇敢的人群。”[11] 在《旬刊》中,除了[ündüsüten]之外,更多使用了[mɔηgɔl hun](蒙古人)、[mɔηgɔl gajar](蒙地)、[mɔηgɔlodom](蒙古血统)、[mɔηgɔl ogsa:](蒙古族)和[mɔηgɔlt∫o:d](全体蒙古)等概念。一直到20 世纪40 年代,在蒙古文信件、主要报刊和有影响力的诗人、作家文学作品中很少使用[ündüsüten](民族)一词。20 世纪40 年代中期之后,[ündüsüten](民族)概念在文化精英的著作中有了广泛的应用,可用当代蒙古文学奠基人、蒙古族思想家、诗人赛春嘎(1914-1973年)的诗歌作品为例证明这一发展特征。
赛春嘎,1938 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他的文学创作至少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38-1945年)。在《压在苫笆下的小草》一首诗中,诗人把奴役人民的封建王公势力比作“破旧而腐朽的苫笆”,并预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你可知道一切陈旧的东西终归灭亡/新生的事物必然蓬勃成长/看吧,我将以巨大的威力挣脱你的纠缠/去和天空的曙光会面。”[12]在1939 年写的《窗口》中,诗人同样表达了热切地呼唤光明和自由的心情。在他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中,如在《成吉思的后代》、《希望之光》等诸多诗歌中,[mɔηgɔlogsa:]“蒙古族”、[mɔηgɔlodom](蒙古血统)、[mɔηgɔlt∫o:d](全体蒙古)等概念频频出现,而没有看到[mɔηgɔl ündüsüten](蒙古民族)一词。
(2)第二阶段(1945之后)。从1945年至1947 年,赛春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赫巴托高级党校学习期间,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许由于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期间受到了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影响,在他这时期的诗歌作品中开始出现了[ündüsüten](民族)一词,表明了他在民族观念上的重大转变。例如,在诗歌《杵臼之声》中他写道:“民族的兴旺/是儿女们的使命/展望未来/闪电般地前进。”[13] 在1947年的《迎接共产国际》一诗中写道:“在喧嚣的城市/宽广的广场上/各民族兄弟/聚集在一起。”[14]

不仅在18 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是国家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抢眼符号和动力源泉,这在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区政治变迁、文化语境下同样如此。
在蒙古地区的历史上,“蒙古人”意识并不完全等于民族主义的“蒙古民族”认同。在近代蒙古地区,除了“蒙人”、“蒙古民族”以外,在蒙古文文献与民间话语中还出现了一个十分笼统而模糊,但极具组织功能和动员能力的群体概念——[mɔηgɔlt∫o:d](泛蒙古或全体蒙古),值得我们关注。笔者认为,蒙古地区的近代民族主义并不完全相伴于[ündüsüten](民族)概念的出现,而与更具广泛特性的[mɔηgɔlt∫o:d]概念息息相关。[mɔηgɔlt∫o:d],由[mɔηgɔ]和[t∫o:d]组成,[t∫o:d]是表示多数的介词。[mɔηgɔlt∫o:d](“泛蒙古”或“全体蒙古”)概念出现于民国初期。1911年底,喀尔喀蒙古地区在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和杭达多尔济等上层精英的带动下获得了“独立”,此行动对包括内蒙古地区在内的全体蒙古社会共同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强烈激发和推动了蒙古地区“泛蒙古”或“全体蒙古”层面上的民族主义进程。这种民族主义是以“全体蒙古”共同体为动员和认同范畴的,集中体现在具有多数、众多之意的蒙古语——[mɔηgɔlt∫o:d]上。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角度看,只有蒙古人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出现重叠,才能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蒙古人“国家”意识形成过程可追溯到古代社会。对蒙古语ulus(国家)一词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可知,蒙古社会从部落或部族分裂、割据中产生了强大的政治集团———“兀鲁思”。兀鲁思(ulus),最早是突厥语词,它原来的形式为“兀鲁昔”(uluš),公元8 世纪左右被借入蒙古语。
到13 世纪,随着蒙古大汗国的建立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兀鲁思”具有了“国家”、“领土”、“人民”等宽泛而模糊的含义。众所周知,13 世纪初,蒙古社会进入了国家的鼎盛时期,蒙古大汗国建立后,蒙古社会进入了封建领主制时期,作为“兀鲁思”统治者的成吉思汗被称为“可汗”。尤其到忽必烈的元朝帝国时期,经历了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和李璮之乱,灭了南宋,巩固了北方、东北边疆,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多民族统一帝国。可见,“兀鲁思”是国家的雏形,但“兀鲁思”所体现的国家规模、性质和规则与近代以来的现代国家有本质上的差异。
进入民国时期,在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汉人排挤性种族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在蒙古地区精英和民众中形成了将中华民国称为domdad irgen ulus(汉人中国),把中华民国视作“汉民族国家”的习惯和话语,进而蒙古精英阶层和民众主张建立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但必须进一步澄清的是,清末民国时期蒙古精英上层主张建立的独立“国家”在性质上并不是西方意义的近代民主国家,而是仍以封建主、传统王公精英为统治者的蒙古独立王国。
喀尔喀蒙古地区独立后,东蒙古地区科尔沁右翼前旗乌泰的反应最为迅速。1912 年8 月,他发布了《东蒙古独立宣言》,表示支持和响应喀尔喀蒙古的独立行为,并宣布独立。其后,内蒙古各地王公精英相继宣布支持喀尔喀蒙古独立,其中有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科尔沁左翼前旗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拉喜敏珠尔和阿尔花公、喀喇沁右旗的海山等。特别是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趁机“怂恿各王公响应哲布尊丹巴活佛。他提议从哲里木盟起事,北联呼伦贝尔,西结西部各盟,和外蒙古统一起来,搞一个蒙古独立王国,这个计划曾得到各王公的赞同。”[15] 这就是当时蒙古地区上层王公精英中的“泛蒙古”或“全体蒙古”民族主义的具体体现。
进入民国后,蒙古地区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更清晰的方向和目标。贡桑诺尔布在1912 年正月明确提出:“这几年来,开办学校,训练军队,振兴实业,这一切都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做准备工作。”[16] 19 世纪20-30 年代,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与民族独立运动达到了高潮,蒙古文献与民间话语越来越强调[mɔηgɔlt∫o:d]概念。例如,20 世纪20-30 年代出现了抵抗汉人军阀、以捍卫蒙古土地为目的的著名的嘎达梅林起义。起义失败后,歌颂嘎达梅林的歌谣在蒙古民间广为流传,歌中唱道:“说起反叛的嘎达梅林/是为了[mɔηgɔlt∫o:d](全体蒙古)自己的土地。”[17]
在民族主义起此伏彼的清末民国时期,宗教人士成为动员民族主义的重要、核心群体。因此,多数王公精英利用民族与宗教的双重力量,不断使其独立行动神圣化,例如,呼伦贝尔的乌泰声称:“博格达葛根有法旨,断定我蒙古民族复兴的机会已经到来,只有大家起来战斗,一定能建成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国家。”[18] 这样,“在‘民族’的话语条件下,蒙古社会追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步伐,从追求民族平等地位的话语出发,利用蒙元帝国的历史资源和与中原社会差异的文化资源,在辛亥革命之际行动起来,谋求建立独立国家。”[19]与“泛蒙古”民族主义行为同步,在蒙古地区一部分王公精英中也出现了背向选择的现象,蒙古精英群体趋于严重的分化和多元认同,结果有些精英开始认同自认为“汉人国家”的中华民国。因为,当时很多蒙古王公精英已清晰地看到,蒙古人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不可能顺利实现,建立独立国家的意志不再是整合社会的力量源泉。这时,一部分精英就开始主张运用新的社会力量,如社会运动、改良或革命来建立新的认同。
民国初期,蒙古地区部分精英的行动转变恰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1912 年10 月和1913 年10 月,哲里木盟10 旗王公在长春两次举行东蒙古王公会议,讨论赞助五族共和、拥护民国,反对外蒙古“独立”。1913 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又召开了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 部34 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20] 无论在哪个处于特殊、窘迫政治环境的社会和群体中“民族”概念、话语及其认同有其独特作用,都很有可能引发或产生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正如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所说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某一民族集团想要具有自己的国家权力的感情,而且指他们自己想要依靠国家权力拒绝被压制、被支配的感情。”[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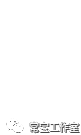
如前所述,在近代蒙汉文文献与民间话语中出现了诸多社会群体性概念,出现了诸多与[ündüsüten](民族)相关的概念,如:[mɔηgɔl hun](蒙古人)、[mɔηgɔl irgen](蒙古庶民)、[mɔηgɔl gajar](蒙地)、[mɔηgɔlodom](蒙古血统)、[mɔηgɔl ogsa:]“蒙古族”、[mɔηgɔle:mg](蒙古爱玛克),等。可用下表来进一步说明:

这些概念各有侧重点,即有些是地域概念,有些为群体概念,而有些是主观认同和想象的概念,从而造成了近代蒙古社会认同的多线性与模糊性。由此可以判断,蒙古地区从古代演进到近代,近代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的社会认同和意识是一种由地域、血缘、行政、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塑造的多线、复杂的认同体系。当然,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群体所凸显和注重的因素、内容和诉求各不相同。从蒙古地区社会认同的总体情况来看,学界和民众始终强调的核心因素和主线是“血缘”,“血缘”在整个社会认同体系中成为梗概和主题,从部落社会直至近代与当代,蒙古社会始终注重血缘关系与认同。
从20 世纪初期开始,在蒙古地区精英思想和民间生活中普遍流传并使用的[ündüsüten](民族)一词仍有浓厚的血缘意涵。从语言结构分析,蒙古语[ündüsüten]的词根为[ündüsü],含“根源”、“血缘”之意。[ten],作为助词不含具体、独立意义,但与独立型词根连接后可以表示“群体”或“领域”的意思,如[erdmten](知识群体)、[sge:ten](精英群体)、[ajilten](职业群体)等。因此,[ündüsüten]有“同根群体”之意。近当代蒙古语[ündüsüten](民族)一词,是蒙古精英在原有社会认同的基础上从传统蒙古语词库中选择,并对应当时汉语系统中的“民族”而生成的词,其表达的意义仍是传统性血缘关系,这与以往[mɔηgɔl ogsa:](蒙古族)、[mɔηgɔlodom](蒙古血统)等概念及其认同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除了仍保留传统语言、历史、文化、心理与信仰等含义之外,不具有显著的近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与“领土”内涵。至今,将汉语“民族”译为蒙古语[ogsa:](族)的现象依然很普遍。
正因为近代蒙古社会所呈现的民族认同具有多线性特点,造成了蒙古地区精英和民众经常混淆[mɔηgɔl hun](蒙古人)、[mɔηgɔl irgen](蒙古庶民)、[mɔηgɔl gajar](蒙地)、[mɔηgɔl odom](蒙古血统)、[mɔηgɔl ogsa:](蒙古族)和[mɔηgɔl ündüsüten](蒙古民族)等血缘、地域、共同体概念的现象,尤其在学术研究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无论是近代学人还是当代研究人员,对此都没有相对清晰的界定和认知。例如,在近代蒙古历史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日本学者山田茂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一书有一段典型的描述:“由于大元帝国建国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同情感———民族意识,可以说蒙古人已经不只是种族或部族,而是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了。民族意识已经成为‘兀鲁思’的强大支柱。民族的秩序和权威已经符合了‘兀鲁思’的要求。由于形成了民族,‘蒙兀儿—兀鲁思’恰好具备了民族国家的性质。”[22] 他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显然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形式,如此论证元帝国时期蒙古社会已具有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意识有些武断。
这就是蒙古社会多线性认同所导致的概念识别的模糊性特征。在当代蒙古语中,[ündüsüten]已成为普遍使用的词语,蒙古人不仅把自己称为[mɔηgɔl ündüsüten](蒙古民族),也将其他民族如将汉族称为[hetәd ündüsüten],将藏族称为[tubәd ündüsüten]。在国家层面的认同上,当代蒙古语将中国称作domdәd ulus,即“中央之国”(CentralState),将中华民族称为[domdaddi:n ündüsüten](称作中央民族)。可见,在这些国家层面概念的翻译和应用上,当代蒙古语更强调纯粹方位与地理方面的空间概念。因此,纳日碧力戈认为:“隐喻用空间中国来统辖文化中国可行且可靠;反过来用文化中国来统辖空间中国,就出现困难:中华文化不只是农业文明,还有游牧文明、游耕文明、渔猎文明等等,大一统的中国努力要让这些民族‘多元一体’。”[23]
[ündüsüten](民族)概念在近代以前的蒙古历史文献和文人、精英著述中从未出现,[mɔηgɔlündüsüten](蒙古民族)的出现和使用与近当代中国历史和民族政治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
在近代蒙古地区,“民族”[ündüsüten]概念的流行和使用无疑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内政治、汉人文化思想界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直接影响,蒙古民众和精英在传统的血统、部落、种族、宗教等概念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了“民族”概念,并为传统的部落、部族赋予了新的意涵。19 世纪末,西方“民族”概念已经传入国内,但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区绝大多数精英和民众并没有立即接受这一概念,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使用[mɔηgɔl hun](蒙人)、[mɔηgɔl ogsa:](蒙古族)、[mɔηgɔl odom](蒙古血统)和[mɔηgɔlt∫o:d](全体蒙古)等词语。从政治背景看,到了20 世纪20-30 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和中国国民党、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与引导,“民族”概念在蒙古地区被广泛使用,融进了民族地区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尤其在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乌兰夫等一群热血青年到北京蒙藏学校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民族理论,大大推动了蒙古地区的革命思潮,使蒙古民众与精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觉醒了。在斯大林“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24] 的观念指导下,蒙古族早期精英们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23 年,由多松年、乌兰夫、奎璧等人创办的《蒙古农民》刊物和后来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办的《内蒙国民旬刊》等都结合内蒙古的实际,把内蒙古农民问题与中国民主革命、把内蒙古地区民族问题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巧妙地联系起来,使内蒙古社会步入了民族革命的崭新历史时期。从本质而言,近代“民族”概念及其认同的出现是蒙古社会传统多线性认同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变异和狭义表述,是蒙古__精英阶层社会行动的实际需要。不言而喻,蒙古精英与民众“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意识在当代不是已经终结,但其认同方式和表述路径一定与西方“民族—国家”截然不同。构建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多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在这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多民族认同,如何解决和改善多民族关系,如何共同面对现代性危机等,依然是今日的重要课题。
注释:
[1][英]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2.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M](第1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172.
[3][英]冯克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00.
[4]张国强.贡桑诺尔布与赤峰近代化[M].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
[5]蒙籍议员忠告蒙人电[N].申报,1919-04-16(2).转引自张建军.清末民国蒙古议员及其活动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258.
[6]《德王为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实行自治致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1933 年10 月28 日)[C]//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08.
[7]尹湛纳希.青史演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26.
[8]尹湛纳希.青史演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34-35.
[9]罗卜桑悫丹著,哈·丹碧扎拉桑批注. 蒙古民俗鉴(蒙古文)[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231.
[10]罗卜桑悫丹著,哈·丹碧扎拉桑批注. 蒙古民俗鉴(蒙古文)[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41-42.
[11][蒙古]德·策德布、王满特嘎编著校正.内蒙国民旬刊(蒙古文)[G].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676.
[12]纳·赛音朝克图全集[G](第1 卷)(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6.
[13]纳·赛音朝克图全集[G](第1 卷)(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213.
[14]纳·赛音朝克图全集[G](第1 卷)(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367.
[15]德力格尔主编.哲里木史话[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5.380.
[16]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C]//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 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113.
[17]苏尤格主编.蒙古族文学史·现代[C](蒙古文).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25-26.
[18]博尔古德.札萨克图旗和镇国公旗的叛乱[C]//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 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67.
[19]周竞红.蒙古民族问题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37.
[20]转引自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12.
[21][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 ———以清末至 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5.
[22][日]山田茂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6.
[23]纳日碧力戈.民族问题、符号理论与结构耦合(上)[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15.
[24]斯大林.斯大林全集[M](第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61.
本论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中文核心)2014年第2期。
- 上一篇: 蒙古族通史——清初至1840年前的蒙古经济文化
- 下一篇: 蒙古语和中国蒙古族语言生活现状,了解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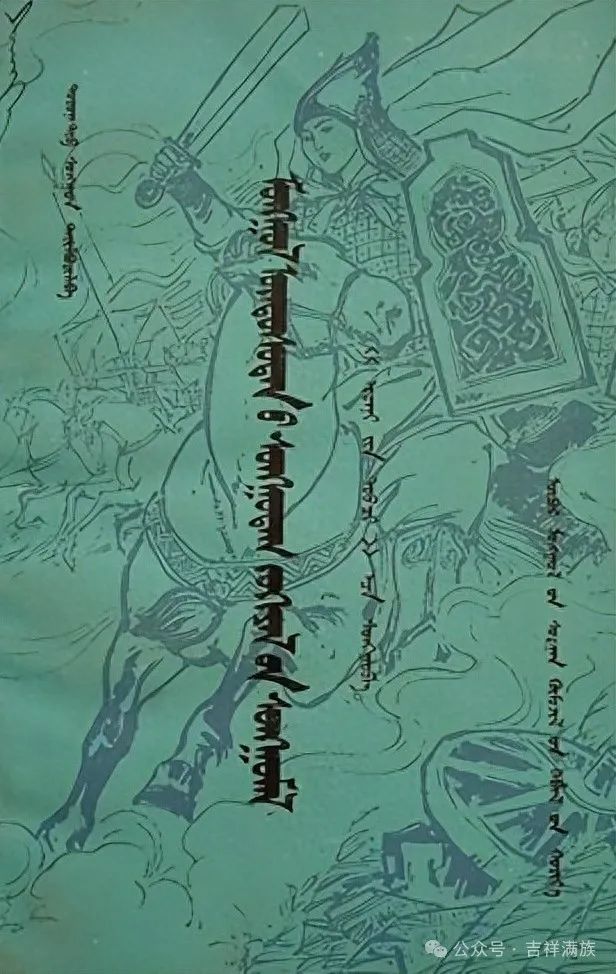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