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宫廷内府的《大藏经》, 刻有藏文、汉文、蒙古文、满文四种。蒙古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刻本,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为蒙古佛教典籍的总集,是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文化和知识的百科全书,在研究蒙古族历史和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蒙古文《大藏经》由《甘珠尔》(佛语部)和《丹珠儿》(论疏部)两大部组成,1720年(康熙59年)清内府在北京刻印蒙古文《甘珠尔》后朱刷经文,现仅存世8部,国内存6部。1749年(乾隆14年)清内府在北京刻印蒙古文《甘珠尔》完毕后朱刷经文,现仅存世3部,国内存2部。之后在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刻板朱印后的蒙古文《大藏经》在大漠南北和千里草原上,牵系着中央政府和蒙古贵族的政治交流,供养着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流转着蒙古族的文化传承,但是相对应的印经原板却鲜有资料和信息提及,甚为遗憾。
2010年,故宫博物院整理重刷《满文大藏经》(清乾隆59年清内府刻原板),在将经板拉往工厂刷印过程中,发现满文经板中混杂着近2万块蒙文《秘密经》、《诸品经》经板,之后故宫博物院专家对上述蒙古文经板进行了详细整理研究。

故宫藏清康熙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原印经板
经清点认看,上述经板计数19,076块,全部为康熙59年清宫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原板,其中尚未发现存有乾隆14年清宫内府刻蒙古文《丹珠尔》原刻经板。通过梳理一系列奏折和康熙皇帝朱批等清宫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刊刻办理蒙古文《甘珠尔》的一些细节,即:康熙55年,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开始奉旨主持刊刻蒙古文《甘珠尔》,至康熙59年刻印完毕;刊经底本使用善寿家藏抄本(善寿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后代,其家藏该抄本很可能是其祖辈征讨蒙古时所获之战利品);刊经的组织者主要是拉锡等人;经费来源布施化缘,但是康熙皇帝带头从内府经费中布施捐银;贝勒西哩、贝子善巴喇什等人,组织蒙古和北京的大德高僧远赴蒙古多伦诺尔庙校勘经文底本,进行统稿;在北京皇城内油毡房,由喇嘛巴克什监制缮写经文;定稿后在内府妙应寺(今北京白塔寺),由妙应寺大喇嘛诺尔布格隆刻制经板,刷成后经书交付武英殿保存备用,供蒙古王公贵族和大庙请用。同在奏折中,还详细罗列了制作蒙古文《甘珠尔》印经板所需经费,即:“刻制一部《甘珠尔》经诸项费用,耗银合计四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两九钱。刷印此一部《甘珠尔》经,需银二千二百八十七两四钱”。
这部耗时4年、耗银4万余两的清康熙宫廷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镌刻原经板总数应有40,952块,其中佛像插画经板216块、涉756尊佛像。然而沧海桑田,时至今日故宫仅存原经板19,076块,其中佛像插画经板仅存4块,更为遗憾的是,未存有乾隆14年宫廷内府刻蒙古文《丹珠尔》原经板。纵观世界其他大博物馆和拍卖,也暂未发现上述原经板的递藏信息。
然而历史总在不经意间给出惊喜,这就是时间和等待的意义。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2016年11月即将举行的秋拍中,征集到了清康熙宫廷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原经板7块,且全部是佛像插画经板,这是继故宫藏4块蒙文《甘珠尔》佛像雕板后的另外发现,且比故宫现存还多3块,同时还征集到了乾隆宫廷内府刻蒙古文《丹珠尔》“御制续藏经序”原经板2块,由于故宫现已无乾隆内府的这批遗留原经板,这2块御制序原经板很可能是“孤板”,因此这9块经板十分难得珍稀,对研究清代宫廷藏传佛教图像学、印刷史、文献史、雕版印刷工艺等均有积极意义,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在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的库房里,我们有幸近距离观摩欣赏了这9块经板,据了解,一位藏家几年前在法国巴黎一个偶然机会购藏了这些经板。经板所承载记录的文化、宗教、艺术信息几乎完整,具体可以分3部分辨识认看。

第一部分有3块,属康熙59年宫廷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经文扉页经板,用于经尾,左右边框分别以汉文、蒙文恭题该函(夹)的经名卷次和页码,经辨识,分别是“诸品经第十一卷下一”、“秘密经第三卷尾”,另一块由于边框被裁切无法辨识。每块全板均由藏传佛教5尊佛像构成,每尊佛像左右下角分别以满文、蒙文直书该佛尊号。刷成后经文页如下图内蒙古图书馆现藏康熙蒙古文《甘珠儿》原经页:


第二部分有4块,属康熙59年宫廷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上内护经板页,用于经头,左右边框分别以汉文、蒙文恭题该函(夹)的经名卷次和页码,经辨识,分别是“大般若经第五卷上一”、“第二大般若经四卷上一”、“三般若经第一卷上一”,另一块由于边框被裁切无法辨识。每块全板由藏传佛教2尊佛像分列左右、中间阳刻蒙古文“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及每函第一部经名卷数”,每尊佛像左右下角分别以满文、蒙文直书该佛尊。刷成后经文页如下图内蒙古图书馆现藏康熙蒙古文《甘珠儿》原经页:

第三部分有2块,属乾隆14年宫廷内府刻蒙古文《丹珠尔》开篇《御制续藏经序》。御制序原有3页,对应3块经板,可惜现仅存这2块。自明永乐皇帝刻印永乐版《大藏经》时,就形成了宫廷内府刻印大典时皇帝“御制序文,以冠经首”的惯例传统。乾隆皇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和康熙皇帝刻印蒙古文《甘珠尔》的遗志,下旨委托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活佛(清代重要宗教领袖,与乾隆皇帝维持了长达60年的宗教顾问关系,是清代宫廷佛教美术和仪轨的奠基人)主持翻译刻印蒙古文《丹珠尔》,并撰写《御制续藏经序》为经文开篇,这些信息在这2块经板御制序文字中有所体现,如:“我皇祖圣祖仁皇帝,能仁御世,觉悟群迷,尝取西番藏经译以蒙古文义,外番咸得通习”、“复得先辈章嘉胡图克图原著百千法语经七函”。
刷成后经文页如下图内蒙古图书馆现藏乾隆蒙古文《丹珠儿》原经页:



上述9块经板,镌刻精美,刀法严谨,部分位置还清晰可见当年刷印时遗留的朱砂。所刻文字字体规范,汉字楷体端庄工整,蒙古文和满文遒劲庄严,是典型清代宫廷官方书法。《甘珠尔》经板四周刻有西番莲和璎珞纹饰,双层莲花座。《丹珠儿》御制序经板四周刻有7对二龙戏珠(均为五爪龙)。细观这批经板所刻佛像插画,庄严肃穆,生动传神,意境高远,虽线条绵密繁复但清晰有序,细腻诠释了忿怒像和慈悲像,方寸间现般若宇宙,显示出精美高超的雕版工艺,以及雕板时那份虔诚纯净的宗教情怀。
故宫藏4块蒙文《甘珠尔》经佛像雕板和本次中贸圣佳7块佛像雕版、共计11块原佛像雕板的出现,对蒙文《大藏经》的研究、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清代宫廷佛教版画的研究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藏传佛教图像学传承发展,康熙蒙古文《甘珠尔》佛像雕版插画的艺术风格,继承自明代宫廷佛教写经,并在直接影响了清代宫廷藏传佛教图像的艺术风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示范作用。过去对于宫廷佛教版画,普遍认为乾隆满文《大藏经》水平最高、艺术最精。但是通过这11块蒙古文《甘珠尔》经佛像雕版与乾隆59年刻满文《大藏经》佛像版相较,满文大藏经佛像风格明显来源继承于康熙59年蒙文《甘珠尔》经佛像,虽略有差异,蒙文《甘珠尔》经佛像又源自台湾故宫藏康熙8年泥金写本藏文《甘珠尔》经佛像,康熙8年泥金写本《甘珠尔》经佛像则又来源于故宫藏明代景泰年间的藏文泥金写本《甘珠尔》经佛像。
近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员乌日切夫梳理史料研究发现,《清代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记载:“乾隆35年12月初三日,库掌四德、五德将西番红字《楞严经》一部经头经尾红字花纹佛像上用金描画不能盖住红色,并查得中正殿东配殿现供《甘珠尔》,经绦一条随铲子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经头上的佛像二尊,经尾佛像五尊,着中正殿画匠喇嘛画五彩颜色其边线,花纹红字不必描金经绦准用。钦此”。根据上述记载,可以肯定满汉藏蒙四种文字的清宫内府《楞严经》是按照康熙蒙古文《甘珠尔》的版印插画上五色彩绘模板,经研究比对故宫现存实物,两者风格确很相似。
综上,康熙56年开始制作的蒙古文《甘珠尔经》经版, 是继藏文《甘珠尔经》经版之后的又一重要活动,也是蒙古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它不仅成为蒙文《甘珠尔经》的最早经版, 也是所有蒙文佛经经版中的佼佼者,为康熙60年开始制作藏文《丹珠尔经》经版的工作, 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并为以后的清内府藏、蒙古、满、汉等文种《大藏经》得以问世, 创出了一条道路。同时,康熙宫廷内府蒙古文《甘珠尔》精美独特的佛像插画艺术风格,对清宫藏传佛教图像艺术和造像艺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感染力,直接影响了乾隆59年刻印满文《大藏经》这一清代最大的宫廷佛教盛事。作为康熙皇帝带头布施化缘筹措经费的蒙古文《甘珠尔》插图版画,其精美细腻程度甚至超过了半个世纪后刊印的清朝政府投资的满文《大藏经》的版画插图,可见这批9块印经板,是可以经过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的艺术珍品,在民间保存至今实属不易,甚为珍贵。
恒河沙数千万,然这9块经板却如沧海遗珠,孑然遗世,透过这些原经板,那些在朝堂上召对运筹、草原高僧千里进京、北京妙应寺寒暑过往、三世章嘉活佛灯下译经等等历史岁月,伴随着蒙古族人民对藏传佛教的虔诚发心,留给我们无限遐思。
注:感谢内蒙古图书馆研究员斯琴毕力格、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员乌日切夫提供有关图片资料,以及对本文的帮助。
- 上一篇: 世界通史性巨著《史集》中的蒙古人(插图)
- 下一篇: 樊泽星:錾在鞣皮上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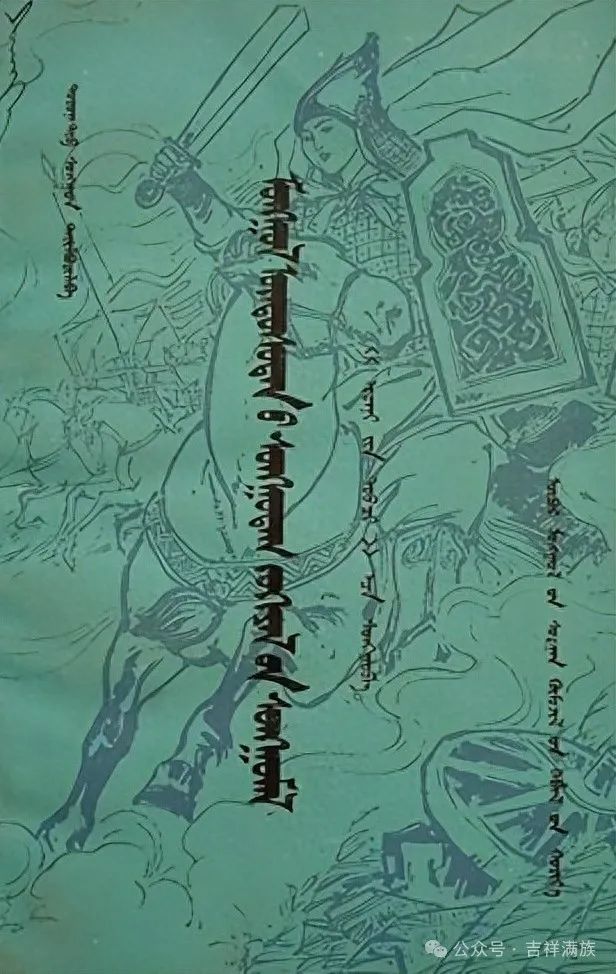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