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忽必烈时期元朝两次征日本,但因遇到台风,元朝征日本的行动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
这两次战役,日本称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称这一时期为"蒙古袭来"或"元寇袭来"。
《蒙古袭来绘词》描绘的是13世纪末蒙古入侵日本时,在日本登陆的蒙古军队与日本军队发生战斗而蒙古人被击败的故事,绘制完成于1293年2月9日。一般认为,‘绘词''是其主人公竹崎季长命令画师所作,故又称《竹崎季长绘词》。
由于竹崎季长亲自参加过与元朝的战争,其描绘的元朝军队的战船、阵容、服饰、兵器、发髻、旗帜等,对元朝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以及元代的造船、战术,蒙古的服饰、习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图后附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乌云高娃《蒙古袭来绘词》史料价值及其运用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26160784642668114.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27160784642775701.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27160784642766027.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27160784642793418.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28160784642838552.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28160784642866416.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29160784642949148.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29160784642919416.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0160784643011274.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0160784643033486.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1160784643128822.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1160784643178643.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2160784643257640.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2160784643216828.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2160784643288640.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3160784643376506.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3160784643338848.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4160784643431687.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4160784643463379.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5160784643557001.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5160784643510099.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6160784643635520.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6160784643647716.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7160784643728407.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7160784643732877.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8160784643888646.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8160784643822444.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8160784643868425.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9160784643965978.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9160784643981440.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39160784643920670.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0160784644034092.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0160784644057142.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1160784644176698.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1160784644127511.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2160784644285694.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2160784644243114.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3160784644366660.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3160784644395110.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4160784644444389.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4160784644490146.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4160784644423933.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5160784644523032.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5160784644547786.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5160784644530761.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6160784644611672.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6160784644624293.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7160784644759610.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7160784644733360.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8160784644877673.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8160784644816611.jpg)
![[转载]日本人绘制蒙古征日画卷【组图】](http://mgl9.com/zb_users/upload/2020/12/20201213160049160784644933460.jpg)
13-14世纪,蒙古帝国对东亚以及中亚、欧洲的历史均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在世界史上被称为“蒙古时代”。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族之后,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国。随着蒙古的兴起,蒙古铁骑震惊了世界,打通了东西陆路、海路交通,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历史、文化面貌。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通过军事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疆域辽阔、统一多民族的大蒙古帝国。尤其,到了忽必烈时代,灭南宋、使高丽臣服蒙古、东征日本,蒙古帝国对东亚的国际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忽必烈继位之后,想通过高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1266年至1273年间,忽必烈六次派使臣诏谕日本,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这与日本镰仓幕府深受南宋禅僧影响有一定的关系。10至15世纪,日本采取封闭政策,与周边的国家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忽必烈征日本是做为蒙古进攻南宋的一个环节。忽必烈想通过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以此来阻断南宋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日本与蒙古并无交往,但是与南宋有着私贸易往来。南宋的禅僧经常随着贸易船来往于南宋与日本之间,南宋禅宗对日本镰仓幕府影响很深。日本镰仓幕府关于蒙古的信息来源于南宋禅僧那里。南宋禅僧对蒙古怀有敌意,因此,日本镰仓幕府从南宋禅僧这里得到的是关于蒙古的负面信息。因此,在日本与蒙古的信息沟通环节上,南宋禅僧并未起到积极的作用。1274年和1281年元朝两次征日本,但因遇到台风,元朝征日本的行动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对这两次战役日本称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称这一时期为“蒙古袭来”或“元寇袭来”。
关于元日关系的相关资料相对薄弱。《元史》及元人文集中的记载较为简单。忽必烈诏谕日本的文书并未留下原件,在日本的寺院保存下来僧人的传抄本,为研究元日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蒙古袭来绘词》以图像的形式记录下来当时蒙古人与日本官兵的海战情况,在研究元日关系、元代造船史研究、元代服饰研究等领域均提供了具有较高价值的新史料。
《蒙古袭来绘词》是日本人竹崎季长亲自参加过与元朝的征战之后,绘制完成于1293年2月9日的长卷画册。以绘画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日本官兵与蒙古的对决。绘图之外还有解释战况的词。可以说,《蒙古袭来绘词》是研究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尤其对忽必烈两次征日本的研究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图像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并被日本学界研究日本史的专家学者所运用。相比之下,国内外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极少关注这一资料。尤其,国内学者对《蒙古袭来绘词》了解甚少,而且,有些学者可能通过二手资料加以运用,因此,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笔者在2005年至2006年在日本访学期间关注到这一资料,回国后也曾在文章中运用过这一资料,但未撰写专题论文对其进行介绍。近期阅读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和韩志远《元代衣食住行》等通俗读物时发现,这些学者运用《蒙古袭来绘词》这一资料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因此,笔者想写一篇文章简单介绍这一资料的情况及其史料价值。
一、《蒙古袭来绘词》史料价值
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多民族统一中央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性的封建王朝。这种华夷世界的变貌使东亚的国际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多事。蒙古在契丹和女真相对抗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迅速崛起,西征讨灭西辽,南下攻破金朝、南宋政权,东征高丽、日本,在东亚国际秩序中夺取了霸权地位。这一时期,在东亚国际秩序中蒙古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东亚三国的政治、外交、商贸、文化交流深受蒙古因素之影响。虽然,元朝征日本失败,但是,蒙古军对当时的日本影响深刻。在日本保留下来的《蒙古袭来绘词》这一资料对蒙古、高丽联军与日本官兵征战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从这一资料可以了解到当时蒙古人、高丽人、日本人、江南军的服饰、阵容、旗帜、元代造船情况等诸多信息,可以说这一资料在研究蒙元时期习俗文化、造船与航海等方面,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
《蒙古袭来绘词》的作者竹崎季长亲身经历了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后来战争结束后还受到了日本朝廷的赏赐。这一绘画卷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元朝军队与日本官兵会战的情景,对少贰景资等日本将领对抗蒙古的场景描绘的活灵活现,对蒙古阵营、船只也绘制得栩栩如生。同时,也是展示镰仓幕府的赏罚制度、御家人竹崎季长个性方面有价值的资料。但是,由于《蒙古袭来绘词》缺损部分较多,绘画和词之间的配置也有问题,有时出现难以正确理解配图与词之间的关系的情况。《蒙古袭来绘词》不仅对中世纪日本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对蒙古史、元朝史,以及13至14世纪中日关系史研究也提供了形象的新资料。
《蒙古袭来绘词》的史料价值较早地被日本学者发现,并运用这一资料对元朝两次征日本的战况、镰仓幕府的情况、竹崎季长个人等进行了研究。池内宏认为在日本关于元寇研究资料颇为缺乏的情况下,《蒙古袭来绘词》是元寇研究最珍贵的史料之一。池内宏在《元寇的新研究》一书中,较早的利用《蒙古袭来绘词》这一资料,对元朝两次征日本时在博多登陆;志贺岛、一岐岛、鹰岛海战的战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樱井清香则认为《蒙古袭来绘词》是元寇研究最大的珍贵的资料。但是,遗憾的是这一资料只是突出了竹崎季长个人参加这一战争的情况,而并未表现元寇研究的全貌。
《蒙古袭来绘词》现在作为皇室的御物收藏于京都东山御文库。笔者在2006年在日本访学期间,参加在京都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会后组织参观了京都东山御文库,有幸看到《蒙古袭来绘词》这一珍贵的资料。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蒙古袭来绘词》由前后二卷组成。各卷有纸的题签,分别写着《蒙古袭来绘词前》《蒙古袭来绘词后》。前卷宽39.3厘米,长为23.69米。后卷宽39.5厘米,长为20.335米。前卷有词15张,绘画21张,白纸8张。后卷有词7张,绘画20张,添书2张,白纸15张,前后卷各有44张。此外,还有十几种明治时期的临摹本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九州大学图书馆等地方。2009年笔者在日本大谷大学访学期间,发现大谷大学也有《蒙古袭来绘词》一涵三卷。这一版本并未被学界所关注,其画风有些粗糙,画面的颜色较为鲜艳。
《蒙古袭来绘词》应该是竹崎季长两次参加抗击元朝征日本战役时所绘制的战地绘图和战时日记。后来保存下来绘制成册。《蒙古袭来绘词》对蒙古军战船、登陆后的军容军貌、元朝军队的服饰、兵器、旗帜、战鼓等均有所描绘,为研究当时蒙古人的服饰、发髻、兵器、战法等问题提供了形象的资料。从元朝军队的服饰可以区分出蒙古人、高丽人或江南汉人的区别。《蒙古袭来绘词》对日本将领少贰景资、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的描绘也非常生动,而且,日本的将领身穿盔甲,手持扇子这些与元朝军队截然不同。从服饰、手持扇子、旗帜可以区分元朝军队与日本官兵的阵营和战船。从《蒙古袭来绘词》描绘的服饰中所透漏的信息,可以,判断绘画中的蒙古人是元朝第一次征日本时的情况还是元朝第二次征日本的情况。还可以判断绘画中出现的人物和战船是元朝军队的还是日本官兵的战船。竹崎季长在《蒙古袭来绘词》对服饰的描绘,反映了当时元朝军队和日本官兵服饰、发髻等方面的差别,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和韩志远《元代衣食住行》等书中,并未关注《蒙古袭来绘词》服饰所透出的信息,因此,出现了引用中的错误。
二、《蒙古袭来绘词》描绘的元军阵容
《蒙古袭来绘词》对日本将领少贰景资等对抗蒙古的场景描绘的栩栩如生,而且,对蒙古大小战船、阵容阵营也描绘得活灵活现。在竹崎季长笔下描绘的元朝军队从发髻、服饰、手持兵器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当时元朝军队的阵容。而且,从服装上也可以区分所描绘的是文永之役还是弘安之役的情况。而且,还从服饰和战船来能够区分所描绘的是元朝军队的阵容和船只,还是日方官兵的阵貌和船只。《蒙古袭来绘词》对元朝两次征日本时登陆后在陆地作战和海上作战的情况均有所描绘。
《蒙古袭来绘词》后卷中的“敌船”这一绘图所描绘的是元朝东征军战船内部的情况,反映了蒙古军在海上作战所持兵器、旗帜、蒙古人的发髻等情况。蒙古军手持的兵器有弓箭和长矛。图中右下角和中上部位出现两种不同的旗帜。中上部位的中间有个圆圈的旗帜,右下角的旗帜似乎有着动物图案。在其他描绘蒙古人阵营的绘图中也出现过这样的旗帜。坐于战船中间位置的头戴帽子之人明显身着汉式服饰,这很有可能是江南的艄公或是江南军。从蒙古人的发髻可以看出,是以蒙古的习俗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剃光,两边留着辫发。船上除了坐着的蒙古人以外,还有战士装备的手持长矛或弓箭的站在船部中央的蒙古人。这一绘图对了解当时蒙古人的留发髻的习俗,服装服饰研究等提供了较为生动的图象资料。从服饰穿戴比较单薄来看,这一幅图所放映的应该是元朝第二次征日本时的情况。因为,元朝第二次征日本的时间是在夏天的五月到七月期间。
《蒙古袭来绘词》前卷中的另一幅“敌船”图,也是描绘元朝与高丽联军战船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中上部分有两种旗帜。一幅是中间有圆圈的旗帜,这幅旗帜很有可能是高丽军队的旗帜。另一幅似乎描绘的是有动物图案的旗帜,这应该是蒙古军队的旗帜。东征军手持的兵器有弓箭,显然这部分人应该是弓箭手。还有手持长枪的,坐在船头的官兵手持盾牌。在船尾的几人有敲锣打鼓的,这明显是为征战鸣鼓助阵的人员。中间部位有艄公在划船。旗手、弓箭手、手持长枪者,身穿蒙古袍、脚蹬靴子、头戴皮毛一体的帽子,很明显所描绘的是冬天的装扮。可见,这一图所反映的应该是元朝第一次征日本时的情景。元朝第一次征日本是在十月的冬初开始。从两幅“敌船”所反映的服饰信息,可以看出元朝两次征日本的不同情况。
从《蒙古袭来绘词》前卷“大矢野、秋月、合田等的兵船出击”这一绘图中官兵的服饰、兵器、旗帜等能区分是元朝军船还是日本人的战船。但是,韩志远在《元代衣食住行》一书中运用了《蒙古袭来绘词》的两幅图对元朝的战船进行了介绍。韩志远运用的是“敌船”和“大矢野、秋月、合田等的兵船出击”这两幅绘图。韩志远将这两幅绘图均标记为元代战船。很明显韩志远在运用“大矢野、秋月、合田等的兵船出击”这一绘图时出现了错误,误将日本官兵的战船认为是元朝战船。“敌船”是元朝征日本时元朝军队的战船。但是,“大矢野、秋月、合田等的兵船出击”是元朝征日本时日本官兵所乘的战船。日本战船上日本官兵的服饰、帽子、旗帜与元朝军队的有着明显的不同。坐在战船中央位置或船头的应该是日本的官军,头戴头盔、身穿铠甲,手持弓箭。日本的旗帜是白色或黑白相间的长条的。从“大矢野、秋月、合田等的兵船出击”日本战船中艄公的穿戴和露着肩膀的服饰来看,这一图所描绘的是元朝第二次征日本的情况。元朝第二次征日本的时间是在夏季的五月至七月。
“大矢野、秋月、合田等的兵船出击”中的大矢野、秋月、合田等人均为参加日本对抗元朝东征时的将领。《蒙古袭来绘词》中的这一幅图表现了日本官军在海上抵抗元朝征日本战争的情况。
日本军与蒙古军相比较,双方在战术和武器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日本官兵没有对外作战的经验,日本武士主要以个人作战为主。另外,日本官兵穿着繁重的铠甲,在战术战略上也没有任何的优势。而蒙古军则轻装上阵,再加上蒙古与高丽联军采用集团军的作战法。同时,除长矛、弓箭之外,蒙古官兵还有铁炮等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蒙古军主要使用长矛和弓箭,蒙古军队与日本官兵在海上作战,蒙古军团的射箭在能够保障远程距离的进攻之外,具有着很大的杀伤力。另外,还有鼓手敲锣打鼓来助阵,锣鼓声音使日本武士、官兵震耳欲聋,影响其作战的劲头。
《蒙古袭来绘词》前卷中的“敌阵图”描绘的是蒙古与高丽联军的阵容阵貌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蒙古、高丽联军在服装上有所差别。最前面的阵容是手拿弓箭的蒙古人,身穿中长的蒙古袍、裤子、脚蹬蒙古靴,靴子上方部位比较宽一些。头戴皮毛一体的帽子,手持弓箭,腰间挂着箭筒之外,还佩戴着细长的腰刀。和“敌船”那一幅图中站在船部中央的蒙古人穿戴一样。在其后面的一波人在服饰和靴子与最前面的蒙古人有所区别。这批官兵身穿长袍,脚蹬靴子,但是靴子比前排蒙古人的靴子要细长。头戴棉布帽子。有手持弓箭者,也有手持长矛者。腰里挂着箭筒,但是,并没有佩戴腰刀。从其服饰看应该是高丽官兵的装扮。“敌阵图”蒙古高丽联军的阵容排列为步兵、骑兵、步兵、骑兵这样的阵势。前面阵容是步兵,盾牌后面是骑马作战的官兵,在其后有几排的步兵阵容。步兵阵容第一排的官兵手持长枪和盾牌。中间位置旗手手持的旗帜与两幅“敌船”中出现的中间为圆圈图案的旗帜相同。在其后的是骑兵阵容,手持弓箭、穿着铠甲的也许是军官,其余轻装的有手持长枪的官兵和敲鼓的几名鼓手。可见,元朝军队作战,敲锣打鼓也是其阵容中不可或缺的作战辅助手段之一。从元朝军队的服饰来看,穿着冬天的服装,长袍、靴子,明显是反映元朝第一次征日本时候的阵容。
三、《蒙古袭来绘词》中火器的出现
《蒙古袭来绘词》中有一幅绘图表现竹崎季长在鸟饲奋战的情况。从图中所描绘的铁炮爆炸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当时蒙古军在征日本战争中使用铁炮的情况。
《蒙古袭来绘词》前卷中“在鸟饲奋战的竹崎季长”这一绘图中,右侧骑马奋战的是竹崎季长,在他的对面有三个蒙古人装束者正在向他射箭,这几个人正是上述“敌阵图”中排列最前面的步兵阵容中的蒙古人。从空中和地上的箭头方向来看,所反映的是双方正在互相射箭。“在鸟饲奋战的竹崎季长”这一图中,在中上部位有铁炮爆炸的场景,铁炮爆炸之后,火焰朝向竹崎季长的方向。
元朝第一次征日本时,蒙古军于1274年十月十四日侵入壹岐岛,日本军防护失守。元朝军队占领对马、壹岐岛之后,经过松浦向东前行,目标指向博多。十九日东征军进而逼近博多湾,二十日先后从今津、百道原等地登陆,主力军以九州岛大宰府为进攻目标。日本方面以少弍景资为大将军来抵御蒙古的来犯,但日本官兵抵不住蒙古和高丽联军,死伤者无数。蒙古、高丽联军采用集团军的作战方法,并轻装上阵。在武器方面蒙古军队使用长矛、弓箭的同时,还有威力较大的铁炮。在这种新的战法和兵器的情况下,镰仓幕府的武士逐渐失去作战的信心,相继出现脱离战场的局面。从博多湾西部上陆的蒙古、高丽联军在鸟饲、赤坂、麁原等地与日本官兵进行了激烈的战争。从《蒙古袭来绘词》中的“在鸟饲奋战的竹崎季长”来看,应该是蒙古军侵入鸟饲之后,双方激战的阵前情况,图中在日本军官战马的前方有铁炮爆炸的情景,战马似乎受伤流血,而且,受到惊吓跳起来的样子。
“在鸟饲奋战的竹崎季长”中在拉弓箭的蒙古人旁边爆炸的就是铁炮。铁炮就是所谓的震天雷。铁炮有铁制或陶制两种。如韩国崇实大学博物馆藏“铁炮”是陶制的铁炮。目前未发现铁制的铁炮。2001年(平成13年)10月在日本长崎县鹰岛发现四个陶制的铁炮。铁炮直径为14cm,厚度为1.5 cm,容器中间是空的,装上火药,点火后投向敌方阵营,威力很大。元朝官兵在逃跑时会向敌方阵营抛掷铁炮,因此,铁炮有点像手榴弹的性质。“在鸟饲奋战的竹崎季长”这一图中,除了手持弓箭的三个蒙古人装束者在向骑马的竹崎季长射箭之外,还有几名高丽官兵向反方向逃跑的样子,这几个逃跑者很有可能就是抛掷铁炮的高丽兵。
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火器是由蒙古人传到日本的。元朝两次征日本的战争中,元军威力强猛的火药火器使日本人受到很大震动。日本的《蒙古袭来绘卷(词)》(1292年,1293年之误)中描绘了弘安之役的情景,说元军发射出的盛有火药的铁罐,向日本武士飞来,爆炸后冒出黑烟和闪光,伴随震耳欲聋的巨响,日本武士慌乱,人马死伤甚众。”这里提到的《蒙古袭来绘卷》应该是指《蒙古袭来绘词》(1293年)。李伯重所认为的《蒙古袭来绘卷(词)》(1292年,1293年之误)中描绘的是弘安之役的情景,这是不正确的。《蒙古袭来绘词》(1293年)“在鸟饲奋战的竹崎季长”这一图中,描绘出蒙古军使用铁炮的情况,当时,所描绘的并非是弘安之役(1281年)的情景,而是,文永之役(1274年)的情景。首先,元朝第一次征日本时元朝军队在博多湾登陆,日本官兵和元朝、高丽联军在鸟饲激战过。第二,元朝第二次征日本时由于日本在博多湾沿线20公里修筑“元寇防垒”,把东征军困在海上,防范了蒙古军在博多湾登陆。所以,李伯重所认为的《蒙古袭来绘卷(词)》(1292年,1293年之误)中所描绘的是弘安之役的情景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结论。而且,书中认为弘安之役是在1284年的论述也是错误的,弘安之役是1281年,而不是1284年。李伯重书中的《蒙古袭来绘卷》(1292年)是《蒙古袭来绘词》(1293年)的误写。很明显李伯重有可能参考的是二手资料,他也许并未看到《蒙古袭来绘词》,因此,连书名和成书年代都是错误的。
四、《蒙古袭来绘词》中出现的“元寇防垒”
由于,日本受到元朝第一次征日的危害,1274年元朝第一次征日本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日本在1275年二月形成了四季轮番分担军役的制度,并制定了九国轮番防御蒙古的军役。从1276年三月十日开始,约在半年的时间里,日本自西面的今津到东面的香椎,沿博多湾近20公里的海岸线,修筑了底部3米宽,高达2-3米的,为防范蒙古来袭而修筑的石头堡垒。在日本九州博多湾还留存着不少当时修筑的“元寇防垒”。笔者2006年在日本访学期间,到九州考察过“元寇防垒”遗迹。因为,博多湾海岸线的变化,一部分“元寇防垒”被埋入海底,一部分被埋入地下,现存的“元寇防垒”只是挖掘了一部分。
日本在博多湾修筑“元寇防垒”有效的抑制了蒙古军在第二次征日本时候在博多湾登陆,将蒙古军困在海上,有效地防止了元朝军队在海上登陆作战。
《蒙古袭来绘词》后卷中“菊池武房阵前行进的竹崎季长”这一绘图反映了元朝第二次征日本时“元寇防垒”的防御作用。图中生动地表现出日本官兵坐阵“元寇防垒”,防范元朝军队登陆的情景。
“菊池武房阵前行进的竹崎季长”这一绘图所绘的是菊池武房在博多湾松原附近“元寇防垒”防御“蒙古袭来”的情景。手拿红色扇子坐在“元寇防垒”上的是菊池武房,中间骑马行进的是竹崎季长。
1281年(弘安四年)元朝第二次征日本时,蒙古有十万官兵到了博多,但是,日本官兵坐阵石头防垒上,使蒙古军未能登陆,在海上转了70多天。九州博多现存的“元寇防垒”。就是当时日本官兵防御元朝军队的“元寇防垒”。
五、《蒙古袭来绘词》中出现的元代战船
在中国、日本、韩国发现了不少元代的沉船,为研究元代造船与航海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是,纵观这些沉船多为贸易船只,其船体较大,船室的分割也是为了存放货物。《马可波罗游记》中也对来自于印度的中国船只有所描绘,但是,也是属于有关贸易的货船。中国蓬莱登州港和日本长崎县鹰岛附近发现了元代的沉船,据考古学家鉴定为元代的战船。《蒙古袭来绘词》中出现的元代战船,可以与这些实际海底发掘的元代战船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蒙古袭来绘词》中出现的元代战船与蓬莱和日本鹰岛发现的元代战船形状相符,可以说,《蒙古袭来绘词》中出现的元代战船为研究元代造船以及忽必烈征日本时期元代的战船的形制、木碇等,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元朝征日本命高丽督造大小战船,忽必烈要求高丽助师、造船、输粮饷等事。1268年二月安庆公淐从蒙古回高丽,忽必烈指责高丽不履行助战、出兵、输粮等事。四月李藏用与蒙古使臣于也孙脱一同到蒙古。忽必烈敕藏用曰:‘尔还尔国速奏军额,不尔将讨之,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敢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正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这一史料证明,忽必烈命高丽督造战船一千艘,大小可载米三四千石的规模。
李藏用回禀忽必烈:“助师之命则虽是残民随所有而检俻,其办舟舰、输粮饷之事,则惟力是任,亦期将供。” 李藏用对忽必烈保证高丽将按时造船,并出师助战、输粮等事。池内宏认为忽必烈命高丽造船也是为了补充襄阳之战缺少船只的情况,命高丽造船与下令在陕西、四川造船,以助襄阳之战是同一时期。
因为元朝命高丽造船的时间紧迫、造船数量较多,因此,高丽在人员投入上下功夫,召集几万人加紧督造船只。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高丽金方庆和洪茶丘加紧督造大小船只。金方庆和洪茶丘在高丽庆尚道、全罗道等处召集人夫、工匠等三万五百名赶赴到全州道边山和罗州道天冠山等造船所,加紧督造大小船只。
金方庆在督造船只时,为了不废功夫,耽误工期,所造的船只未依照南宋的式样。为了图省事就依高丽船只的样式督造战舰。《高丽史》记载:“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诏方庆与茶丘监造战舰。造船若依蛮样则工费多,将不及期,一国忧之。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罗,遣人咨受省檄,用本国船样督造。”从这一史料可以看出,宋代的造船技术发达,造船的工序较高丽船样应该更废功夫。高丽的战船是平底船,这种船型适合在河流航行,不适合在海上作战。元朝在征日本时大量使用高丽战船,最后,经不起暴风,元丽联军第一次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蒙古袭来绘词》“敌船”一图中出现的元代战船,应该就是高丽督造的战船,船头和船尾高,平底。木制结构,船尾悬挂着木碇。木碇有船舶靠岸停泊时固定船只的作用,后来发展为铁锚。在日本九州博多湾和长崎县鹰岛附近发现了一些石碇或木碇,被认为是蒙古袭来时期的石碇,因此,被称为“蒙古碇石”。
1274年六月高丽派人到蒙古向忽必烈汇报舟舰已制造完毕,船只全部停放到高丽金州待命。忽必烈下令以七月为期征日本。《元史》记载:“十一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从这一史料可知,蒙古高丽联军征日本的船只有三种,一种为千料舟,这有可能就是忽必烈命高丽督造的“可载米三四千石”规格的船只。这种大船应该是运输粮食、战马、武器等所用的船只。一种是拔都鲁轻疾舟,拔都鲁是蒙古语勇士的意思。另一种是汲水小舟。《蒙古袭来绘词》中出现的元代战船有大小船只。“敌船”应该是规模大一些的属于第一种的千料舟。船上有蒙古人,弓箭手、鼓手、艄公等。《蒙古袭来绘词》中出现的有小一点的战船,有乘坐十人以内或十几人的战船,士兵们手拿盾牌把小船围城一圈,这个也是就是所谓的拔都鲁轻疾舟或是汲水小舟。
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征日本时,南宋灭亡,江南军与江南的船只加入到出征日本的行列。元朝第二次征日本以4500只船只,十几万官兵之规模出现在日本海,比元朝第一次征日本时的900艘船只出现在博多湾的规模要大的多。
从《蒙古袭来绘词》中出现的元朝第二次征日本时的战船来看,可以了解到当时元朝江南战船的情况。《蒙古袭来绘词》中“船上作战的竹崎季长”这副图表现的是日本将领竹崎季长于1281年七月五日在志贺岛与元朝军队进行海战,竹崎季长等日本官兵登上元朝的战船进行奋战的情况。从这一战船的形状来看,应该是元朝在江南制造的战船。船内有船舱,船舱有很多方形的像窗户一样的探口,旁边坐着弓箭手,很有可能从这些探口往外射箭之用。船头和船尾有甲板,船头的甲板上有手持长矛的官兵,正与登上战船的日本官兵奋战,船尾甲板上应该是艄公,穿着便服,手中没有武器,被日本官兵杀害的样子,脖子上流着血,倒在甲板上。这艘战船应该是中大型船只,日本官兵是乘坐小船,靠近元朝船只之后,登上大船作战的。这艘元朝战船的船尾与第一次征日本时战船的船尾不同,这艘船的船尾有两个能旋转的木轮,应该是艄公用来划水的水轮。这种水轮在《蒙古袭来绘词》中的日本战船的尾部也出现过。这证明日本的战船与南宋战船的设计有相互影响的地方。相对来讲,日本与南宋的接触及私贸易往来更为密切,在造船技术方面受南宋影响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总之,《蒙古袭来绘词》虽然是竹崎季长绘制个人参战、授奖等情况,但是,其描绘的元朝军队的战船、阵容、服饰、兵器、发髻、旗帜等,对研究元朝时期造船技术、海上的战术、蒙古的服饰、习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注】文章原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这是一套由10位不同的日本教授写的中国通史,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掀起一阵飓风!
- 上一篇: 婚礼邀请词 — 可以在请柬上写,实用(蒙古文)
- 下一篇: 学习这些汉词翻译成蒙古文怎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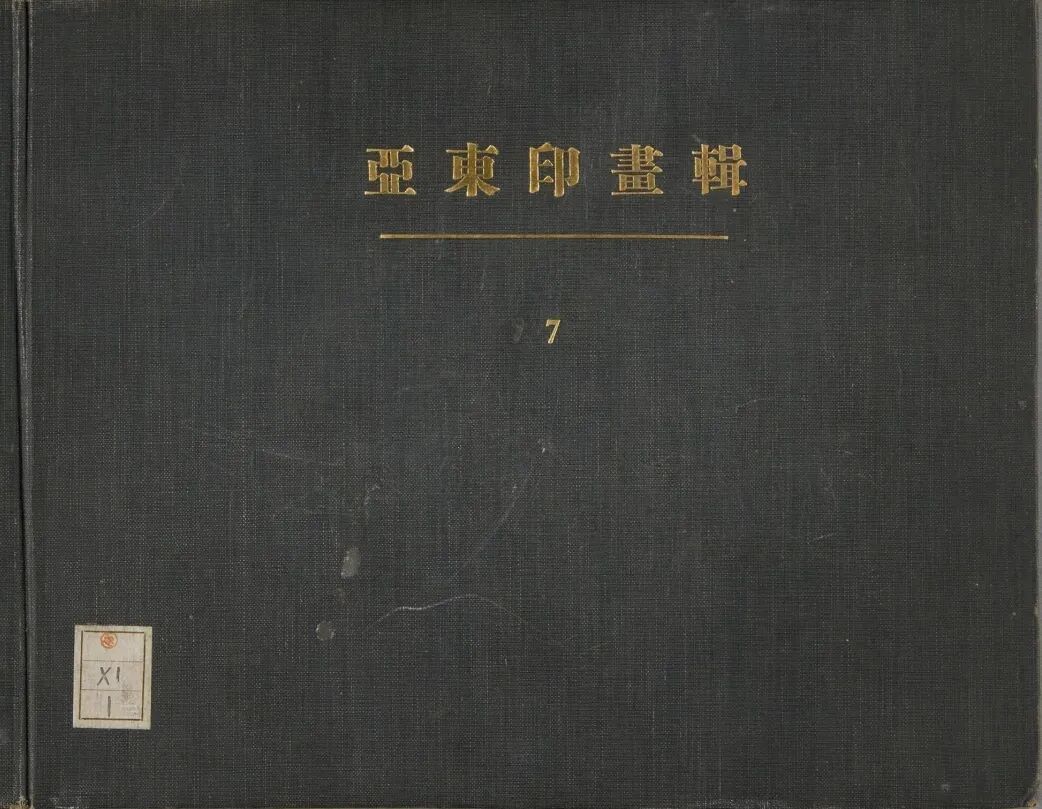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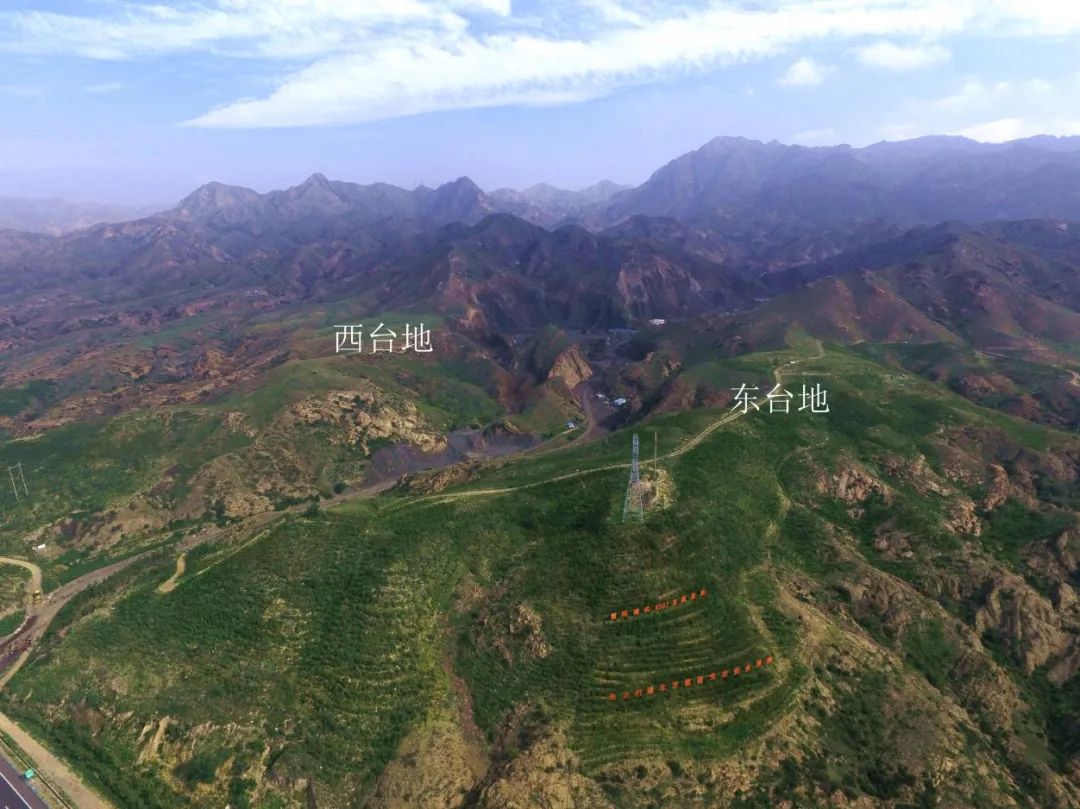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