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碑刻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集历史、文学、书法、镌刻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蒙元时期的碑刻文献异常丰富,其中蒙古文碑刻十分突出,分布地域辽阔,形式多样,数量众多,虽历经近800年的发展变化,但其仍然不仅以独特的载体形式保存了大量的书法篆刻艺术,而且也反映了当时草原地区的历史文化情况,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物史料,对蒙古学研究及史学考证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史料。蒙元时期碑文多为皇帝圣旨、皇后懿旨、皇子诸王令旨或帝师法旨。尤其元亡以后,元代碑刻散失在草原上渐被历史埋没,大部分元代典籍也因战乱而散失,这就导致蒙元史的研究因缺乏新资料而难度很大。明初编撰《元史》时尚在战乱时期,仓促成书,纰漏甚多。自明清以来陆续有学者立志于补写《元史》,但因档案、碑刻文献的缺乏,进展很缓慢,造成研究和补写工作收效甚微。本文对散在全国各地乃至蒙古国境内的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碑刻作一概要介绍,以便于大家的收集利用。
1.《成吉思汗石文(cinggis qaGan-u qilaGunbicig)》。亦称《也松格碑》,1224-1225年立。石高202厘米、宽74厘米、厚22厘米,铭文共蒙古文单词21个。内容为成吉思汗之弟哈萨尔次子也松格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返回途中在不哈速赤忽之地举行盛大庆祝大会时,也松格远射335丈之地,为此立碑纪念。石碑是19世纪初俄国人于蒙古额尔古纳河上游发现的,今收藏在圣彼得堡市艾米塔尔(Ermitar)博物馆。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过此碑文。《成吉思汗石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部蒙古文石刻文献,它向我们展示了蒙古书面语使用20年间的书法有关蒙古文碑刻模式,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2.《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大蒙古国时期汉文白话文和蒙古文两种文字合璧碑铭。碑文为太宗窝阔台十二年(1240)圣旨。这是现存最早的年代明确的蒙古文碑铭。此碑在河南省济源市十方大紫微宫,故称为“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碑文拓片收藏在北京大学艺风堂缪氏旧藏碑拓中。碑铭为“也可合敦大皇后懿旨并妃子懿旨”,刻有蒙古文3行,汉文11行。内容为根据窝阔台皇帝的圣旨,由大皇后与诸合敦下达的关于让山西命沁州管民官杜丰监督雕造道藏一事的懿旨。文末有一段威慑性的文字“如违要罪过者”,最后署懿旨写成的时间(庚子年三月十七日)。此庚子年必在杜丰死(1256)前,于是人们推测懿旨颁布时间应为1240年。
此碑1951年由蔡美彪发现,之后他制作了该碑拓片并对其汉文部分进行了介绍[①]。碑文中写道:“也可合敦大皇后懿旨并独诸妃子懿旨”,当时蔡美彪认为“此也可合敦当即脱列哥那六皇后乃马真氏”。这一推测曾被国内外学者赞同,或乃称为脱列哥那皇后懿旨[②]。1989年蔡美彪重新进行考证后指出:发布1240年懿旨的也可合敦大皇后不应是脱列哥那六皇后,而是另一个合敦孛剌和真,并认为紫微宫碑的大皇后推定为孛剌和真,自然最为合理[③]。碑末有三行15个字回纥蒙古文。这十五个字是在一般圣旨、懿旨等最后写的 “我的懿旨不依的,不拣甚麽人,断按打奚死罪者。准此,鼠儿年……”等语。看来蒙古文字未全刻。
3.《窝阔台汗时期的景教瓷碑》。该碑出土于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文字是用古回鹘文书写在瓷碑上的,记述了一位蒙古将军在此建立宫殿的过程。瓷碑呈长方形,胎质较粗,釉呈黄白色,碑体外缘边框用粗大的铁锈色线条勾勒,框内绘出一个大十字架,以十字架为主体将碑面分割成4部分。在这4个区域内,上部的两个空白处书写着两行竖写的古叙利亚文,可译为“看见你”和“想着你”。在十架下部两个空区,从左至右写有8行古回鹘文,内容可译为:“从亚历山大汗算起一千五百六十四年,从中国纪年算起,于牛年正月二十日,术安·库木哥将军匕十一岁时,按照上天的旨意,将这座宫殿和围墙完成。
在这建筑的地方,立起与天永久的石碑。”碑文中写的亚历山大汗是古希腊的著名帝王,公元前336年即位,公元前323年去世。当时刻碑者是以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一年为纪年起点,所以考古学家们据此便推算出了碑的纪年为公元1241年,即蒙古太宗(窝阔台汗)十三年。此碑在纪年的表述上,既有蒙古传统的十二生肖纪年,又有用古希腊亚历山大逝世之年(公元前323)纪年的方法;此外,在瓷碑上,还绘有希腊式的“十”字图案。这些文字和图案,证明了窝阔台汗时期与欧洲曾保持着联系,可为《元史·太宗本纪》作补充。
4.《贵由汗玺文》(gUyUg qaGan-u tamaGan bicig)。大蒙古国第三代大汗贵由(gUyUg,1206-1248)汗玺文,蒙古文刻写。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在1923年至1931年间刊布的《蒙古与教廷》(Les Mongols ed ia Papaute)一文中报道了他于1922年夏亲眼目睹贵由汗印章的具体情况:该印玺是大蒙古国大汗贵由汗于1246年12月给罗马教皇因诺曾爵四世(Innocent Ⅳ)信札的波斯文译文上所盖的印玺。信札是用黑墨写于蒙古人常用的黄色波斯纸上。文中盖有蒙古文贵由汗印章两处(波兰神甫西利尔·卡拉烈夫斯基于1922年1月12日交来所记此项文件外形时所盖这两块印章为宽长各异,伯希和纠正这一说,指出:所谓宽长各异者,盖纸之伸缩有以致之。[④])这两块印章皆用同一印玺钤盖,印方形,都是朱色,印章长14㎝,宽14㎝;每印文有字6行,仅有细栏围之。盖有贵由汗印玺的波斯文信札今保存于梵蒂冈档案馆。印文为蒙古文,用现代汉语翻译为:
凭借长生天的力量,
大蒙古国大海汗的圣旨,
如果颁发到将要臣服的人民那里,
他们应当对旨意表示尊崇和敬畏。
贵由汗的印文清晰可辨。由于早期蒙古语文物留存极少,使得我们对一些古蒙古语词汇和字母的最初形态还不是很肯定,在这种情况下,贵由汗印文的发现无疑更加显现出其珍贵价值。伯希和根据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an of Plano Carpini )出使报告中的记载,推测此印玺为在蒙古汗廷中服务的一名俄罗斯工匠科斯马(Kosma)所雕刻[⑤]。但仔细观察附图印文,有一些有趣的现象。蒙古文属于竖体的拼音文字,书写起来长短不一,把这长短各异的18个词汇整合限定在印章面的范围之内,又要做到整体美观,确实要费一翻心思,由此也可见印章篆刻人拥有相当高的篆刻水平。
5.《释迦院碑记》。大蒙古国时期蒙汉文合璧碑铭,立碑时间为1257年。1953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考察队在库苏古尔省阿尔宝力格县境内的得力格尔河北岸的一处元代古城遗址上发现。石碑正面上方为汉文碑额“释迦院碑记”五字,左侧刻汉文12行,右侧刻回鹘式蒙古文3行。碑刻今收藏在蒙古国中央博物馆。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考察队成员那木南道尔吉首次介绍该碑的发现经过,公布了石碑照片,并对碑文作了初步解释。此后,195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隆、1959年永谢布·仁钦、1961年美国尼古拉·鲍培等相继对此碑进行过研究,发表文章,各述其见[⑥]。
因为该碑字迹漫漶不清,释读起来很是困难,学者们虽有研究,但许多地方还各执一词。根据汉文内容,这是当时外剌(oyirad, 斡亦剌部)部驸马八里托(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之孙,从血源上讲他也是成吉思汗的外孙)和公主一悉基舍财建寺,为蒙哥皇帝祝福,为自身祈福而树立该碑。碑上的三行蒙古文的读法学者们一度有不同看法目前一致认为,美国学者尼古拉·鲍培所提出的读法顺序是正确的:碑文三行中第二行即由蒙哥汗御名抬头的中间一行,应视为实际上的第一行。这样整个碑文末的三行蒙古文字的读法顺序应为:当中一行为头一行,然后依次读第一行、第三行[⑦]。我们现按鲍培的读法将碑文用拉丁文音写排列则应是如此:
(1)(原刻中间抬头行)Mongke qaGan tUmen tUmennasulatuGAi kemejU bars tOge bosGaGul[ju?ba?](蒙哥汗万万岁,八里托建立[了?])
(2) (原刻第一行)oruGunoruGaiGar kedUn kedUn Uyes-te(子子孙孙延到几代)
(3) (原刻第三行)kUrtele enetabariGtu buyan kUrtUgei .(将这因缘福分享受吧)
该碑的发现,不仅为研究中世纪蒙古语言文字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研究大蒙古国时期的历史、宗教提供了珍贵资料。
6.《少林寺蒙汉文圣旨碑》。蒙元时期蒙古文和汉文对译的圣旨碑,现存河南登封少林寺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宽敞的庭院中。大雄宝殿月台下有八通大石碑,分列甬道两侧,每侧一列四通。蒙元时代《圣旨碑》是甬道西侧自北向南排列的四通大石碑中最北面的一通,紧挨在月台脚下。碑身高248㎝,厚32.5㎝,宽118㎝,碑额高78㎝,龟趺座高51.5㎝,通高377. 5㎝。碑的阴面,碑额环雕盘龙,圭上刻汉字隶书“圣旨碑”三字。碑身分四截。上面三截为回鹘式蒙古文,最下面一截为八思巴字。最上面一截刻蒙哥汗于牛儿年(1254年)颁给少林寺长老福裕的圣旨,共15行;第二截刻忽必烈汗于鸡儿年(1261年)颁给少林寺五位长老的圣旨,共39行;第三截刻忽必烈汗于龙儿年(1268年)委付肃长老为河南府路众和尚提领的圣旨,共49行;最下面一截即第四截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于鼠儿年(1312年)颁给河南府少林寺、空相寺、宝应寺、天庆寺、维摩寺长老、提点、监寺为首诸和尚的圣旨,共32行。其中前三道属蒙古汗国时代即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以前的碑刻,用当时蒙古族通行的回鹘式蒙古文书写。
最后一道是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以后的八思巴文写的碑文,在一件文物上同时保存着蒙古族使用过的两种文字,并且从时间上反映出这两种文字的交替情况,此碑当属首例。碑的阳面,碑额无字。阳面碑身刻汉字,也分为四截。内容与阴面四截相同。碑身阳面右方自上而下镌有“延佑元年孟冬吉日立”九个字,表明上述四道圣旨合刊一石的时间为延佑元年(1314)[⑧]。从碑文所用的语体看,阴面的蒙古文,无论是回鹘式蒙古文还是八思巴字,都非常明白通顺,与当时的蒙古文文献风格一致,属于标准语体。而阳面的汉文则属于所谓的“元代白话”,不是当时的汉语标准语体。“元代白话”以汉语北方话为基础,其基本的词汇和语法贴近当时口语,同时又掺杂大量中古蒙古语成分,不熟悉蒙古语的人很难读通。少林寺蒙汉文圣旨碑原文多用回鹘式蒙古文或八思巴字写成,再译为白话汉语,具有鲜明的直译体特征。
从内容上看,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颁发给寺院僧侣的护持文书,此碑亦属首例。三道回鹘式蒙古文圣旨中的蒙哥汗圣旨,时间仅次于现存的《也松格碑》和《贵由汗玺文》,属于早期碑刻文献,弥足珍贵。学者们认为,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发现为回鹘式蒙古文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蒙汉对译的圣旨文本对判定一系列词语的确切意义,解决一些专有名词的译法问题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助于研究古蒙古语吸收汉语借词的规律,了解当时汉语对蒙古语影响的程度。该《圣旨碑》为我们研究蒙古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新材料。[⑨]总之,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发现,对研究蒙古语言史、文字史,对研究蒙元时代的宗教政策、政治制度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研究少林寺的历史发展沿革变化更有特殊意义。少林寺元代《圣旨碑》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7.《蒙哥汗圣旨碑》。蒙汉文合璧圣旨碑。碑文镌刻在少林寺蒙古文圣旨碑阴面最上面一截,碑文末端所写时间为“葵丑年的十二月初七日”即1254年。阴面碑文蒙古文15行,相对阳面汉语白话译文24行。蒙汉文内容一致,但行数不同。这道圣旨碑原为口传的圣旨,是蒙哥汗于牛儿年(1254年)颁给少林寺长老福裕的圣旨[⑩]。碑文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再一次确认了曾令福裕管辖哈喇和林所有和尚的事实;后半部分则叙述了再令福裕任蒙哥时代的“都僧省”,继续管理哈喇和林诸佛僧的内容。
根据本圣旨,完全可以认为,贵由汗时代到蒙哥汗时代,居于哈喇和林的所有僧侣,无论其出身与教派如何,都完全置于曹洞宗福裕管辖下的事实。通过这一道圣旨,我们还了解到,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对佛教是采取保护政策的,并且以任命僧官的形式来巩固佛教的地位。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少林寺作为中原的一座名刹是受到蒙古族统治者高度重视的。
8.《忽必烈汗鸡年圣旨碑》。蒙汉合璧忽必烈汗圣旨碑。碑文镌刻在少林寺蒙古文圣旨碑阴面第二截,碑文末端所写时间为“鸡儿年六月初一日”即1261年在开平(元上都)“写来”。蒙古文39行,相对阳面汉语白话文32行。蒙汉文碑文内容相同,是由忽必烈汗颁发给少林寺少林长老、宝积坛主、姬庵主、圣安长老、金灯长老等五管领人的圣旨[11]。圣旨明确指出,五个管领人在八思巴师的属下管理汉地佛教,同时对属于禅宗的佛教僧侣与藏传佛教僧侣的关系,佛教僧侣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僧俗之间的诉讼、审判问题,都有规定。该碑刻内容对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大有裨益。
9.《忽必烈汗龙年圣旨碑》。蒙汉合璧忽必烈汗圣旨碑。碑文镌刻在少林寺蒙古文圣旨碑阴面第三截,碑文末端所写时间为“龙儿年正月二十五日”即1268年。蒙古文49行,相对阳面汉语白话文33行。蒙汉文碑文内容相同。圣旨内容为委付少林寺肃长老为河南府路众和尚提领的圣旨[12]。圣旨中明确指出,如果众和尚当中发生任何纠纷,都要根究八思巴大师的意见和经典的例规,由肃长老提领按规矩决断。学界认为,在少林寺蒙古文碑铭中这道碑文书法极好,不但书写流畅运笔娴熟,笔势饱满,而且笔误最少。从研究蒙古文字史角度看,是很值得注意的。
10.《少林寺八思巴字圣旨碑》。八思巴字音写蒙古文与汉文合璧圣旨碑。碑文镌刻在少林寺蒙古文圣旨碑阴面第四截,碑文末端所写时间为“鼠儿年三月十三日”,即皇庆元年(1312年)三月十三日。八思巴字32行,相对阳面汉语白话文30行。这是武宗海山卒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普颜笃皇帝继承皇位的第二年。是迄今所见普颜笃皇帝8道同类圣旨中最早的一道。[13]可见,中原少林寺等五座禅宗寺院受到仁宗普颜笃皇帝的优先重视。碑文内容为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颁给河南府路嵩山祖庭大少林寺、空相寺、宝应寺、天庆寺、维摩寺长老、提点、监寺为首的诸和尚的圣旨。
元朝时期(1271-1368)所遗留的石刻文献很多。其中主要的有:
1.《张氏先茔碑》(zhang ying soi-yin uridus-yuGan tula jarlaG - iyar bayiGuldaGsan bi taS)。元代蒙汉文合璧碑。全称为《大元敕赐故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茔碑》(碑额题)。“元统三年”,即1335年立碑。碑通高56.3㎝,宽13.5㎝,厚3.7㎝,碑首正面用汉文篆书额题四(1行?)行:“大元敕赐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碑首背面为篆刻八思巴字四行,内容同碑首正面的汉文。碑身正面为汉文楷书,字体端庄雄健,共39行约2000多字。碑身右侧刻有“大都西南房山县独树村石经山铭石”的字样,由此表明,石碑是在现在的北京山县石经山所刻,历经千里才运到草原上。碑身背面阴刻57行3000多字的蒙古文,是碑刻汉文的译文,是内蒙古元代碑刻中字数最多的,也是元朝石碑中蒙古文字数最多的。发现地点在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北80公里处的国公坟之地(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梧桐花乡国府村鸡冠子山东南坡)[14]。虽然历经600多年的风雨,但是字迹仍然清晰可辨。碑文内容繁富,史料价值很高。记述了世居蒙古弘吉剌部的汉人张应瑞及其子孙为元代以及蒙古弘吉剌部首领尽忠效力之事。
最早研究该碑文的研究者是日本学者田村实造。他于1937年在“蒙古学”(Mongolica)首次发表碑文。之后是美国学者柯立夫(F.W.Cleaves,1911--1995)。他于1950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3期)(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了《1335年为纪念张应瑞所立汉文蒙古文碑铭(张氏先茔碑)》[15]一文,全面介绍蒙汉文碑铭,也附拉丁文转写和碑文影印拓片等。墓主人张应瑞,为蒙古弘吉剌部贵族的王傅。书写碑文的作者为元代大书法家康里子山。此碑对于研究元朝宗室与蒙古帝王的关系以及元代的文化和民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竹温台公神道碑》(daruGaci jegUntei-yinyabuGuluGsan sayid Uiles-i uqaGulqui bii taS)。元代蒙汉文合璧碑。全称为《大元敕赐故诸色人匠府达鲁花赤竹公神道碑铭》(碑额题)。“至元四年五月吉日建”,即1338年立碑。碑通高46. 7㎝,宽15.1㎝,厚2.7㎝。碑首正面汉文篆书额题四行字。碑首背面为蒙古文“daruGaci jegUntei-yin yabuGuluGsan sayid Uiles-i uqaGulqui bii taS”三行字,内容同碑首正面的汉文篆书额题四行字。碑身正面阴刻汉文楷书,共27行。碑身背面阴刻37行蒙古文。该碑1921年发现于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南3.5公里处的乌兰板村,名为“大元敕赐故中顺大夫诸色人匠都总管府达鲁花赤竹君之碑”的石碑,石碑的发现者是一个名叫李彬的农民。
碑文首先简要记述了蒙古人竹温台是鲁国大长公主的陪臣,鲁王十分宠信他。竹温台善于畜牧,他的畜牧秘诀是顺其自然,依照动物本身的天性让它茁壮成长。遂冒鲁王族弘吉剌氏,家居弘吉剌部驻冬之地全宁(今翁牛特旗乌丹镇西),成为全宁人的情况。然后记述了竹温台在全宁时期善于牧养,家有马牛羊过万。竹温台由陪臣升为弘吉剌部极有实权而管理财政的高层人物的经过等。[16]碑文也详细记述了元朝时期,弘吉利部除了享有其驻牧地应昌、全宁的全部收入外,还收入其他州县交纳的差科。这些财产的收入最后都要归入鲁王府。竹温台从那时候便开始经管鲁王府的经济收人,同时,还掌管官府开支、赏赐、贸易、手工业、畜牧业、农业等一系列事务。竹温台在职期间,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1323年,年仅42岁的竹温台逝世,全府上下一片悲痛。正如碑文中所言:“府中如失其兄弟,境内之民如失其父母。”竹温台在世期间,曾经得到大量的赏赐,碑文中予以详细罗列。竹温台在草原上的卓越成就,一方面与他超群的才华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鲁王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体现。最早研究该碑文的是日本学者田村实造。
他于1937年在“蒙古学”(Mongolica)首次发表碑文。之后美国学者柯立夫(F.W.Cleaves,1911--1995)于1951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4期)(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了《1338年为纪念竹温台所立汉文蒙古文碑铭(敕赐诸色人匠府达鲁花赤竹温台公神道碑)》[17]一文,全面介绍蒙汉文碑铭,附拉丁文转写和碑文影印拓片等。该石碑内容丰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遗憾的是,该石碑已经不存在了,幸好碑文上的内容巳经被完整地记录在了《翁牛特旗志》中。由于有了碑文抄件,后人对竹温台这位元朝卓越的蒙古族畜牧专家和理财能手才有所了解。根据碑文的记载,再结合元朝史料并参考应昌、全宁两座古城发现的文物,可以对当时这两座草原城市的经济、文化以及弘吉剌部的显赫地位做进一步了解。
3.《云南王藏经碑》(Un nam ung Ganjuur nom-idelgegUlkU -yin kUsiyen bicig)。元代蒙汉文合璧碑。亦称阿鲁王碑,1340年立碑,今存于云南省昆明市西郊玉案山筇竹寺内。碑通高148㎝,宽83㎝。正面刻有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于延祐三年(1316)颁给筇竹寺主持玄坚和尚的圣旨。石碑背面刻有云南王阿鲁于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颁给筇竹寺的用回鹘蒙古文写的令旨。令旨上方有八思巴字镌刻“云南王藏经碑”六字。碑上的回鹘蒙古文令旨共20行,行款从左到右竖写。从20世纪20年代起学者们开始研究此碑。符拉基米尔在他刊布的《蒙古文“五卷书”的故事》[18]的注释中将“云南王藏经碑”称作“多龙(d'Ollone)在云南发现的石碑”。后来符氏把这个碑又称为“1340年云南王阿鲁石碑”。伯希和(P. Pelliot)则称之为“1340年的蒙古文碑”。
后来,蒙古国的罗布桑巴拉丹、匈牙利的G.卡拉、美国的柯立夫等人陆续发表了此碑的研究报告。[19]碑文主要内容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阿鲁(AruG)王简述了当地的“耆宿百姓”为他树碑的缘故。同时令旨内容涉及“秃坚、伯忽之乱”。碑云:“伯忽、阿禾、秃坚诸王叛后,俺的百姓非常困乏,死者被弃下,残存者缺乏食物,寻食物去了,俺的逃亡者很多啊。如今俺的死者如同复活了一般,俺的逃亡者全都回来了,太师来后,俺的田禾好起来了。俺的百姓做生意也如以前一般了。树碑的缘故如是。”碑文的后一部分与本碑文令旨上方用八思巴字镌刻“云南王藏经碑”内容相合。碑云:“为报答大长公主(指阿鲁王姑母)收继的恩情,双亲养育的恩情,把自己的梯己钱给筇竹寺槠币一百五十锭,每年用其利息诵大藏,为皇帝祈福,并报答大长公主收继的恩情,双亲养育的恩情,给该寺以为常住。这诵大藏的槠币是俺的梯己钱,不拣兄弟、亲戚、伴当、奴婄均不得争夺!着筇竹寺收执令旨。”[20]此碑为考订元史尤其是元代云南史事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该碑保存得相当完好,对于研究蒙古语言和文字史,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4.《敕赐兴元阁碑》。汉文蒙古文对译残碑。“丙戌年十一月初七”,即1346年立碑。发现地点在蒙古国旧都哈剌和林(karakorum)遗址上,残碑今存于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该碑是受大元皇帝妥欢帖木儿的敕命,由许有壬(1287~1364)撰写碑文,在大蒙古国故都哈剌和林所立。19世纪末俄国拉德洛夫(Radloff)探险队在大蒙古国旧都哈剌和林城遗址(今蒙古国前杭爱省)上首次发现其断片,今存于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该碑的汉文碑文在许有壬的《至正集》、《圭塘小稿》中已经全文载入,因此传世。原碑石在16世纪末原地建立额尔德尼召之时被断开,当做堂宇基石或修筑栏杆用的石料。至今已经发现的断片有9片。1892年俄国拉德洛夫(Radloff)探险队发现了两枚碑片,1926年苏联学者鲍培(N. Poppe)又发现了两枚碑片[21]。
在此前,于1912年波兰蒙古学者科特维奇(В. Котвич)访问哈剌和林城遗址时发现了三枚断片[22]。科特维奇所发现的三枚断片被嵌入在额尔德尼召佛塔基石里,因僧人们的反对而未能取出。三枚断片的内容是与拉德洛夫所发现的两枚断片连接的。对此三枚断片,科特维奇于1918年只是做了报道,最终并没有公开发表。1952年,美国蒙古学家柯立夫(F. W. Cleaves)将已经发现的《敕赐兴元阁碑》蒙古文面的四枚断片,与汉文面的一枚断片以及《至正集》所收《敕赐兴元阁碑》对照,并进行综合研究后,对蒙古语碑文进行了拉丁文转写与译注[23]。2003年秋,蒙古国和德国合作的“哈剌和林宫殿项目组”又发现了一枚新断片。2009年九月,蒙古国和日本合作的“额尔德尼召项目”小组在额尔德尼召现场调查中发现了又一枚断片[24]。
这样,到2009年,已经发现了《敕赐兴元阁碑》的9枚断片。通过已经发现的该碑断片的研究,蒙古学家们认为,自19世纪末第一次发现以来,该碑不仅成为考证当时尚未确定准确位置的哈剌和林城位置的基本史料,而且通过21世纪以来的考古学发掘调查,又成为提出兴元阁建立在窝阔台汗万安宫所在地的新观点的依据。此外,现存于万安宫附近的巨大的石龟所负载的,正是该《敕赐兴元阁碑》。该碑文对解读大蒙古国故都哈剌和林城历史极为重要,其史料学术价值,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5.《岭北省右承郎中总管收粮记》。亦称《哈剌和林Ⅱ号碑铭》,1348年立碑。关于该碑的存在,自俄国拉德洛夫探险队于1892-1899年出版其成果《古代蒙古遗址地图》,发表其拓影后才被学界所知[25]。发现地点在大蒙古国故都哈剌和林城遗址上。据报道,碑铭阳面留存22行汉文,5行蒙古文,碑铭阴面留存4行蒙古文字,有汉文,但由于磨损而几乎不能释读。主要内容为元代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录。残碑今存于蒙古国南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庙内。最早对此碑的汉文内容进行研究的是李文田撰《和林金石录》(1897),其中只著录了碑阳的汉文。碑阳的5行蒙古文和碑阴的4行蒙古文由日本国松川节于1997年较完整地解读并发表[26]。
6.《西宁王忻都神道碑》。元代蒙汉文合璧神道碑。全称为《元敕赐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亦称为《西宁王忻都碑》,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追封西宁王忻都神道碑。发现于在甘肃永昌东北武威县石碑沟, 今北京图书馆藏有该神道碑蒙汉文拓片。阳面汉文32行,阴面蒙古文54行。清代《甘肃通志》、《武威县志》和《新疆图志》均有著录。碑通高56.5㎝,宽14.9㎝,厚0.45㎝。神道碑碑额阳面楷书镌刻汉文《元敕赐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共3行12个字;阴面蒙古文碑额《yeke MongGululus-tur jarlaG-iyar Si ning ong indu-da bayiGuldaGsan bii tas buyu》,共4行15个字。神道碑原文是用汉文写的,由中书省参知政事危素撰文,中书省左承也先不花翻译成回鹘蒙古文。该神道碑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注意。1908年,法国伯希和(P. Pelliot)得到碑文拓片后曾经在他的文章里引用过[27]。1949年美国哈佛大学柯立夫教授发表了《1362年汉蒙古文忻都王碑》[28]。柯立夫对该神道碑的研究内容有:前言、绪论、汉文的英文译文,再加注释238条;蒙古文拉丁文转写、英文译文和注释267条;附有蒙汉文原文影印件。对研究该神道碑的人来说,柯立夫教授的这篇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成为不可或缺的佳作。此外,我国学者也从80年代开始研究此碑,其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亦邻真于1983年在中国民族文字研究会第二次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29]。
文中对碑文的蒙古文进行拉丁转写并加以解读和汉译,从语言学角度对碑文文字进行解读和说明。除此之外,道布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30]中有现代蒙古语译文等。神道碑的主要内容则记述元顺帝时代平章政事畏兀儿人斡栾(orun)的三代先人自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归降蒙古人。到了元代由于都瓦之乱,从西域别失八里迁到哈剌火洲,然后又迁至永昌定居之事。神道碑叙述了哈剌、阿台不花、忻都、斡栾家族几代人,尤其忻都、斡栾及其诸子对元朝的忠贞、功德以及追封忻都的详细情况。这些记载,对研究元代西部地区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从文字学角度而言,碑文对研究中世纪畏兀儿蒙古文有着特有的研究价值。
7.《应理州重修廨用碑铭记》。元代汉蒙碑铭记。至正八年(1348)立碑。发现地点在今宁夏省中卫县。碑文为汉文15行,其后加刻了两行蒙古文,约有23个词。1908年法国伯希和(P.Pelliot)获得该碑的蒙古文,但没有全文发表。1949年美国学者柯立夫(F. W. Cleves)发表了该碑文的汉文和蒙古文全文,同时也附带发表了《中卫县志》所载碑文相关内容[31]。学界有人也称该碑为《宁夏达鲁花赤甘州海牙碑》[32],其原因是该碑原文有不少处受损而缺字,成为残碑,尤其碑文汉文部分残缺不全,而据《中卫县志》著录的汉文碑文,在两行蒙古文前还有:“维大元至正八年(1348)岁次戌子六月巳未朔是日乙亥建欧阳庵书丹,奉直大夫宁夏府应理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管内劝农事甘州海牙”的记载。同时原碑蒙古文两行有:
1)Wung ji dai Wu iIraGai daruGaci Gamju qay-a yamunudunger -Un tebsiyeger
(将此词柯立夫教授读成 debisger ,似乎不确) jasa [……]
2)ulugan-a jil zhi zheng naimanon namur-un terigUn sar-a-yin arban dolugaGan- [……] 。
碑文内容为,元至正八年,由当事任奉直大夫,宁夏府应理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管内劝农事甘州海牙为重新修缮原来的已经破损不堪的旧衙门的房屋而“因建碑记事,此亦古跻千百猶存之一也,用錄而存之。” [33]
8.《八思巴字碑铭》。元代八思巴字碑铭文献中官方文献占据绝大多数,其次是印章、牌符等,文本文献极少。官方文献主要有,忽必烈皇帝牛年(1277~1289)圣旨3份、忽必烈皇帝龙年(1280~1292)圣旨、完者笃皇帝牛年(1301)圣旨、完者笃皇帝马年(1306)圣旨、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圣旨4份、完者笃皇帝南化寺圣旨2份(因碑尾残缺而无法确认立碑年代)、普颜笃皇帝马年(1318)圣旨、格坚皇帝猪年(1323)圣旨、妥欢帖睦尔皇帝猪年(1335)圣旨、妥欢帖睦尔皇帝鼠年(1336)圣旨(天玉宫圣旨碑)、妥欢帖睦尔皇帝成都圣旨、妥欢帖睦尔皇帝兔年(1351)圣旨、妥欢帖睦尔皇帝猴年(1368)圣旨、答己皇太后猴年(1320)懿旨、答己皇太后鸡年(1321)懿旨、安西王忙哥剌鼠年(1276)令旨、皇太子安西王令旨碑文末三行字、小薛大王兔年(1303)令旨、海山怀宁王蛇年(1305)令旨、帝师公哥罗古思监藏班藏卜鸡年(1321)法旨以及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碑(Jiben temUr dai ong Uge ,1277),等等。对这些石刻文献国内外学者大都进行过研究并发表了相关成果。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由照那斯图先生汇集刊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0年,1991年)。此外,八思巴字书写汉语的碑铭也有二十多种,北京大学文研所所藏24种碑拓已由罗常培、蔡美彪二先生编著增订本刊行。
9.《忽必烈皇帝牛年圣旨碑》。元代圣旨碑,今存于山西省交城县石壁山玄中寺,保存完好。石碑身高82㎜,宽64㎜,碑两面分别刻有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及汉语白话译文。碑阳面刻八思巴字蒙古语22行,阴面刻有汉语白话文译文21行。这道圣旨碑是元世祖忽必烈于牛年(1277/ 1289)正月二十五日授予玄中寺安僧录的护敕。日本学者小泽重男和德国学者弗朗克(H.Franke)分别在1962和1966年发表文章介绍过这道圣旨,并对文字内容作了考证研究。其后,1986年中国学者照那斯图发表文章,进一步研究和考订碑文。[34]
10.《哈剌和林Ⅱ号碑铭》。元代汉蒙碑铭记1348年立碑。发现地点在蒙古国旧都哈剌和林遗址。残碑今存于蒙古国南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庙内。据报道碑铭阳面留存22行汉文,5行蒙古文,碑铭阴面留存4行蒙古文字,主要内容为元代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录。此碑国内至今无人进行研究。
11.《京兆府达鲁花赤墓碑》。发现于包头市达茂旗。用汉文、蒙古文、古叙利亚文刻写的三体文“京兆府达鲁花赤墓碑”,其年款为泰定四年(1327),上刻景教“十”字纹和莲花、日月等图案。墓主人为元代汪古部人阿兀拉,他曾任元朝京兆府的达鲁花赤,即今西安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块用3种文字刻写的墓碑反映了当时内蒙古草原与内地交流的情况,对《元史》研究很有价值。
碑刻文献是地方文献的一种,而且作为地方文献首要物证,门类甚广,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极为重大。碑刻和其他文物一样,也有一个从发现发掘→辨识考证→公布信息→入藏展示→开门利用的过程。只有这样,碑刻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才会得到应有的体现。经过专家的辨识和考证,许多碑刻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得以反映和体现,价值越高越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得到更好的保护。
【作者简介】全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 编《朔方论丛》(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
来源:蒙古语
- 上一篇: 朝洛蒙 • 蒙古文书法作品欣赏
- 下一篇: 篆刻丛谈:八思巴文篆刻原石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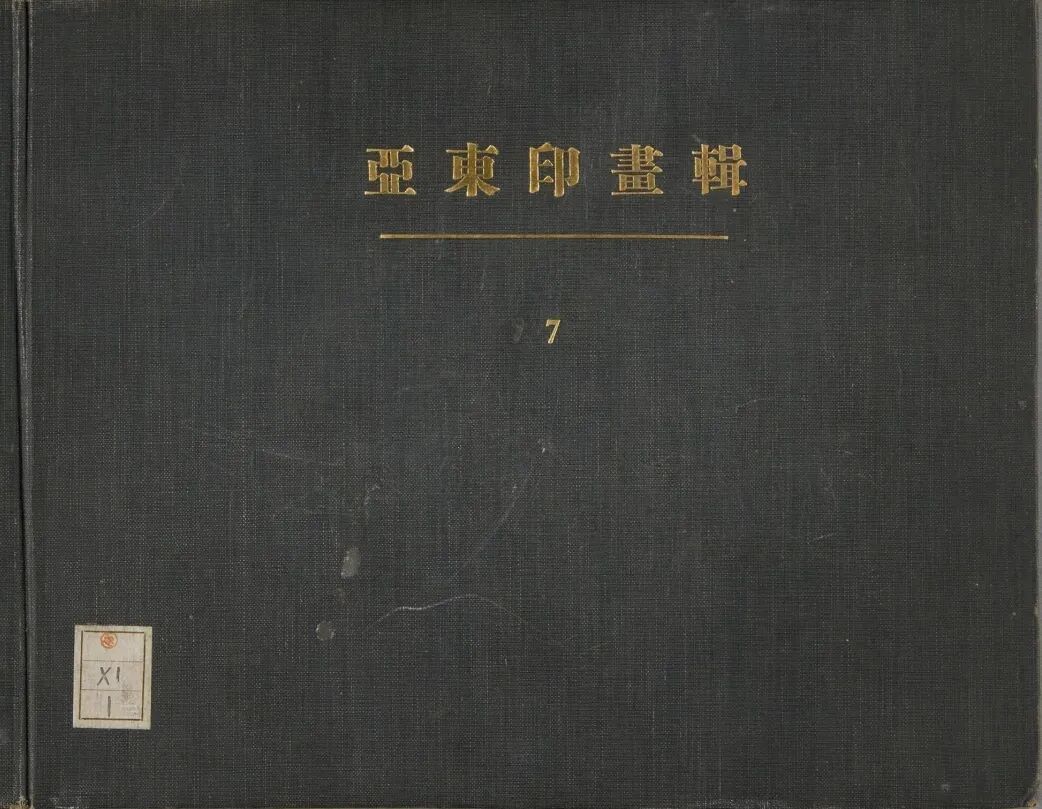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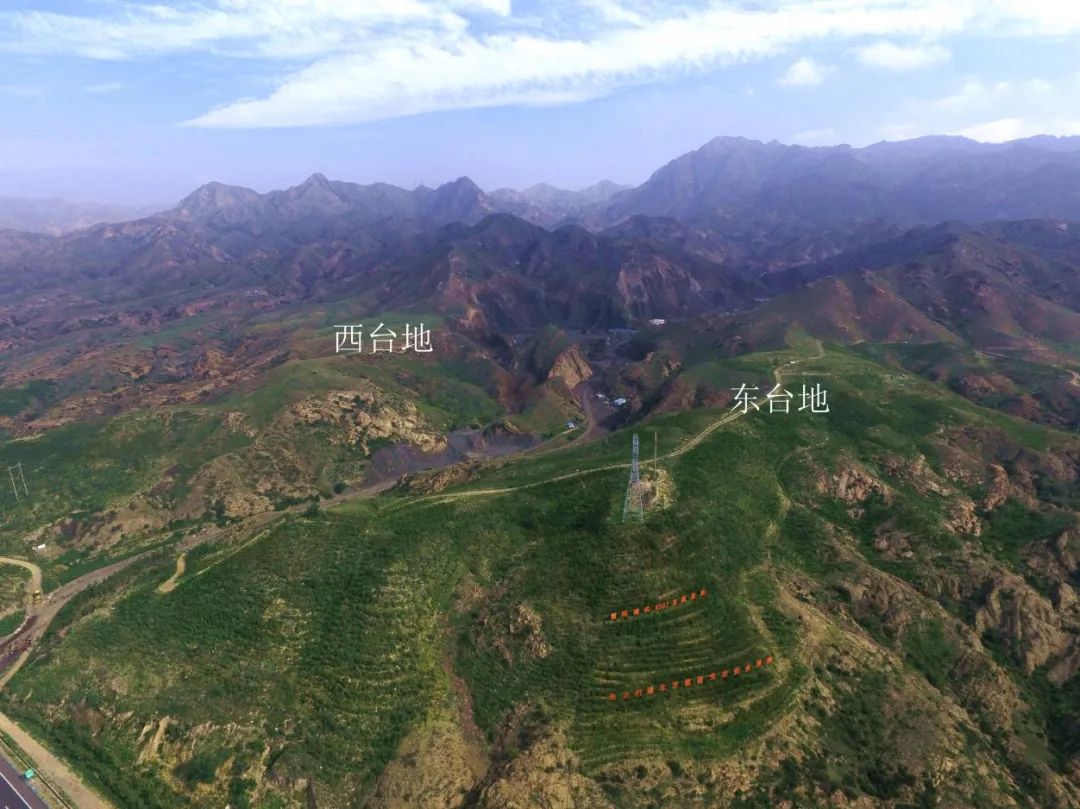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