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元代边疆史地研究-7月13日。
昨日拜读《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第一章、二章(以下简称邱文),特草就札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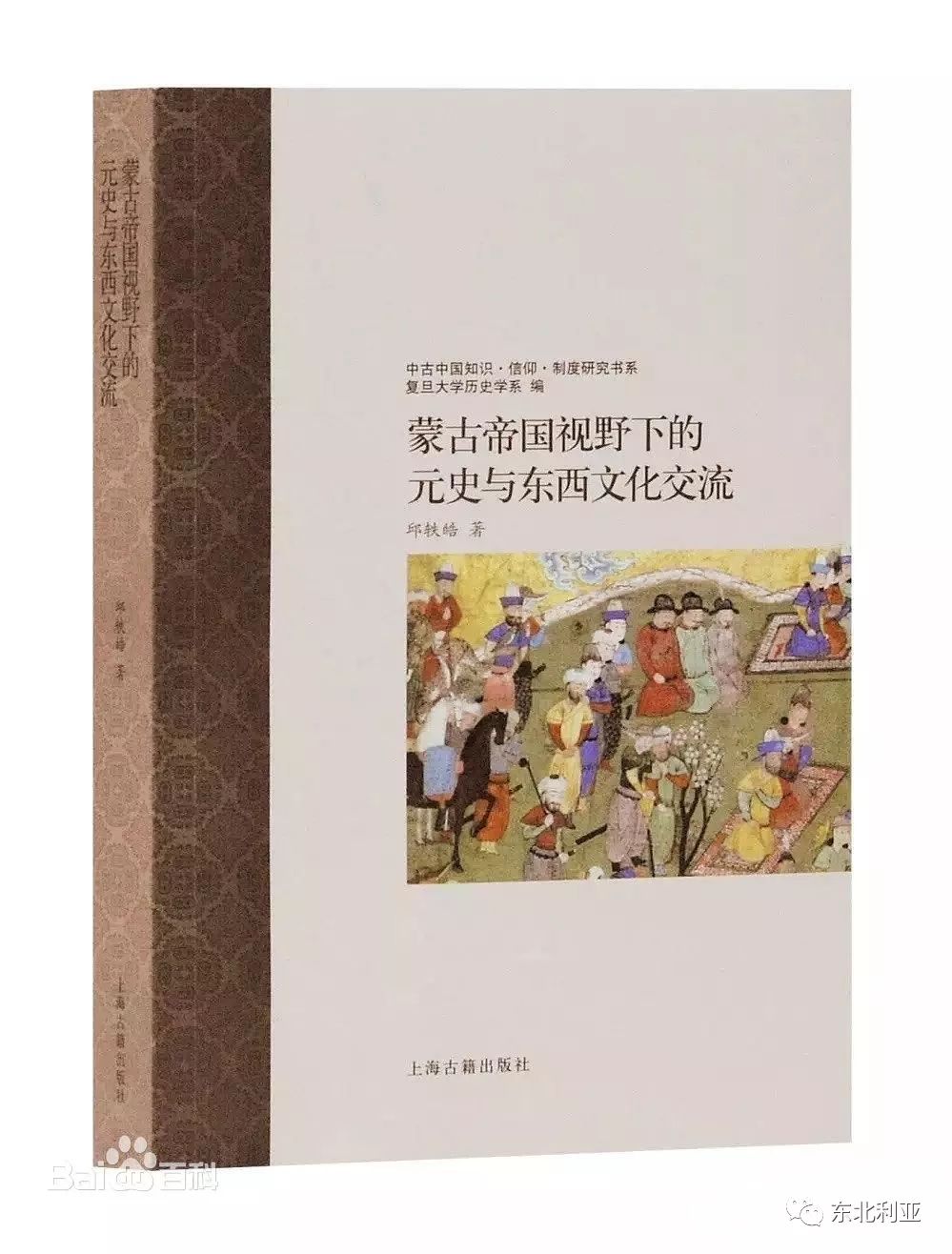
一、关于《史集》几处“蒙古斯坦”所指地域
邱文P22以为“蒙古斯坦”相当于《南村辍耕录》之“鞑靼田地”;邱文P24-25以为《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汉译本P122)所载克烈部冬、夏营地之“蒙古斯坦”;以及《史集·部族志》“乃蛮”条(P229)也儿的石河、乞儿吉思之间群山延伸至克烈部王罕居地之“蒙古斯坦”,均为泛指,指斡难、怯绿连河蒙古人土地,位于蒙古高原东部,而乃蛮部与汪古部领地不包括在内;邱文P25以为《史集·蒙哥合罕纪》(P272)“蒙古斯坦中央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虽然大致位于蒙古高原东部、斡难河中游,但“恰好处于诸蒙古语部族活动范围的中心”,故称其地位于蒙古斯坦中央。
首先,《南村辍耕录》之“鞑靼田地”大致范围并不确定位于漠北,《史集》“蒙古斯坦”广义上应相当于汉文记载“达达国土”,甚至《秘史》“也可蒙古兀鲁思”。
其次,《史集·部族志》序言所列举克烈部冬、夏营地the Onon ,the Kelüren, Tatan Balj’us, Burqan Qaldun, Kökä Na’ur, Bu’ir Na’u,Qarqab,Küyin,Ergūne,Qala’ir,the Selenga,Barqujin Tögüm, Qalajin Äalät,Öngü,依次为斡难(今鄂嫩河)、怯绿连(今克鲁伦河)、答兰巴勒渚思(答兰版朱思之野)、不儿罕合勒敦(今肯特山)、颗颗脑儿(阔阔纳浯儿)、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合儿合(合勒合、合泐合,今哈拉哈河)、回引(今伊敏河支流辉河,即《析津志》“兀失温”站东两站之“回引”站)、额儿古涅(今额尔古纳)、海剌儿(今海拉尔河)、薛灵哥(今色楞格河)、巴儿忽真脱窟木(巴儿忽真之隘)、合剌合勒只惕(合兰只之野、哈阑真沙陀)、汪古惕(界壕)。
严格而言,上述地名均非克烈部冬夏营,故上述地名并不能用以考订“蒙古斯坦”所指涉地区。因为《史集·部族志》“克烈部”条明载有克烈部王罕冬夏营地与左右翼军队禹儿惕所在。笔者在波义耳、陈得芝先生复原校订基础上,可以确定王罕冬营地六处之三处:汪吉河、鈋(é)铁钴胡兰、札剌兀忽兰;夏营地两处为达兰达葩(答兰答八思)、Güse'ür Na'ur(即距哈剌和林四日程之窝阔台秋营地KösäNa'ur、《圣武亲征录》曲笑儿泽);右翼禹儿惕两处为秃零古、盏零古两山(亦即窝阔台夏猎地),左翼禹儿惕四处仅可确定界墙南部附近阿卜只合·阔帖格儿。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前人多误将曲笑儿泽与曲薛兀儿泽(古泄兀儿纳浯、曲先脑儿)混而为一。
再次,乃蛮部也儿的石河、乞儿吉思之间群山延伸至克烈部王罕居地之“蒙古斯坦”,狭义上盖指达兰达葩、曲笑儿泽、秃零古、盏零古等哈剌和林西部以及哈剌和林北部地区。
最后,“蒙古斯坦中央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这一记载明显有误。笔者已考蒙古部在斡难河源、中游、下游至少有三处营盘:斡难河源不峏罕·哈勒敦、斡难河中游月良兀秃剌思之野、斡难河下游豁儿豁纳黑·主不儿,月良兀秃剌思之野、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分别为泰亦赤乌部、札木合老营。因豁儿豁纳黑·主不儿位于斡难河下游或最东部,故其地当为蒙古斯坦“东部”,并非“中央”。

关于《史集》“蒙古斯坦”所指涉地区,确实多为泛指,乃蛮部、汪古部(甚至乞儿吉思部)并不包括在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史集·忽必烈合罕记》一处载(1257年)塔察儿远征南家思无功而返之前一年,忽必烈在“蒙古斯坦哈剌温只敦”自己帐殿中静养;一处载(1260年)忽必烈抵达哈剌和林、在汪吉河过冬,之后遣回急使,在哈剌温只敦帐殿中停驻下来。邱文P88页误以为“蒙古斯坦哈剌温只敦”系年为蒙哥元年(1251),“哈剌温只敦”位于蒙古斯坦或蒙古高原东部、大兴安岭南端;并据“壬子岁(1252),圣主居潜邸,驻跸岭上”,而以为“岭上”即“哈剌温只敦”山麓某处营地。笔者以为《史集·忽必烈合罕记》有忽必烈帐殿之两处“哈剌温只敦”当为同一地名。
据《元史·世祖本纪》忽必烈1260年十月“戊午,车驾驻昔光(当为“黄兀”之误,指汪吉河野马川)之地”、十二月“帝至自和林,驻跸燕京近郊”,可知哈剌温只敦当位于汪吉河与燕京近郊沿途,而显然并非蒙古高原东部、大兴安岭南端。
1252年(春夏)忽必烈“驻桓、抚间”,当年夏赴曲先脑儿觐见蒙哥,因而“岭上”当位于“桓、抚间”,而可指金莲川凉陉或炭山。哈剌温只敦为蒙古语“黑山”之意,前人多以为《史集·忽必烈合罕记》之哈剌温只敦位于漠南金莲川。此说基本可从,则“蒙古斯坦哈剌温只敦”即元代上都路“炭山”、金莲川凉陉。进而言之,山后草地或爪忽都之金莲川地区,亦可称之“蒙古斯坦”。
因此,《史集》“蒙古斯坦”既可泛指克烈部、蒙古高原东部蒙古诸部(例如蔑儿乞部、弘吉剌部、塔塔儿部、乞颜部、泰亦赤乌部、札答阑部)居地,亦可指乞台地区山后草地,邱文对“蒙古斯坦哈剌温只敦”地望的考证并不可从。
狭义上“蒙古斯坦”最初可能指克烈部曲笑儿泽、秃零古、盏零古以东,额儿古涅、海剌儿以西,薛灵哥、巴儿忽真脱窟木以南,这一广袤地区并不能如邱文简单归纳为蒙古高原东部、蒙古语诸部族活动区域,因为邱文亦承认此区域中哈剌和林位于蒙古高原“中心”位置,且成吉思汗建国前后蒙古高原诸部居地与语言并非一成不变(《史集》视克烈部为突厥语部族)。

二、哈剌和林前身、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蒙古高原政治中心
邱文P61以为哈剌和林的重要地位在窝阔台即位之前“未得到充分体现”,仅处于拖雷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邱文P16以为窝阔台时期哈剌和林由诸蒙古语部族活动范围的“边缘”,一跃为蒙古帝国“中心”;P64以为窝阔台即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蒙古帝国存在新、旧两个政治中心,即哈剌和林、三河之源或斡难-怯绿连大斡耳朵。
首先,关于哈剌和林历史地位,邱文并没有厘清。
《元史·昔都儿传》“(至元)十四年,从诸王伯木儿追击折儿凹台、岳不思儿等于黑城哈剌火林之地”之“黑城”,即忽必烈1256年“冬,驻于合剌八剌合孙之地”之“合剌八剌合孙”,学者赵琦率先将“合剌八剌合孙”比定为回鹘牙帐,其说甚是。
元代史料中,黑城与哈剌火林经常相提并论,或者广义上黑城即哈剌火林。例如,元人耶律铸言
可知龙庭当即和林西北七十里之苾伽可汗宫城。苾伽可汗宫城又称斡鲁朵城、龙庭单于城、古回鹘城、回鹘单于城、卜古罕城。
回鹘牙帐为蒙古高原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即使在回鹘汗国崩溃后亦长期延续下去。例如,王延德太平兴国六年(981)出使高昌回鹘路经九族达靼居地,史载
引文之“合罗川”即元代和林川,“城”并非前人普遍以为之镇州可敦城,而当为回鹘牙帐。进而言之,合罗川回鹘牙帐其时为九族达靼政治中心。与此同时,《史集·部族志》“克烈部”条载王罕父亲忽儿札忽思—不亦鲁黑汗在斡耳朵八剌合孙有禹儿惕,“斡耳朵八剌合孙”即回鹘牙帐,此暗示王罕父亲老小营或政治中心很可能位于回鹘牙帐。
此外,史载
引文所言蒙古与西夏约为兄弟之国一事发生于1209年秋成吉思汗第三次南征西夏之役后不久,其时西夏使臣觐见成吉思汗地点为“和林”。《元史·地理志》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和宁路条载
而《元史》又载“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乙未,城和林,建万安宫”、“太宗乙未年,城和林,作万安宫”,关于成吉思汗1220年“定都”和林,窝阔台1235年“城”和林记载,笔者赞同伯希和、陈得芝先生所言成吉思汗在和林地区新设一个斡耳朵。
不过,成吉思汗在哈剌和林地区所设斡耳朵,并非始于1220年,而至迟可追溯至西夏使臣曲也怯律约1209年觐见成吉思汗于和林地区时。进而言之,窝阔台城和林,实际仅仅是将成吉思汗哈剌和林斡耳朵扩建为城池,哈剌和林的前身广义上可谓成吉思汗和林之斡耳朵,乃至斡耳朵八剌合孙、合罗川回鹘牙帐、龙庭。因此,哈剌和林为蒙古高原政治中心之历史地位,实际自回鹘时代回鹘牙帐、九族达靼时期合罗川之“城”、克烈部斡耳朵八剌合孙、成吉思汗和林斡耳朵(龙庭)一脉相承下来。

哈剌和林遗址
其次,关于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蒙古高原政治中心,邱文论述不免过于简单。
邱文承认蒙古前四汗时期属“行国”体制,那么,严格而言,前四汗时期即使哈剌和林建城之后,大蒙古国实际上亦长期没有固定的政治中心,因为其时政治中心随季节变化而迁至不同营地。简而言之,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大蒙古国政治中心可谓乃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窝阔台四季营地。其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成吉思汗最重要斡耳朵当为斡难河源(不儿罕哈勒敦)、克鲁伦河曲雕阿兰大斡耳朵、萨里川哈老徒、土兀剌河合剌屯、哈剌和林之龙庭。
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国政治中心已有所变化,即由成吉思汗称汗建国之斡难河源南迁至曲雕阿兰大斡耳朵,且哈剌和林地区之龙庭重要性亦日益凸显出来,因为曲雕阿兰、哈剌和林交通上较斡难河源更便于成吉思汗南下金国或西夏。成吉思汗后期,曲雕阿兰成为其最重要斡耳朵,其政治地位最高,而可谓大蒙古国政治中心。而斡难河源,依旧为蒙古龙兴之地。
窝阔台之所以城和林,主要因素之一是窝阔台四季营地均邻近哈剌和林,而位于哈剌和林北、西、南三个方向。窝阔台即位后较少巡幸蒙古高原东部成吉思汗斡难-怯绿连地区诸斡耳朵,未必可简单归咎于政治中心变迁。蒙古诸汗均设四大斡耳朵而有不同营地,窝阔台四季营地与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并不相同,故前四汗时期政治中心难免有所不同。邱文不明成吉思汗五处最重要斡耳朵、窝阔台四季营地位置,哈剌和林地区龙庭(邱文误以为龙庭特指曲雕阿兰)长期以来漠北诸游牧政权政治中心历史地位,故邱文第二章推论多难成立。
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蒙古高原政治中心的变迁,实际上可简单归纳为斡难河源不儿罕哈勒敦、曲雕阿兰、哈剌和林,其变迁原因有交通、蒙古诸罕斡耳朵延续性、漠北诸游牧政权传统政治中心等多种因素。窝阔台、成吉思汗实际上继承了克烈部较多营地,诸如成吉思汗继承了土兀剌河合剌屯、斡耳朵八剌合孙,窝阔台则继承了达兰达葩(夏营地)、曲笑儿泽(秋营地)、鈋铁钴胡兰(冬营地)。哈剌和林建城以后,实际上窝阔台并非定居其城,哈剌和林一定程度上仅为大蒙古国名义上的都城,其时蒙古高原真正政治中心当为窝阔台四季营地。
三、邱文第一、二章错讹举例
1、P22邱文注释二所引白玉冬先生“原本受阻于回鹘而活动于贝加尔湖东南、薛灵哥河中游以北、阔阔桑沽儿河以东地区的各支原蒙古语部落纷纷南下”,“阔阔桑沽儿河”当为“库苏古尔湖”之误。
2、P49邱文以为1227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过程中卒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此处当为“殡”于萨里川哈老徒,伯希和、王颋、薄音湖等学者与及笔者均曾论及成吉思汗卒地,成吉思汗当卒于金国“清水县”。
3、P63、P78邱文以为耶律楚材1218年经居庸、武川、云中之西、天山之北、大碛所至“行在”,即罗依果所言撒阿里客额儿行宫。耶律楚材出天山(大青山)之北所至“行在”要么为龙庭之回鹘牙帐,要么为曲雕阿兰大斡耳朵,而显然不可能为萨里川哈老徒行宫。因为没有史料可证出净州有路直通萨里川哈老徒行宫,笔者目前仅发现史料可证出净州一可西北至龙庭之回鹘牙帐,一可东北至曲雕阿兰。1218年正月成吉思汗曾南征西夏,当年耶律楚材所至“行在”很可能为龙庭之回鹘牙帐。

4、P64邱文以为陈得芝先生已经否定了白石典之将阿兀拉嘎遗址比附为彭大雅所言“大斡鲁朵”的推测,但可以认为阿兀拉嘎遗址乃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之外“另外五个斡耳朵”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陈得芝先生《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一文仅否定白石典之先生将蒙古国阿兀拉嘎遗址比附为成吉思汗陵或成吉思汗祭庙遗址,并否定彭大雅能就近观察成吉思汗“大禁地”;陈得芝、白石典之等中外学者均公认阿兀拉嘎遗址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兰遗址,且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中政治地位最高之大斡耳朵。邱文曲解陈得芝先生观点,且误将阿兀拉嘎遗址定为四大斡耳朵之外“另外五个斡耳朵”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说明其并不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位置。
5、P64邱文以为曲雕阿兰大斡耳朵汉文史料称“龙庭”,《元史》中多处“龙庭”均非泛指。狭义上龙庭,根据耶律铸记载,当指回鹘牙帐;广义上龙庭,可指蒙古前四汗任何一处斡耳朵。《元史》中“龙庭”没有一处可以确定为曲雕阿兰。
6、P65邱文以为成吉思汗黑林行宫已经为其冬营地,但事实上没有史料明载黑林行宫为成吉思汗冬营地,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并非四季营地,其四大斡耳朵位置迄今尚有争议。
7、P65邱文以为根据《秘史》,1233年夏窝阔台没有返回怯绿连河旧营地,而直接入驻合剌豁鲁麻(哈剌和林),当年冬其才返回(蒙古高原)东部的“阿鲁兀忽可吾行宫”。然而,《秘史》第273节所载窝阔台返回合剌豁鲁麻之事,邱文P20页已言当为1232年之事,其P65所言窝阔台1233年驻跸合剌豁鲁麻显然有误。此外,《元史·察罕传》载其“太宗即位,从略河南。北还清水答兰答八之地”,窝阔台1232年经官山(取道木怜驿)北返漠北,当年“九月,拖雷薨,帝还龙庭”之“龙庭”很可能当指其夏营地“清水答兰答八”。关于窝阔台1233年冬所至“阿鲁兀忽可吾行宫”,位置不详,未必位于蒙古高原东部,阿鲁兀忽可吾即阿剌黑忽客儿、阿剌黑忽客里,突厥语“花牛”之意。
8、P65邱文以为1234年窝阔台在夏营地“达兰达葩”和“八里里答阑答八思之地”两次召开宗亲会议,商议征宋。然而,“达兰达葩”即“答阑答八思之地”,“八里里”不详,当年达兰达葩当仅召开一次征宋会议。
9、P67邱文以为1235年后翁金河上游野马川取代黑林行宫成为新的冬营地,1237年“冬十月,猎于野马川。幸龙庭,遂至行宫”乃窝阔台其时唯一东幸东部驻牧地的活动,并将“龙庭”均比定为曲雕阿兰。事实上野马川冬营地遗址白石典之先生已有论及,其地并非位于翁金河上游,而当为中游;1237年“冬十月,猎于野马川。幸龙庭,遂至行宫”之“龙庭”、“行宫”不排除指野马川冬营地。
10、P68邱文以为《史集》所载1245年秋选立贵由为汗之“阔阔纳兀儿”,当位于“答兰答八思”范围内,乃窝阔台时期秋营地,其对波义耳、陈得芝先生关于阔阔纳兀儿、曲先恼儿争议不知如何堪同,而以为目前似未有完美的解释。邱文对颗颗脑儿、曲先脑儿、曲笑儿泽三处斡耳朵位置皆不明了。笔者早已考订阔阔纳兀儿(颗颗脑儿)为铁木真逃离泰赤乌部后所设首个营盘,当即美国陆军制图局所编制蒙古地图Öndör Haan分幅之Delger Hanuy Nuur(E108°90´,N47°52´)。窝阔台秋营地当为曲笑儿泽,位于达兰达葩地区。曲先恼儿即曲薛兀儿泽、古泄兀儿纳浯,位于怯绿连河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兰附近,亦即民国《百万分一中国舆图》“乌得”一图克鲁伦河南岸之“哈喇湖”。

克鲁伦河
11、P68邱文以为1246年贵由在哈剌和林地区的汪吉宿灭秃里即位,“汪吉宿灭秃里”盖即窝阔台野马川冬营地,至少其地显然并非位于哈剌和林地区。
12、P69邱文据《史集》所载十一岁忽必烈与九岁旭烈兀在乃蛮边境爱蛮-豁亦(aīmār-hūī)狩猎,其地邻近叶迷立-忽真,且邻近叶迷立-忽真(Imil-Qojin)附近、亦列河(the Ili River,今伊犁河)彼岸、距畏兀儿地区不远,而以为忽必烈、旭烈兀兄弟为幼童,爱蛮-豁亦当为其父亲拖雷营帐,拖雷家族在窝阔台潜邸分地叶密立、霍博附近有禹儿惕。然而,《史集》实际载载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返回自己斡耳朵时,忽必烈与旭烈兀出来迎接成吉思汗,二人适在叶迷立-忽真附近、亦列河彼岸、邻近畏兀儿地区的乃蛮边境之爱蛮-豁亦(aīmār-hūī)分别猎杀一只兔子与山羊,成吉思汗根据小孩第一次狩猎需在大拇指拭油的习俗亲自替二人拭指。之后,他们从那里出发,驻扎在不合速只忽,设置金帐,举行聚会,其地土质甚轻,成吉思汗命每人搬取石头投掷到其营地上。由此可见,爱蛮-豁亦(aīmār-hūī)并非拖雷禹儿惕或营帐,而当为成吉思汗西征返程驻跸之斡耳朵。
13、P71邱文据《元史》1251年夏“复大会于阔帖兀阿阑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于斡难河”,而以为蒙哥1251年即位于斡难河源曲雕阿兰。然而,“斡难河源”当为克鲁伦河之误,曲雕阿兰与斡难河源相距甚遥。
14、P71邱文据《史集》以为蒙哥1251年冬在汪吉河驻冬,次年夏《元史》始第一次明载其“驻跸和林”。然而《史集》所载蒙哥1251年驻冬汪吉河很可能为1252年之事,因为《元史》明载1252年十月驻“月帖古忽兰”之汪吉河野马川地区;且蒙哥1251年于曲雕阿兰即位,其自曲雕阿兰要赴旺吉河驻冬,史载交通线只有自曲雕阿兰经萨里川哈老徒、黑林行宫、哈剌和林至汪吉河。换言之,蒙哥如果1251年即位当为便自曲雕阿兰赴汪吉河驻冬,其当年便已驻跸哈剌和林。
15、P73邱文以为1252年八月徐世隆、姚枢等觐见蒙哥之“行宫”,当为萨里川哈老徒行宫。陈得芝、马晓林等学者早已考徐世隆、姚枢等觐见蒙哥之“行宫”为曲雕阿兰,或曲先恼儿,或驴驹河(克鲁伦河)。
16、P73邱文以为日月山为“哈剌温山”,“在和林之北”恐非确论,或出于汉人想象之辞,而以为日月山位于不儿罕山脉中距颗颗脑儿、军脑儿甚近的某处。日月山为“哈剌温山”,“在和林之北”,此记载准确可靠。关于日月山位置,陈得芝、宝音德力根、赵琦、马晓林等学者与笔者均有论及,其地即斡难河源不儿罕山,距颗颗脑儿、军脑儿甚遥,且学者马晓林已经梳理1252年蒙哥日月山祭天详细过程。
17、P75邱文表一 史料所见前四汗时期驻营地,标注1224年秋成吉思汗自花剌子模返回黑林行宫。然而,1224当为1225年之误,《秘史》第264节明载成吉思汗鸡年(1225)返回黑林行宫。
18、P75邱文标注1225年夏,成吉思汗驻跸“布哈绰克察”,“布哈绰克察”由于清人忘改而无法复原。笔者早已考布哈绰克察即《史集》之Buqa-sučiqu、成吉思汗碑(移相哥碑)之Buqa-(s)učiqAi,其地正为《史集》所载忽必烈与旭烈兀狩猎后随成吉思汗至“不合速只忽”聚会之地。
19、P75邱文标注1232年夏窝阔台驻跸“阿剌合的思”,但《元史》明载当年夏窝阔台避暑“官山”或九十九泉,阿剌合的思(杂色山岭)乃拖雷随窝阔台自官山北返漠北沿途去世之地,并非窝阔台驻夏营地。
20、P78邱文标注1218年耶律留哥觐见成吉思汗之“按坦孛都罕”,屠寄考证为“驴驹行宫”。伯希和、蔡美彪先生均论及按坦孛都罕词义、位置,按坦孛都罕为“金糕驼”之意,指金莲川凉陉,笔者已考其具体指今太仆寺旗骆驼山。按坦孛都罕很可能得名于山上遍布黄色金莲花,而山形似骆驼。

金莲花
满洲语aisin xu ilha
蒙古语 altanghvwa ceceg、altan batma
21、P79邱文标注1236年邹伸之使团觐见窝阔台于怯绿连大斡耳朵。然而,王国维先生已考邹伸之两次出使蒙古,《黑鞑事略》所载彭大雅、徐霆出使蒙古路线虽然不同,但二人觐见窝阔台之地很可能均为窝阔台夏营地达兰达葩。
22、P81邱文标注李志常1251年冬、1255年七月分别觐见蒙哥于汪吉河、哈剌和林。但李志常1251年冬所至“阙下”未必位于汪吉河,当年冬蒙哥亦可能驻曲雕阿兰;史载李志常乙卯(1255)七月觐见蒙哥于“行宫”,《元史》载当年夏蒙哥驻夏达兰达葩地区月儿灭怯土,邱文所标注李志常1255年觐见蒙哥于哈剌和林与蒙哥驻夏月儿灭怯土之事自相矛盾。此外,邱文注释②所标注“秋七月见上于行宫”实际为乙卯年之事,而当移入1255年条下。
23、P81邱文既标注1255年那摩大师、少林长老等人觐见蒙哥于哈剌和林,附录又注明“以七月十六日,觐见帝于鹘林城南之昔剌行宫”,前后自相矛盾,且那摩大师、少林长老觐见蒙哥之事为丙辰(1256),并非1255年。此外,邱文1256年条附录注明噶玛拔希、鲁木王子阿老丁抵达“昔剌斡耳朵”,亦可证那摩大师、少林长老等人1256年觐见蒙哥于昔剌行宫记载准确无误。但需要指出的是,邱文标注噶玛拔希、鲁木王子阿老丁朝觐地点为“哈剌和林”,与昔剌斡耳朵自相矛盾。昔剌行宫即剌斡耳朵,即“金帐”之意,亦即窝阔台夏营地月儿灭怯土,位于达兰达葩地区。因此,昔剌行宫实际位于鹘林城“西”或西南。
小结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第一章《“蒙古斯坦”的形成与草原领地的分封》、第二章《草原政治中心的西移与哈剌和林之成立》,源自该书作者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蒙古帝国的权力结构(13~14世纪)——汉文、波斯文史料之对读与研究》第一、二章,此两章内容曾以《哈剌和林成立史考》刊于《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总体而言,此两章内容基本一直无多大变化或修订。《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收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第三辑,其“书系缘起”中,余先生2011年12月言此套丛书乃追求学术沃土而并非“党同伐异的山头”之“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在学术出版过度繁荣的当下,推出的数年打磨而写定的心力交萃之博士论文佳作(第一辑)、研究班成立后历次往复匡谬正俗之结晶(第二辑)。第三辑学术定位,不详。笔者昨天走马观花选读了《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第一章、二章内容,偶然发现了上述问题。作为2011年已经定稿之博士论文章节,距今已七八年,却没有“数年打磨”、“往复匡谬”而基本原文不动收入论文集或专著中,此不免既对读者不负责任,亦不尊重近年来学界新出之相关研究成果。按照学术惯例,博士论文答辩后出版时,一般多适当加以修订完善。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作者以为《史集》乃研究蒙古帝国早期历史最重要史料,强调使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多语种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尤其是汉文、波斯文史料对读、比较。汉文、波斯文史料对读的方法值得提倡,不过研治元史首先应学习的民族语言可能应该是蒙古语、突厥语,相关汉文史料的比较分析,亦应重视。《史集》对蒙古早期历史事件的记载,系年、地点经常错误百出,《史集》记载很多情况下不如《秘史》、《亲征录》、《元史》更准确可靠。上述两章虽然史料十分翔实,但内容涉及蒙古诸部营地、成吉思汗诸斡耳朵、窝阔台四季营地一系列蒙古高原史地,而作者基本不明相关历史地理,相关地名位置多引据前人之说,不免疏于考订。
笔者对民族语言半窍不通,一日草就此札记,唯一目的是希冀学界能多出一点诸如伯希和、波义耳、陈得芝先生民族语言与史地紧密结合、考证精辟之作。(读书札记草稿,请勿引据,多谢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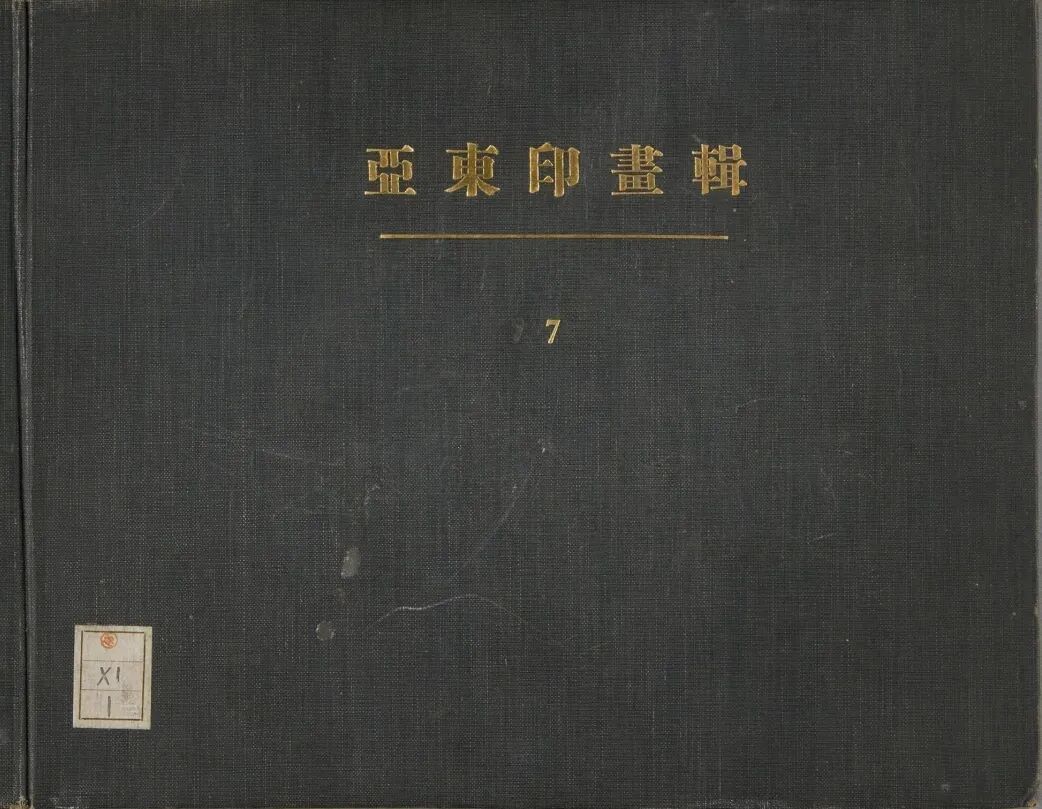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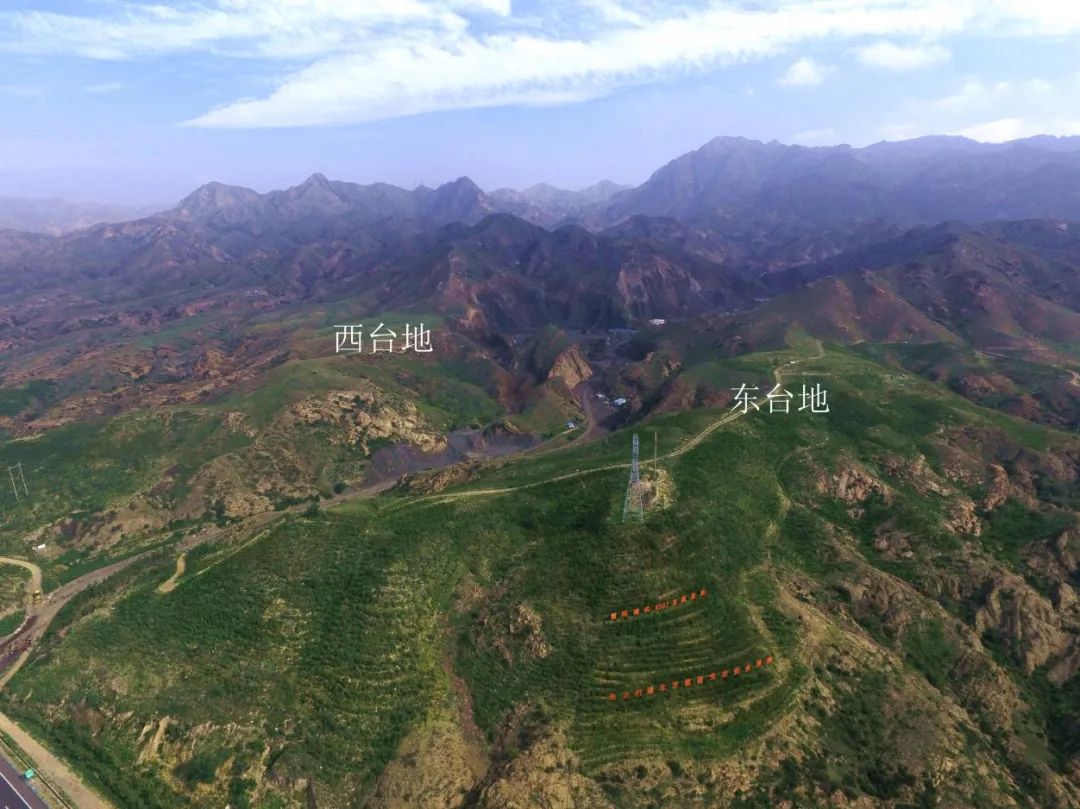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