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利,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以及天下边疆。
二、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试图建立中心的实践
如前文所述,在俺答汗时期,蒙古诸部就已开始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1603年,转世于俺答汗家族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在蒙古贵族的护送下到达拉萨,但是他在1616年突然在哲蚌寺去世,年仅28岁,这更加引起了西藏局势的动荡。西藏藏巴汗抓住这个机会,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在西藏确立了统治地位,格鲁派的势力岌岌可危。
此时的中国各地,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634年秋,林丹汗亡故后,1634年12月14日,嘛哈噶喇佛像为后金所得,
“蒙古大元国世祖呼(忽)必烈汗时,有帕克斯巴(即八思巴)喇嘛用金铸嘛哈噶喇佛像,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萨斯遐地方。又有沙尔巴胡图克图喇嘛复移于大元国裔蒙古察哈尔国祀之。奉天承运满洲国天聪汗威德遐敷,征服察哈尔国,旌旗西指,察哈尔汗不战自逃,其部众尽来归。于是,墨尔根喇嘛载嘛哈噶喇佛像来归。天聪汗遣必礼克图囊苏喇嘛往迎之。天聪八年甲戌年季冬月十五日丁酉,必礼克图囊苏喇嘛携墨尔根喇嘛至盛京城。”

满洲文老档中对此事的记载:
《满洲文老档·博格达彻辰汗》汉文译制版30

“嘛哈噶喇”又译写为“玛哈噶拉”,意为“大黑天”,这对于信仰藏传佛教后的蒙古人来说,是与传国玉玺一样重要的象征之物,即传国玉玺是“政教二道”中“政”的象征,嘛哈噶喇佛像是“教”的象征,二者的转移就象征着“政教二道”的转移。
虽然皇太极对此或许没有后世顺治帝、康熙帝等人有高度的认识,但他还是决定修建寺庙,并向朝鲜国王致信索要修建寺庙所用的颜料,该庙就是实胜寺。1635年2月,林丹汗之子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率部投降后金,传国玉玺也归皇太极所有。由此,漠南蒙古“政教二道”的象征物都归后金所有。

辽宁沈阳实胜寺
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台吉会于盛京,共向皇太极上尊号为“博格达·彻辰汗”,这不但标志着漠南蒙古正式归附于后金,也标志着皇太极成为蒙古大汗。皇太极正是在蒙古势力的支持下,此后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清政权借助于蒙古的力量,于1644年入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满蒙的政治军事联盟似乎超越了蒙藏在宗教上的意识形态联盟,这两个联盟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但实际上,清朝利用自己的优势,把佛教的中心由蒙古转移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清帝的称号有“曼珠师利大皇帝”、“文殊菩萨”、“文殊皇帝”、“转轮王大皇帝”等等,这实际上是以满洲为中心的表现。
但藏传佛教的转世理论有很大的弹性,故使蒙古诸部领袖纷纷争夺或建构自己是忽必烈转世的地位。而在清朝入关前后,远处西北的卫拉特蒙古各部亦试图主导藏传佛教格鲁派,亦试图使得“政教二道”的中心转移到自己的部落来,以号令诸部,与清朝抗衡,这其中最有实力的部落就是和硕特部和准噶尔部以及土尔扈特部,因为准噶尔部与西藏的关系笔者已经有长文发表,故本节只讨论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构建“政教二道”中心的努力。

河北承德外八庙
1、和硕特部与西藏格鲁派的关系
17世纪中叶左右,卫拉特蒙古和青海蒙古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因为游牧经济的分裂性,卫拉特蒙古内部也纷争不断,和硕特部固始汗率军向外进行扩张和迁徙。1637年初,固始汗率军在青海湖击败了青海的却图汗,很快就占领了青海的主要地区。而固始汗之所以能够胜利,也是与格鲁派信徒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原来却图汗与西藏藏传佛教噶举派联系密切,从而在噶举派的斡旋下,试图与西藏仇视格鲁派的藏巴汗联盟,以消灭格鲁派,这引起了包括蒙古诸部在内的格鲁派信徒的反抗,而固始汗以护持格鲁派为名,进军青海,自然就引起了各地格鲁派信徒的大力支持,从而战胜了却图汗。
固始汗驻牧于青海后,发展经济,积聚力量。这个时候,康区的白利土司试图联合藏巴汗,以打压格鲁派,于是他加紧四处活动。1639年,正当五世达赖喇嘛举行施食法事时,白利土司给藏巴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
“在神山上已插置神幡。由于甘丹颇章没有保证蒙古人不进攻康区,明年我将带兵到卫藏。那座称为觉卧仁波且的铜像是招致战争的根源,应当扔到河里去。把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破坏以后,应在其废墟上各垒筑起一座灵塔。藏巴汗应当与我亲善起来,一同供养卫藏和康区的佛教徒和苯教信徒。”
但是这封信在途中被格鲁派僧人截获,后交给了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知道后很生气,他说:“这个白利土司十恶不赦,他是应进行诛灭的主要对象”。由此,固始汗以白利土司勾结藏巴汗为由,派兵剿灭了白利土司,此后声威大震。
固始汗到达康区后,1641年拉萨祈愿大法会期间,就派“噶居格年顿珠和大王妃来(拉萨向达赖喇嘛)通报情况,并派色钦乌巴锡等大批人员前来请安问候”,这个时候西藏关于蒙古军队的传言有很多,有人说固始汗返回青海了,有人说他领兵临近卫藏,达赖喇嘛也和协敖·索南绕丹商讨应对之策,索南绕丹主张依靠固始汗,
“如果我们不依靠固始汗的恩德从藏巴汗的法度下解放出来,以后就再不可能有得到解脱的机会,因此,在派出信使格年顿珠的时候,我就提出了固始汗应当用兵后藏的请求。”
但是达赖喇嘛主张还是把固始汗劝说回青海去,两人争执不下,后来以占卜的方式解决问题。占卜的结果是固始汗进兵西藏暂时不失为善策,但是长远的结果不好。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中和了达赖喇嘛和索南绕丹意见的占卜结果,后来的结果实际上是按照索南绕丹的意思在进行。
此后,固始汗准备往西藏进军,他一面为避免不测,给达赖喇嘛写信说,班禅大师在后藏会有危险,以大王妃上了年纪不能去后藏为由,让班禅到前藏来;一方面又佯装已退回青海,以麻痹藏巴汗,而后趁虚进入西藏达木地方。
当藏巴汗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让正赴拉萨途中的班禅暂时“滞留在喀日丁地方”,而索南绕丹则立即赶赴蒙古军队中去见固始汗,他安排达东乃引领固始汗军队进攻藏巴汗,自己则与固始汗的两位王妃一起来拉萨。在格鲁派的支持下,固始汗的军队进展顺利,到1642年3月,“西藏所有木门人家都归于持教法王(固始汗)治下”。然后,固始汗给达赖喇嘛捎来口信,让达赖喇嘛从拉萨哲蚌寺去后藏,固始汗则亲自到德庆地方迎接,并
“将八思巴大师的曼朵法铃和一只称为‘索布贝杰’的绿宝石碗赠送给我(指五世达赖喇嘛)。据说这两件奇特的珍宝曾经在西藏十三万户长的手中传来传去,后来从内邬栋孜传到仁蚌巴的手中。”
固始汗将八思巴用过的宝物赠送给达赖喇嘛是有非常的用意的。八思巴(1235-1280),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1247年在其幼年时随其伯父萨迦至凉州会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长大后,得到了忽必烈的喜爱。1260年忽必烈尊其为国师,赐玉印。1264年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1269年以其所制蒙古新字颁行全国,是为“八思巴字”。1270年升号为“帝师”,进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1276年返藏,聚卫藏徒众七万人,举行曲弥法会,自认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同时任命“本钦”统领西藏十三万户,僧俗并用,军民兼摄,是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

西藏拉萨哲蚌寺
可以说,在五世达赖之前西藏的历史上,八思巴在政教两方面的地位无有出其右者,所以固始汗将八思巴所用过的宝物赠给五世达赖喇嘛,自有一种权力交接的意味。尤其是达赖喇嘛到达日喀则之后的首次聚会所举行的仪式更有如此的意味,据五世达赖描述当日的聚会是这样的:
“我到达日喀则后的首次聚会是在桑珠孜的大厅中举行的,难以数计的蒙藏人士聚集在那里,当大家就座之时,按忽必烈皇帝向八思巴大师奉献三次大布施之例,固始汗向我奉献了阿阇世王的所依止的圣物即供奉在江喀孜的那件世尊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八思巴曾经亲自交给益希巴的有名的垂罗宝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件宝饰是莲花生的明妃之一空行母益布措杰的护心镜,是掘藏师曲却旺秋活佛发掘出来的)、以仁蚌巴阿旺久典旺秋吩咐制作的那顶精美的帐幔为主的内供物品,喇嘛身像、铜像以及汉地所造的许多供品。然后,汗王宣布他将包括日喀则在内的西藏十三万户全部献给我。”
按照“忽必烈皇帝向八思巴大师奉献三次大布施之例”,固始汗向达赖喇嘛布施了好多珍宝,而最珍贵的当然是西藏十三万户。这里面的寓意是把固始汗当成了忽必烈的继承人,把五世达赖喇嘛当成是八思巴大师的继承人,由此和硕特部蒙古人和藏传佛教之间有了前后相继的勾连,这与上文所说的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分别是忽必烈和八思巴的转世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说明,政教二道的中心转移到了和硕特部。
据说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的三次大布施是:
第一次是以全藏十三万户作为贡献;
第二次是以全藏三区作为供礼;
第三次是以阿阇世所分得舍利的“舍利份子”作为供养。
这三次布施中,前两次布施仅仅是经济上的布施,最后一次则是皈依了佛教,以佛教圣物——舍利作为供养,则是皈依佛教的表现,就不只是要布施,更有传播佛教的责任了。如果把固始汗当作忽必烈的继承人的话,那么达赖喇嘛也希望固始汗这样做,当然这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理想,但是至少他的理想实现了一部分,固始汗果然布施给了他西藏十三万户。
但是当时在西藏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万户制度,固始汗以“十三万户”的名义布施给达赖喇嘛,实际上是强化他作为忽必烈的继承人、五世达赖是八思巴继承人的印象。
所以,这个仪式与其说是布施之仪式,不如说是建立蒙藏联合政权之仪式,以忽必烈和八思巴的继承人的名义,固始汗取得了在西藏的世俗领导地位,而五世达赖喇嘛取得了在宗教上的领导地位。
实际上,五世达赖喇嘛早就有当宗教领袖的愿望,在他的自述中写道:
“在西藏这块土地上,如果有一个领袖,时局才会安定,萨迦、噶举、宁玛等其他教派四分五裂的局面才可能有所改观。”
固始汗在当时已经控制了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和硕特汗廷,对于他来说,提高达赖喇嘛的地位,以号令蒙古诸部是个比较明智的选择,所以,他仅仅布施了“西藏十三万户”,并未把自己控制的全部地区都布施给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在自述中,强调忽必烈向八思巴的三次大布施,则不仅仅是有蒙古人和西藏高僧政、教两方面继承的意味,还有试图让固始汗布施更多的意味。无论如何,这次仪式等于宣告了蒙藏联合政权的成立,这也就是被后世所称的“甘丹颇章政权”。

反映内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绘画作品
2、蒙古土尔扈特部与西藏的关系
因为蒙古和硕特部、准噶尔部与西藏接壤,所以在清代初期对西藏影响也最大,而其他几个蒙古地区,如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以及喀尔喀蒙古等,因为距离西藏较远,如果要进行武力等干预,中间必须得经过青海蒙古或者准噶尔,所以他们与西藏的联系主要是延请高僧、修建寺庙以及入藏熬茶布施。
土尔扈特蒙古或许是卫拉特诸部中最先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部,在1628-1632年,因为牧场狭窄以及内讧等多种原因,土尔扈特部从塔尔巴哈台辗转迁至伏尔加河流域,若到1771年渥巴锡率部东归,则共经历了140余年、八代汗王,这八位汗王是:和鄂尔勒克、书库尔岱青、朋楚克、阿玉奇、策凌敦多布、敦多布旺布、敦多布达什、渥巴锡。在历代领袖的倡导下,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尔扈特部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他们修建寺庙,延请高僧,并入藏熬茶。他们所建的寺庙有:
表一、蒙古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流域所建寺庙
寺庙名称 | 建造者 | 备注 |
昂加恩库热 | 昂家恩一世喇嘛 | 第一所新建寺院 |
巴克希恩库热 | 额木其昂海腾 | 阿玉奇汗资助 |
喇嘛库热 | 沙克尔喇嘛 | 阿玉奇汗资助 |
共芒库理雅 | 果芒本鲁敦珠嘉措 | |
宗喀巴库理雅 | 策克尔察恩德克 | |
却进库理雅 | 护法神寺院 | |
喇嘛却进库理雅 | ||
呼图克图格根庙 | 卫拉特籍咱雅班智达僧众 | |
哈布青达尔库理雅 | ||
却藏库热 |
这些寺庙规模宏大,喇嘛人数也很可观,“在伏尔加河两岸喇嘛庙当喇嘛的有1万多人,最多时达到2万多人。”如此多的喇嘛在促进当地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土尔扈特部的负担。
德国学者帕拉斯曾经亲眼见过土尔扈特部的一些寺庙,他说:
“固定的庙宇一般都建造在地势优雅的风水宝地,上等僧侣和部落首领通常都将自己的住宅建在寺庙附近的地方。他们在每月例行的诵经日聚会于庙宇,节庆日也多在此欢度。位卑的僧侣则多居住在自己的帐篷里,帐多搭在他们自己围造而成的小庄园之内,底下垫上厚厚的木块防潮。——有的僧侣甚至将住宅建在庙宇旁边,这样可使畜群一年四季都有好草使用,生活在中国的蒙古王公以及宗教领袖的牙帐也演变成了这种不可徙动的固定住宅。”
从帕拉斯的观察可以看出,因为藏传佛教的关系,改变了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由原来的流动性的生活方式变成了固定性的生活方式。

满洲国时期帐篷中聆听喇嘛教诲的信徒们
土尔扈特部远离西藏有万里之遥,但是他们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多次赴藏熬茶。下面根据《五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进行一个统计,详见下表。
表二、土尔扈特部入藏熬茶情况
时间 | 人员 | 布施内容 | 备注 | 出处页码 |
1643年 | 土尔扈特岱青 | 给五世达赖喇嘛赠送了一百匹带鞍子的马,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后把达赖喇嘛又请到大昭寺,呈献了成千上万的重要礼品。 | 土尔扈特岱青还夸口说如果与主巴派活佛白玛旺波相会,也会奉献这样的厚礼(即一百匹带鞍子的马——笔者注)。 | (上)第153页 |
1655年 | 书库尔岱青之弟衮布伊勒丁 | 五世达赖向其传授了长寿灌顶法 | (上)第291页 | |
1674年十二月初一日 | 土尔扈特的代表喜饶格隆 | 向达赖喇嘛赠送了很多礼品 | (下)第162页 | |
1675年三月十五日 | 翁则曲杰 | 连同土尔扈特首领阿玉锡捎给达赖喇嘛的礼品,翁则曲杰向达赖喇嘛赠送了黄金350两、白银700两、茶叶、绸缎、皮张、布匹等大批物品,并布施会供物品 | (下)第175-176页 | |
四月初四日 | 土尔扈特代表 | 达赖喇嘛向包括土尔扈特部在内一些人士赠送了礼品 | (下)第181页 | |
四月十二日 | 土尔扈特巴图尔的代表额尔克格隆 | 达赖喇嘛向其传授了《修法大海》中所说的“十三尊空行随许法” | (下)第181页 | |
1681年7月11日 | 土尔扈特阿玉锡的信使 | 向五世达赖赠送了茶叶、银子、绸缎、马匹等礼品 | (下)第441页 | |
8月初九日 | 信使 | 五世达赖设茶宴招待了信使等人 | (下)第443页 |
除了上述使团外,实际上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还派遣了多次使团,尤其是1698年以其侄阿拉布珠尔母子为首的使团最为有名,这是因为该使团从西藏返回伏尔加河游牧地时,必须经过准噶尔地界,但是由于土尔扈特与准噶尔当时关系恶化,无法回去,所以“遣使至京师,请内属”,清朝于1704年封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于党色尔腾。
土尔扈特部不但进藏熬茶布施,还希望达赖喇嘛对其领袖进行册封,并举行盛大的授号仪式。1735年,土尔扈特部首领策凌敦多布就举行了这样盛大的授号仪式,我们看看帕拉斯的记载:
“仪式定于1735年9月1日举行⋯⋯帐内置有一个特别高的座位或称御座,供汗用;御座右边的一张椅子稍矮,供当时土尔扈特部最高僧侣书库尔喇嘛坐用⋯⋯
身着豪华服饰的汗端坐在帐中为他设立的御座上,静等书库尔喇嘛的到来。书库尔喇嘛诵经已毕,庄严地从他的住所走出,步向汗帐。聚集在佛庙内的僧侣出来列队奏乐迎接书库尔喇嘛,并陪同他走到汗帐门前。这时,僧侣们转身往回走,而喇嘛则直接趋步上前坐在御座旁边的椅子上。紧接着,受汗派遣到西藏的巴图尔鄂木布——他已得名巴图尔格隆并入僧籍——率领一大批随从僧侣骑马来到汗帐。巴图尔格隆本人脱离队伍,走到前面,将达赖喇嘛赐给汗的那份神圣令旨放在自己的头上。两位僧生一人手持一束点燃了的香烛,一人手捧一只底下烧着煤的水壶,壶内煮有西藏产的块根;两人一起敬奉着令旨款步向前。巴图尔格隆身后紧跟着另一位僧侣,手执佛像和佛祖遗物。在他们的后面,僧侣们列队牵来一匹供汗用的御马,备有达赖喇嘛赠赐的御鞍,其他人拿着圣衣、圣帽、圣带(上面挂有一把匕首和一把小刀)以及供汗用的马刀、枪支、箭囊和弓矢。队伍最后面是两面大纛,一面是达赖喇嘛送给汗的,是汗位的象征,另一面是达赖喇嘛的活佛曲钦送给汗的使节的。这一支队伍与前面的喇嘛一样,受到僧侣们的迎接并被陪同着到汗帐前,一路高奏乐曲,吟诵经文。
及至帐前,巴图尔格隆及其随从滚鞍下马,和手捧着圣衣的人一起进入帐内⋯⋯书库尔喇嘛从椅子上站起来,先从巴图尔格隆头上拿下达赖喇嘛的令旨,将它放在汗的头上,再接过汗用的圣衣,这时汗也站起身来,书库尔喇嘛给汗穿上圣衣,再次入座。书库尔喇嘛用唐古特语朗诵达赖喇嘛的令旨,先是在汗帐内,后又到外面向众人宣读。令旨的内容如下:
英名神圣幸福的沙索本色岱青汗(此乃达赖喇嘛赐给汗的新名),我们祝福你,祝愿你和你的臣民能再过上过去的美好时光,愿你的实力不断扩张,愿你成为英明无比的执政王,像高贵的鲜花一样闪闪发光,愿你和其他人都能增强对神圣宗教的信仰!——你出于对我们的无比热爱,遣使来到西藏,你带来了我们的祝愿。你送给我们的礼物,一块上等的哈达和地毯,两个用珍珠制成的玫瑰花环,80枚金币,两匹布料等等,我们都已以神圣的宗喀巴和黄教高级僧侣的名义领受了。我们祝愿你的人民和全体生灵都能恢复内部和外部的和平,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祝愿你笃信宗教,乐善好施,爱民如子。令尊大人是本教的保护者,是我们坚定的崇拜者,他已仙逝。全体土尔扈特王公以及其它部落的王公必须以令尊大人为榜样,父亲似地或祖父似地衷心爱戴他们的臣民,接受乐善好施的教义,尽心尽力地传播和增强黄帽的真谛;要乐意宽宥下人的过失,帮助他们步入正道;要努力牢记规定的经文,虔诚地摆设心灵和信仰之物,心中永远不忘佛、法、僧三宝。如斯,我们会永远爱戴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给你和你的人民提供精神帮助。兹送给你桑嘉一条,本人画像一幅,普度众生者的真舍利、释迦牟尼佛祖的舍利各一块⋯⋯
书库尔喇嘛当着众人宣读完这封令旨后,站在四周的贵族以及有权前来参加仪式的普通人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书库尔喇嘛面前,书库尔喇嘛把令旨放到每个人的头上,以示祝福之意⋯⋯。汗本人则从帐中走出,腰挂达赖喇嘛赠赐的马刀、箭囊和弓矢,骑上御马向佛庙驰去。及至佛庙,他翻身下马,步入佛庙,卸下武器让众人抬入,僧侣们鼓乐齐鸣,列队相待,还在佛像前一一诵经⋯⋯”。

卡尔梅克信徒
由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授号的仪式庄严而弘大,首先是大汗要盛装等待,然后由派遣到西藏归来的喇嘛带着达赖喇嘛的令旨款步而来,随后由土尔扈特部地位最高的喇嘛书库尔喇嘛接过令旨,放在汗的头上,以示已领受,之后给汗穿上圣衣,而后书库尔喇嘛面向众人宣读达赖喇嘛的令旨内容,这实际上是广为布告,以说明汗号来源于达赖喇嘛,以示汗位的合法性,随后大汗赶赴寺庙祈祷诵经,用以说明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以及广为推广之意。整个过程都已经被神圣化了,而这个神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土尔扈特首领试图进一步收拢人心的结果,他广为宣传藏传佛教,也试图借助达赖喇嘛的封号来加强自己的统治,所以,仪式的神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汗权的加强化过程。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效果,所以几乎各部蒙古王公都希望从达赖喇嘛处得到封号。
1771年,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东归,归附清朝,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抚恤救济,妥善安置,安排土尔扈特部首领赴避暑山庄朝觐,并安排赴藏熬茶事宜。但这里的赴藏熬茶已经是“政教二道”的中心转移到清朝之后的安排了,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了,况且已有郭美兰先生详细的研究成果,故本文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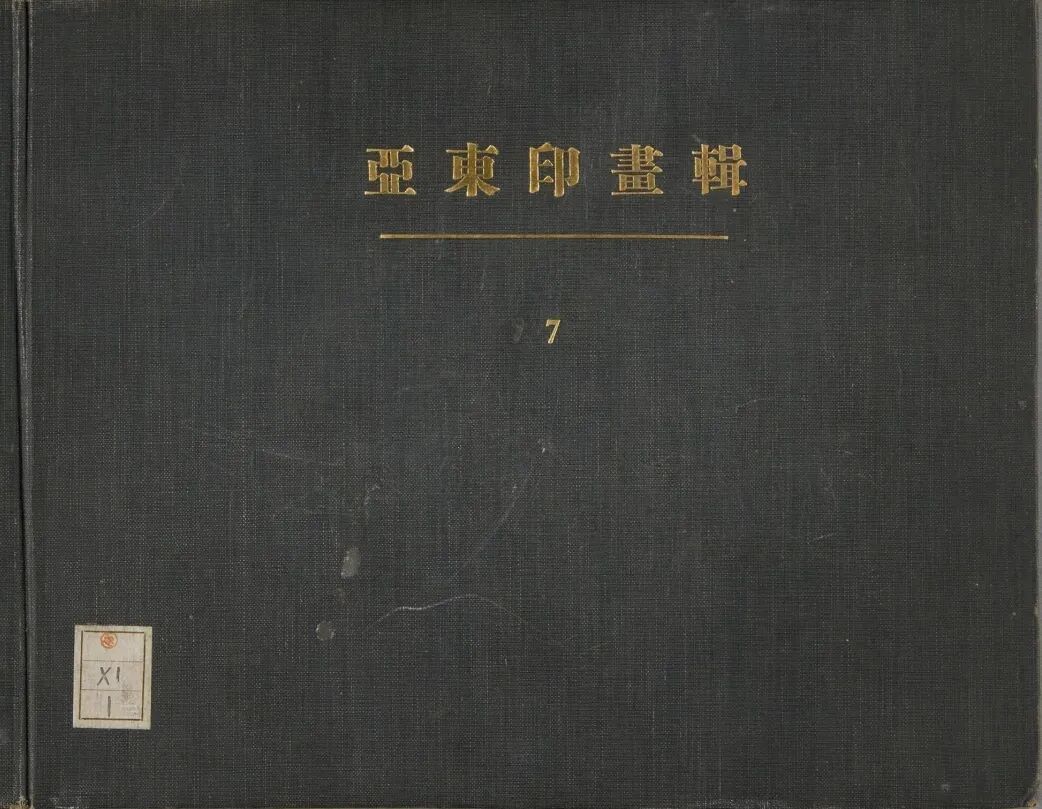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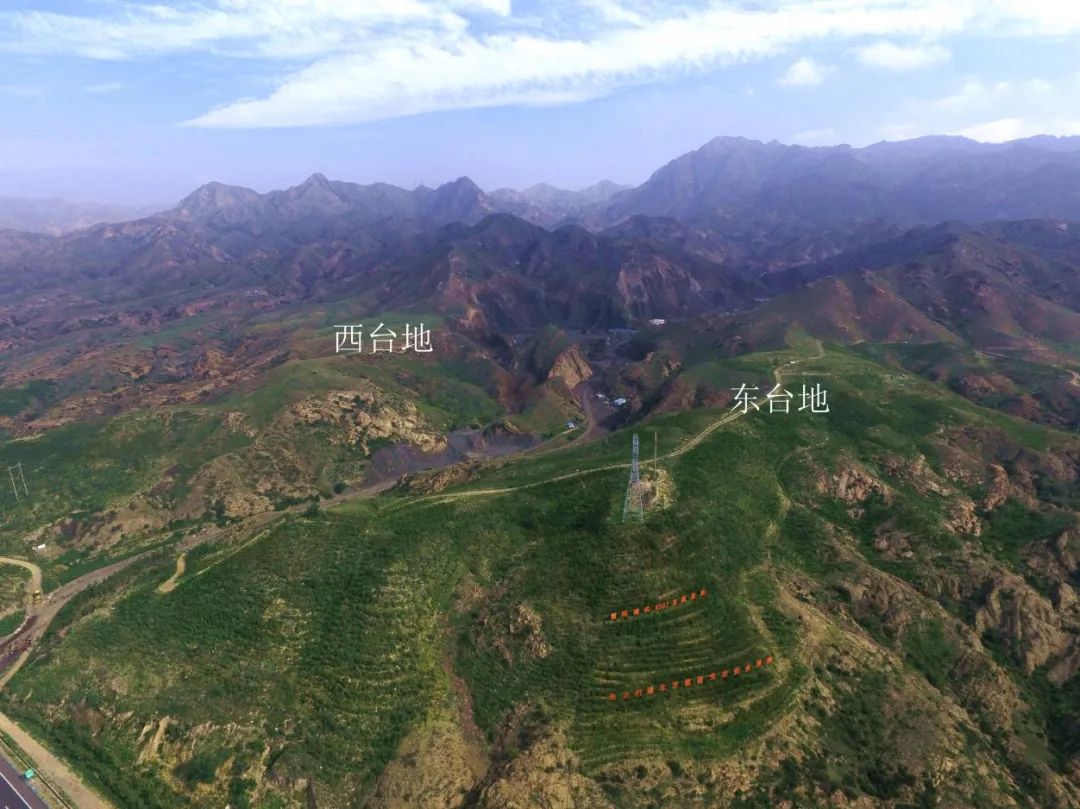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发表评论